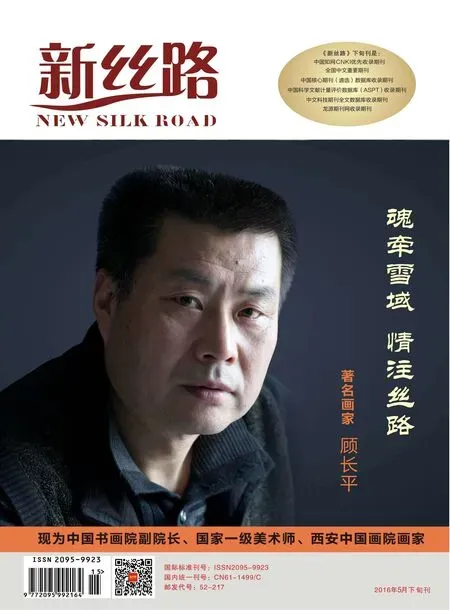發揮兵團熔爐作用推進南疆認同整合
黎鏡明(第一師黨委黨校 新疆阿拉爾 843300)
?
發揮兵團熔爐作用推進南疆認同整合
黎鏡明(第一師黨委黨校 新疆阿拉爾 843300)
摘 要:在現代民族國家的語境中,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是社會成員認同體系的兩個主要方面,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在南疆相互糾纏,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認同關系結構。一方面南疆新型民族關系不斷得到鞏固,民族認同的兼容性和協調性是主流,另一方面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緊張關系,在認同序列上可能出現以民族認同凌駕國家認同、無視國家治理、挑戰國家權威的現象。實現南疆認同整合從歷史邏輯出發具有可行性,發揮兵團“大熔爐”作用則應該是其中的應有之義。
關鍵詞:認同整合;兵團;民族團結
【DOI】10.19312/j.cnki.61-1499/c.2016.05.015
在現代民族國家的語境中,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是社會成員認同體系的兩個主要方面。所謂民族認同是指某一共同體的成員將自己和他人認同為同一民族,對這一民族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持相近態度。國家認同則是指社會成員確認自己的國民身份,自覺歸屬于國家,形成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的主體意識。[1]南疆作為典型的邊疆民族地區,受特殊歷史地理因素和族群文化的影響,當地少數民族在保有自身民族認同的同時,又形成并保持著國家認同。[2]在南疆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二者的關系總是處于動態變化中。在“民族—公民”身份相統一意義[3]上探索南疆認同整合的有效路徑,理應被納入推進新疆長治久安的視野中。
一、立足區情審視南疆認同狀況
南疆歷史上處于絲綢之路南線的中繼站,東西方文明在此風云際會,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希臘文明、波斯文明等諸多版塊在此碰撞、重疊、融匯,多元文化長期共存的局面一方面使新疆成為積淀厚重的文化“富礦”。另一方面又有明顯的“伴生礦”特質,呈現地域性、民族性乃至國際性的特征,多元文化的異質性本身即蘊含著文化沖突的可能。南疆少數民族曾經作為獨立的民族、政治單位在此生息繁衍,擁有“原生性”的民族認同。歷史上伴隨著中原王朝的經略與施治,又逐漸被納入中華文明的體系中,成為統一中華帝國的一部分。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建構和現代多民族國家的成型,使南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對象轉變成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形成“工具理性”[4]的國家認同。
新中國成立65年來,南疆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政治上實現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相互依賴,以“三個離不開”為代表的民族思想成為新時期南疆正確處理民族關系的重要指導思想,平等、團結、互助的新型民族關系不斷得到鞏固。南疆地區注重以法律手段保護少數民族的合法政治權益,積極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團結教育條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條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規。著力改善民生,不同時期從民族群眾最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入手,通過財政補貼、定向扶貧等手段,使各族人民享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實惠。少數民族自覺捍衛國家主權、積極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民族群眾廣泛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歸屬的最高對象,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兼容性和協調性是主流。
另一方面,南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緊張關系。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南疆經濟社會的較快發展,少數民族自身發展定位與利益訴求與國家總體目標間產生過些許不一致乃至沖突。在現代化進程中,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不斷感受到自身社會結構解體的危機,在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上面臨選擇困境。此外,南疆少數民族通常以本民族語言為母語,面對以漢語普通話為表征的市場經濟浪潮的席卷,民族間適應能力的不同直接導致現實利益獲取方面的差異。一旦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產生的沖突得不到及時緩解,民族隔閡就相應加深。國際上“雙泛”等反華勢力以民族宗教問題為切入口,制造分裂輿論、傳播極端思想、挑起民族爭端,并組織參與暴力恐怖活動,以達到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最終目的。內外因的相互作用造就了部分南疆少數民族的認同危機,在認同序列上出現了以民族認同凌駕國家認同、無視國家治理、挑戰國家權威的現象。
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在南疆相互糾纏,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認同關系結構。這一結構形成于歷史進程,并在社會發展中不斷獲取新的內涵。對統一多民族國家來說,南疆的認同問題既是歷史的,也是常新的,是需要永恒關注的問題。“在一個存在認同危機的時代,如果國家不能有效地促進公民對國家的認同,社會將分散成無法整合的整體,無論是宗教、族群,還是利益集團、地緣組織等,都可能構成對國家的傷害,其后果將不僅是破壞社會穩定,甚至可能引發國家內部秩序的崩潰”[5]。實現南疆的認同整合至少具有兩個維度上的意義:其一,防止民族情緒趨于極端,打擊分裂勢力。其二,形成南疆全體社會成員的黏合劑,提供南疆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安定秩序與社會環境。

二、南疆地區認同整合的可行性分析
“我們人人都有不同的領土層次認同聯系,這可使我們的認同很容易的從一個層次轉向另一個層次”[6],南疆地區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價值取向具有內在一致性,可以和諧共生。
1.在南疆,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在歷史、土地、文化等方面存在許多契合點。中原王朝在漫長歷史進程中對南疆行之有效的治理,使民族之間形成了良性互動。南疆少數民族大多以伊斯蘭教為宗教皈依,當前“三股勢力”往往打著宗教的旗號為其分裂祖國的行徑尋求道義支撐,但同時也應該看到愛國是伊斯蘭信仰的一部分,“愛國是信仰中的堅守,也是穆斯林的擔當和責任,彰顯出穆斯林的高度與大義”[7],《古蘭經》規定“吉哈德”(圣戰)是穆斯林的宗教義務,但同時又提出“如果他們(非穆斯林)傾向和平,你也應該傾向和平”。庫爾班·吐魯木騎著毛驢去北京見毛主席的故事在南疆廣為傳誦、民族團結模范人物不斷涌現,共同的苦難與輝煌使各族人民使各族人民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從而樹立了共同繁榮發展的理想抱負,預示著認同整合的必然趨勢。
2.中國“和而不同”的文化傳統令民族間的界限充滿彈性。“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8]古代先民往往用文化而非血統作為“我族”與“他族”的區隔,并留下雙方相互轉化的孔道。儒家知識精英所推崇的“天下體系”雖然具有文化中心主義的特征,但極具包容性,在這一體系中服從國家發展大局和豐富民族自身文化并不沖突。中國傳統文化為南疆認同整合預留了足夠的文化空間。
3.新疆與內地一體化程度的加深,使南疆民族與國家的聯系更為緊密。新的歷史時期,南疆各民族無論是否愿意,都必然要與其他民族發生聯系,“民族不再是古代的那種民族—同屬于一個祖先的后裔,或繁衍于一個特定地域的土著...而是在國家影響下,在歷史進程中發展。它源于國家,而非位于國家之上”[9],固步自封的民族不可避免的會走向邊緣化,而積極投入國家建設帶來的南疆社會面貌的改觀和民族自身發展,會使南疆的國家認同得到提升并趨于穩固。
三、以兵團熔爐作用帶動南疆認同整合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次新疆工作會議中強調:“要在各族群眾中牢固樹立正確的祖國觀、民族觀,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各族群眾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2015年8月24日,習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又增加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五個認同”本質上是對認同整合的闡釋與升華,在認同整合中構筑一體多元文化,兵團“凝聚各族群眾大熔爐”的功能定位要求兵團人在推進南疆認同整合中發揮表率作用。
1.兵團凝聚各族群眾的熔爐作用是由兵團文化的多元因子決定的。兵團人來自五湖四海的特征和多民族的人員結構,使得兵團人具有兼容并蓄的胸襟和底蘊,具有凝聚新疆各族人民的親和力,也使兵團具備在南疆推進認同整合的內在優勢。兵團一方面以“熱愛祖國”為精神坐標,一方面又是民族團結的縮影,在兵團這個大家庭中,各民族干部職工平等和睦、攜手共進,始終保持著國家認同相對其他認同的優先性。發揮兵團文化高地作用,將民族文化與現代文化熔于一爐,激揚多元文化的活力與和諧,勢必能在南疆認同整合中有所作為。在具體做法上可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鄉土情感教育、傳統美德教育、民族團結教育、結合起來,尤其需要注重雙語教育,打造民族間交流互動的基礎性話語平臺,通過潛移默化的引導,使兵團少數民族產生對祖國的親近感,提升南疆認同整合的時效性。
2.南疆的認同整合呼吁和諧的兵地關系。兵團四個師散落鑲嵌在南疆四地州,兵地是共同擔負建設南疆任務的統一整體。兵團的熔爐在鍛造民漢文化“合金”的同時,也在向周邊地方輻射光和熱。在南疆,只有增進兵地間的交往,才能產生更高層次的民族認同,才能實現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并軌與協調。南疆的認同整合不能脫離兵地協調發展,具體而言,就是要求兵團政治上加強與南疆地方黨政溝通理解,經濟上加強與地方發展規劃的銜接,社會治理上探索探索促進兵地團結的途徑方式,維穩戍邊上構建構建兵地一體的反應機制,干部隊伍建設上促進兵地干部掛職交流。做到邊疆同守,優勢互補,互利共贏,讓兵地融合發展成為南疆認同整合的實現途徑。
3.要以兵團熔爐作用構建基礎性的國民身份。美國歷來被視為熔爐政策的典型,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曾自豪地宣稱“美國人國民身份高居于其他身份之上”[10],我國在南疆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尊重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但針對少數民族的特殊政策絕不等同于在政治宣傳和社會治理中總是要強調社會成員的民族身份,承認少數民族作為公民的一般權利也絕不等同于承認其作為特殊族群的集體權力。構建基礎性的國民身份是兵團熔爐作用的最終價值取向,實踐中要引導少數民族認識到:正是由于其國民身份,全體社會成員才能以平等身份共處于南疆這一廣袤國土上,平等追求利益的實現,國民身份同時意味著需要承擔維護祖國統一的義務,從而推進南疆的認同整合。
注釋:
[1]沙勇:《多元一體: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整合機制研究》,載《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2]由于南疆漢族同胞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高度同構性,本文所指南疆認同整合主要指南疆少數民族的認同整合。
[3]蔣紅:《多維視野下基于價值觀建設的認同整合路徑探析》,載《西南邊疆民族研究》2012年第12期。
[4]陸海發:《邊疆治理視野下的認同整合研究》,載《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5]關凱:《族群政治》,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02頁。
[6][西]胡安·格:《民族主義與領土》(徐鶴林等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7]王平:《愛國是伊斯蘭教的優良傳統》,人民日報2014年5月20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0520/c1003-25037616.html。
[8][唐]韓愈:《原道》,《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全七冊)》,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651頁。
[9](英)阿克頓.自由與權力:《阿克頓勛爵論說文集》(侯健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10](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頁。
參考文獻:
[1]馬戎,趙嘉文.民族發展與社會變遷[D].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2]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兵團調查總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統計年鑒(2012)[Z].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
[3]馬大正等.新疆史鑒[D].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簡介:
黎鏡明,男,第一師黨委黨校科研辦,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