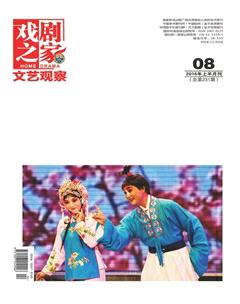費(fèi)洛蒙下的愛(ài)
【摘 要】近年來(lái),用中國(guó)傳統(tǒng)戲曲形式去移植和改編西方經(jīng)典名著的作品層出不窮,各種移植與改編的形式多種多樣,各有千秋。豫劇《朱麗小姐》屬于比較典型的移植改編成功的作品,它賦予了劇中人物鮮活的生命力,無(wú)論在語(yǔ)言、動(dòng)作、人物形象等各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充滿了創(chuàng)新性與實(shí)驗(yàn)性。
【關(guān)鍵詞】豫劇《朱麗小姐》;實(shí)驗(yàn)性;創(chuàng)新性;人物形象;大團(tuán)圓結(jié)局
中圖分類號(hào):J825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007-0125(2016)08-0016-02
一、豫劇《朱麗小姐》的創(chuàng)新性與實(shí)驗(yàn)性
《朱麗小姐》是瑞典戲劇大師斯特林堡著名的自然主義代表作品,歷年來(lái),對(duì)于《朱麗小姐》移植與改編的作品眾多,其曾經(jīng)多次以電影、話劇、舞劇、戲曲等形式上演,足以證明斯特林堡的作品在主題、故事情節(jié)、哲學(xué)性以及人性等方面對(duì)觀眾的吸引力。而傳統(tǒng)戲曲對(duì)于《朱麗小姐》進(jìn)行移植與改編的作品也有很多,比較著名的是劇作家孫惠柱改編創(chuàng)作的京劇版《朱麗小姐》,對(duì)之后其他地方戲曲劇種的移植和改編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而豫劇版《朱麗小姐》在保留了京劇本唱詞的基礎(chǔ)上,將豫劇化的對(duì)白加入其中,非常具有實(shí)驗(yàn)性與創(chuàng)新性,也贏得了觀眾的認(rèn)可和贊賞。移植和改編國(guó)外作品,最重要的是用中國(guó)化的視角去分析原著深厚的思想內(nèi)涵,要研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藝術(shù)特色的表現(xiàn)方式,用東方的民族文化去解讀西方名著,從而達(dá)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費(fèi)洛蒙”是動(dòng)物界包括人類、哺乳動(dòng)物、昆蟲等同物種之間相互溝通,并發(fā)出求偶、警戒、社交、合作等訊號(hào)的訊息分子,存在于人和動(dòng)物體內(nèi)的天然化學(xué)信息,它能激發(fā)性吸引及其系列反應(yīng),在西方是“性欲望”的代名詞。“費(fèi)洛蒙”在《朱麗小姐》中通過(guò)朱麗小姐、男仆項(xiàng)強(qiáng)和女仆桂思娣三人錯(cuò)綜復(fù)雜的人物關(guān)系得到很好的闡釋,顯示了兩性的吸引、男女支配權(quán)的爭(zhēng)奪以及“在前的必將在后,高高在上的必將跌落凡塵”這一打破尊卑秩序、揭示命運(yùn)輪回的社會(huì)命題。此外,豫劇《朱麗小姐》在方言的運(yùn)用以及戲曲動(dòng)作的編排上極具開(kāi)拓性與創(chuàng)新性。
首先,豫劇《朱麗小姐》在河南方言的運(yùn)用上是獨(dú)特的,從實(shí)驗(yàn)性上來(lái)說(shuō),嘗試用豫劇移植外國(guó)名著,實(shí)驗(yàn)性已經(jīng)足夠明顯。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載體,將方言融入戲劇表演中的作品也非常罕見(jiàn),有利于貼近群眾生活,同時(shí),幽默風(fēng)趣的方言更有利于增加作品的詼諧效果。當(dāng)觀眾聽(tīng)到女仆桂思娣撒嬌嗔怒罵項(xiàng)強(qiáng)“你個(gè)鱉孫……”時(shí)發(fā)出哄笑,這些內(nèi)容帶給觀眾一種意想不到的感覺(jué),證明選擇方言的目的達(dá)到了。在斯特林堡的原著《朱麗小姐》中,桂思娣被認(rèn)為是完全沒(méi)有主見(jiàn)、遲鈍的人,但是豫劇《朱麗小姐》在河南方言的運(yùn)用下,使桂思娣頓時(shí)獲得了鮮明的存在感。豫劇版方言對(duì)于女仆立體形象的塑造起到關(guān)鍵作用,有利于在悲劇作品中增強(qiáng)喜劇效果,同時(shí)增添了活潑生動(dòng)的色彩。
其次,豫劇《朱麗小姐》中最大的實(shí)驗(yàn)性和創(chuàng)新性還表現(xiàn)在對(duì)戲曲程式動(dòng)作以及舞蹈動(dòng)作的編排和加工上,包括渲染熱鬧氣氛的元宵節(jié)大頭娃娃舞、村民獅子舞和代表眾口鑠金、世俗評(píng)論的圍剿舞。個(gè)人的舞蹈包括表現(xiàn)朱麗欲念的思春舞,項(xiàng)強(qiáng)自以為地位上升時(shí)洋洋自得的穿靴舞和驚慌失措時(shí)的脫靴舞,這一穿一脫的身段動(dòng)作借用老生、花臉、丑行的功夫,通過(guò)表演生動(dòng)地將項(xiàng)強(qiáng)的心理活動(dòng)展現(xiàn)給觀眾,這也使得斯特林堡的作品達(dá)到戲曲化技藝美所無(wú)法企及的高度,同時(shí)也具有相當(dāng)深厚的思想內(nèi)涵。親繡襪舞和調(diào)情的雙人獅子舞在視覺(jué)上增加了娛樂(lè)性、刺激性,在色彩處理上也下了功夫,這場(chǎng)戲成為主創(chuàng)人員樂(lè)于強(qiáng)調(diào)的戲曲程式技巧與芭蕾有機(jī)結(jié)合的成功范例,既能表現(xiàn)含蓄、寫意的曖昧場(chǎng)面,也能提升劇作的視聽(tīng)觀賞性。實(shí)驗(yàn)豫劇《朱麗小姐》以河南豫劇充滿鄉(xiāng)土氣息的道白與聲腔,鮮活地描繪出西方戲劇大師筆下人物的復(fù)雜心聲。為了充分體現(xiàn)河南韻味,豫劇《朱麗小姐》將西方生活場(chǎng)景變?yōu)楹幽相l(xiāng)間大宅。為了體現(xiàn)“西洋劇目本土化,傳統(tǒng)藝術(shù)現(xiàn)代化”,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在劇情、舞美等方面都下足了功夫,表演中將北歐音樂(lè)元素成功地融入到音樂(lè)曲調(diào)設(shè)計(jì)之中。豫劇音樂(lè)是根基,但有新鮮的元素融入其中,互相呼應(yīng),那婉轉(zhuǎn)動(dòng)聽(tīng)的音樂(lè)也是極其優(yōu)美的。
二、豫劇《朱麗小姐》中人物性格的復(fù)雜性
豫劇《朱麗小姐》鮮明地塑造了朱麗小姐敢愛(ài)敢恨的“真女子”形象,以及項(xiàng)強(qiáng)虛情假意偽君子的形象。朱麗小姐雖貴為千金,但自身卻是脆弱的,從她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高傲的風(fēng)骨和對(duì)世俗的挑戰(zhàn)精神。但是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她卻是天真、幼稚的,她畏懼的不是現(xiàn)實(shí)的殘酷,而是榮譽(yù)的喪失;她不畏懼死亡,而是害怕精神上的崩潰;她敢于挑戰(zhàn)世俗,卑微地前行;她為了自己并不真實(shí)的愛(ài)情,寧愿放下貴族的身份,最后甚至愿意放棄生命與尊嚴(yán)。由此可見(jiàn),東西方女性形象還是有明顯區(qū)別的。從女權(quán)主義的視角去分析,東方女性和西方女性形象的不同點(diǎn)在于:東方女性的形象大多被塑造為善良、溫柔、美麗、堅(jiān)貞的,都是為男人而生,處于從屬和依附的社會(huì)地位,離開(kāi)了這些作為世界主宰的男人,一切皆無(wú)意義。而西方女性則更具反抗意識(shí),勇于挑戰(zhàn)世俗,追求愛(ài)情的自由,是叛逆者的形象。東方女性和西方女性形象的相同點(diǎn)在于:兩者都有自甘屈從、犧牲的自我定位以及“沒(méi)有愛(ài)情,寧愿去死”的人生定位。在男性視角下的中國(guó)戲曲作品中,并不回避女性爭(zhēng)取愛(ài)情的主動(dòng)性,她們期盼著理想中天長(zhǎng)地久的愛(ài)情,為了愛(ài)情寧愿放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而這些外表柔弱、性格剛烈的女子,最終往往會(huì)在絕望的時(shí)刻,帶著她們堅(jiān)貞的愛(ài)情觀,選擇以死殉情的歸宿,這就是她們所謂的斗爭(zhēng)精神和反抗方式。朱麗的悲劇有歷史必然性,根源在于特殊的封建階級(jí)的局限性,封建勢(shì)力通過(guò)聯(lián)合其他勢(shì)力對(duì)于朱麗小姐的扼殺,完成了對(duì)覺(jué)醒的毀滅。《朱麗小姐》完美詮釋了悲劇──歷史的必然要求與現(xiàn)實(shí)的不可能性之間的矛盾,使得斯特林堡戲劇在今天依然有強(qiáng)勁的生命力。
長(zhǎng)期以來(lái),人們?cè)噲D用男女、階級(jí)、女權(quán)主義來(lái)分析這部作品。在西方,其實(shí)下層女人嫁給上層男人并不具有反叛意義,而精神和地位處于上層地位的女人和下層男人發(fā)生關(guān)系才是叛逆的。一個(gè)女主人或者千金小姐愛(ài)上賣油郎或者窮書生在中國(guó)戲劇中是常事,“仙女嫁農(nóng)夫”更是佳話,廣為流傳,而在西方是男神愛(ài)上凡女,這就是東西文化的不同。西方特別強(qiáng)調(diào)作為男子的自然本能,強(qiáng)調(diào)男性的社會(huì)地位,而在中國(guó)文化中更多的是男女倒錯(cuò),更愿意將自然的本性淹沒(méi)在社會(huì)功能之中,所以陰盛陽(yáng)衰在我們的文化中是正常的現(xiàn)象。東西方不同文化起源和思想觀念對(duì)戲劇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明顯的影響,文化認(rèn)同和主客觀意念的不同對(duì)東西方民族意識(shí)也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北歐一向以女權(quán)主義勢(shì)力聞名于世,這和斯特林堡的女性問(wèn)題也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當(dāng)代中國(guó)女性已經(jīng)得到極大的解放和自由,但是人性的進(jìn)化是緩慢的,關(guān)于人性問(wèn)題的探討也將是永恒的。
三、由豫劇《朱麗小姐》對(duì)比看中西結(jié)局
豫劇《朱麗小姐》是中西結(jié)合的產(chǎn)物,戲中以中國(guó)獨(dú)特的藝術(shù)形式揭示了深刻的思想內(nèi)涵以及對(duì)人性的剖析與鞭撻,以劇中人物的悲慘命運(yùn)透析西方社會(huì)各階級(jí)的思想觀念。由豫劇《朱麗小姐》對(duì)比看中西結(jié)局,兩者在創(chuàng)作上還是有明顯區(qū)別的。中國(guó)戲劇的主人公大多具有積極向上、進(jìn)取的反抗意識(shí),而西方戲劇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矛盾的綜合體,有的鮮艷光明,有的灰暗慘淡,著重塑造雙重性格的人物,盡顯人性本質(zhì)。《朱麗小姐》是斯特林堡的著名作品,認(rèn)真研讀任何作品時(shí)我們都應(yīng)知人論世,從深層次研究社會(huì)本質(zhì)和人性的復(fù)雜性,才能得出更理性、更透徹的理論。縱觀斯特林堡一生的命運(yùn),他曾經(jīng)有過(guò)三次幸福的婚姻,但都以離婚為結(jié)局,每一次短暫的幸福都以痛苦的折磨而告終。這些經(jīng)歷也造成他在生活中的瘋狂與偏執(zhí),導(dǎo)致他在作品中毫不顧忌社會(huì)道理與現(xiàn)實(shí)。而在他的作品《朱麗小姐》中,仆人項(xiàng)強(qiáng)延續(xù)著于連式的激憤,但英雄氣概已不復(fù)存焉;而朱麗小姐不體面的結(jié)局更令人驚慟──她敢于活下來(lái)才是悲劇,悲劇不止是毀滅,更是承擔(dān),是熱愛(ài)命運(yùn)所啟迪的神秘。但斯特林堡不信任如此結(jié)局,沒(méi)了自由、愛(ài)及信仰,朱麗如同項(xiàng)強(qiáng)摔死的鳥兒,也像一件陪葬于冰冷墓穴的珍美瓷器。
然而,在中國(guó)作品中卻很少出現(xiàn)像《朱麗小姐》這樣的悲慘結(jié)局,就算再悲慘的故事,最后都會(huì)被作者賦予圓滿的結(jié)局,這種現(xiàn)象反映了中華民族對(duì)待事物所獨(dú)有的認(rèn)識(shí)發(fā)展規(guī)律。從歷史哲學(xué)的角度看,中國(guó)幾千年的農(nóng)業(yè)基礎(chǔ)使百姓形成了安土、樂(lè)天、安居、樂(lè)業(yè)的觀念,黎民百姓面對(duì)寒來(lái)暑往的自然,故易養(yǎng)成周而復(fù)始、物極必反的循環(huán)發(fā)展理念。善惡有報(bào)的大團(tuán)圓結(jié)局和好人由順境轉(zhuǎn)入逆境的悲慘結(jié)局,只是表達(dá)是非之心、愛(ài)憎之情的兩種不同形式,而不是愛(ài)憎是非本身;大團(tuán)圓是為滿足崇尚圓滿的社會(huì)心理需求而創(chuàng)造的理想境界,它不是藝術(shù)家對(duì)社會(huì)生活的逼真再現(xiàn)。西方的創(chuàng)作一直追求寫實(shí)的生活藝術(shù),追求形似,因此許多作品中都講究生活的真實(shí),這也是西方作品中有眾多優(yōu)秀悲劇的原因。
這兩種結(jié)局的設(shè)計(jì)涉及創(chuàng)作者到底是該追求生活真實(shí),還是一味去滿足觀眾的需求而追求藝術(shù)真實(shí)的問(wèn)題。“生活真實(shí)是基礎(chǔ),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來(lái)源,任何藝術(shù)都來(lái)自于生活真實(shí),沒(méi)有生活真實(shí)作基礎(chǔ),一切文學(xué)藝術(shù)就是無(wú)源之水,無(wú)本之木。任何文學(xué)作品脫離了生活真實(shí),靠主觀臆想,胡編亂造,就沒(méi)有了真實(shí)性,也就談不上藝術(shù)真實(shí)。”①也就是說(shuō),藝術(shù)來(lái)源于生活,但更高于生活,是對(duì)真實(shí)生活的提煉與升華。我們可以通過(guò)藝術(shù)的真實(shí)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事物進(jìn)行改造和升華,創(chuàng)造集藝術(shù)性、生活性、創(chuàng)新性于一體的新事物,這就是藝術(shù)。因此,藝術(shù)真實(shí)是可以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進(jìn)行改造而實(shí)現(xiàn)的。關(guān)于中西方兩種結(jié)局的探究,我們無(wú)法給出一個(gè)具體而明確的答案,也不能盲目地說(shuō)孰好孰壞,因?yàn)檫@和中西傳統(tǒng)文化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而且中西藝術(shù)也追求不同的境界。豫劇《朱麗小姐》的實(shí)驗(yàn)性或許可以為今后中國(guó)戲曲作品對(duì)西方藝術(shù)作品的新詮釋作出突出貢獻(xiàn),促進(jìn)中西藝術(shù)的相互交融。
注釋:
①賈振華.論中國(guó)古代戲劇的大團(tuán)圓結(jié)局[J].當(dāng)代戲劇,2007(8).
參考文獻(xiàn):
[1]周愛(ài)華.戲曲美學(xué)導(dǎo)論[M].北京:中國(guó)戲劇出版社,2012.
[2]李漁.閑情偶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張之薇.中國(guó)古典悲劇戲劇論[M].北京:學(xué)苑出版社,2011.
[4]周憲.美學(xué)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
作者簡(jiǎn)介:
許昌朋,山東藝術(shù)學(xué)院2015級(jí)戲劇與影視學(xué)專業(yè)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