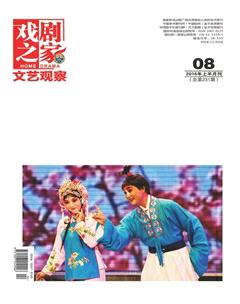電視劇《紅高粱》與小說、電影的敘述視角對比分析
【摘 要】2014年電視劇版《紅高粱》在四大衛視齊亮相后,立即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也得到了褒貶不一的評價。有原著和電影珠玉在前,人們已經有了固定的心理圖勢,“紅高粱”這個文本留下的空白已經很少,因此電視劇《紅高粱》的改編是戴著鐐銬去跳舞的勇氣之作,無論成敗得失,它反映的是當今影視創作的現狀和趨向,帶有時代和社會的烙印。
【關鍵詞】《紅高粱》;敘述視角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8-0113-02
從小說敘事到電影敘事,再到電視敘事,由于各自的敘事媒介不一樣,表現方式也不一樣。因此從小說到影視的文本轉換之間,“紅高粱”這個“元故事”在不斷的改編過程中呈現出多元化的審美傾向。本文將結合小說和電影版的《紅高粱》,對比分析電視劇在敘述視角上的不同之處,就改編的得失提出自己的一點看法,并簡要分析出現這些得失的當代社會原因。
敘述視角是敘事者與人物之間認知關系的一種表現形式,是指呈現故事時采用的方式和觀察故事時所用的角度。敘述視角作為敘事學中的一個概念,以前主要在文學敘事中分析,當電影和電視逐漸成為新的敘事載體,并有不同于文字的敘事技巧時,對影視作品中如何運用敘述視角來更好地講故事顯得迫切而重要。比如:畫外音可以跳脫出當前的敘事時空,豐富敘事的層次,出現的獨白是敘述人稱的轉換,蒙太奇手法可以使多時空并列交錯進行。因此,電影與小說對同一個故事的表達不同,電視又與電影的表達不同,因為“誰在講故事”“以誰的眼光看故事”和“講誰的故事”在不同的敘事載體中有各自適用的表達方式。敘述視角按照所知視角來分析,可分為三種情況,即“全知敘述視角”“限知敘述視角”和“純客觀敘述視角”,熱奈特稱之為“零度聚焦”“內部聚焦”和“外部聚焦”。全知視角即上帝視角,敘述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既知道事情的外部沖突,又知道人物的內心活動;限知視角是指敘述者與故事中的人物知道的一樣多,故事中人物的命運、前因后果是隨著劇中人自己的行動而發生的,敘述者并沒有擁有事先知情權;純客觀敘述是指敘述者比任何一個人知道的都少,它僅僅敘述某些特定的人聽到的、看到的。申丹在此基礎上提出四種視角:1.零視角(即全知敘述);2.內視角(第三人稱有限視角、主人公經驗敘述視角和處于“故事”中心第一見證人敘述);3.第一人稱外視角(第一人稱回顧式敘述自我眼光和處于故事邊緣的“我”的第一人稱見證人敘述);4.第三人稱外視角。《紅高粱》的小說、電影和電視劇各自運用了不同的敘述視角。
小說《紅高粱》講述了“我爺爺”和“我奶奶”的傳奇人生故事,作者運用了三種敘述視角,在不同的場景敘述中選取不同的敘述視角。小說一開始就以“我父親這個土匪種”開頭,串聯起“我爺爺”“我奶奶”的愛情故事和抗日故事。“我”是敘述者,是擁有當代身份的人,既是第一人稱視角,又是全知視角。“我”回到故鄉高密縣后,通過自己查資料以及旁人的敘說,知道了“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故事。當時的“我父親”也只是十四歲的孩子,我更是不可能知道“我爺爺”顛轎時或“我奶奶”臨死前的內心活動,顯然,“我”并不是參與故事建構的當事人,而只是一個故事的轉述者,因此“我”的敘述擁有全知視角也是可以理解的,并在故事敘事中充當了隱含作者的代言人,將以前文學作品中隱含作者無法發聲而需要讀者去想象和揣摩的格局打破。小說中除了“我”的視角外,還有“我父親”的第三人稱限知視角,比如從“我父親”的角度去講述最后抗戰的畫面和羅漢大爺被剝皮示眾的場景。這種視角隨時切換的講故事方式并沒有讓觀眾誤解,反而增加了文章表達的豐富性,因為不同視角的敘述并不是重復,而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對當時的場景進行描述,比如羅漢大爺被剝皮示眾的時候,“我父親”看到的不是反抗日軍侵略暴行的行為,而是民族氣節的展示,是不帶有政治因素的純粹感官上的認識,而“我”作為一個現代人,以全知視角去想象那段畫面時,對羅漢大爺的犧牲產生了深深的敬意。“我父親”作為目擊者是充當了歷史代述者,而“我”的敘述屬于子孫后輩的想象,帶有當代社會語境,同樣的事情切換不同的敘述視角,打破了時空阻礙,將歷史與現代聯系起來,豐富了小說的內涵和文化意蘊,同時將作者的觀點通過“我”這個隱含作者之口表達出來。
電影《紅高粱》沿用了“我”的敘述視點,影片開頭黑場的時候即以敘述人“我”的畫外音形式解說:“我給你說說我爺爺、我奶奶的這段事,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還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緊接著畫面就是“我奶奶”身穿紅色嫁衣出場的特寫鏡頭,開始講述“我奶奶”被嫁去單家,路上遇到土匪,回門和“我爺爺”在高粱地里野合的故事,這時敘述者“我”處于第三人稱外視角的位置,是外聚焦敘事。“我”在影片中雖然不是直接講述者,但是是連貫整個影片必不可少的部分,起到了起承轉合的作用,比如在時間處理上,羅漢大爺走后,我家的現狀用“一晃九年過去了,我父親也九歲了”進行交代,作為故事的引出者,“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故事可以添加進“我”的想象與理解中,拓寬了單純從“我父親”的視角觀察到的故事。貌似是在追敘先輩的故事,其實在這種單線敘事的背后由于敘述者“我”的存在,使影片呈現一種“復調式二聲部”的結構。與小說相比,電影把許多原來“我”的評論和理解具象化為畫面語言,這樣既避免了“我”的時常出現打亂了影片的正常敘事,又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形成心理幻覺時保持一份清醒。畫面內敘事是隱含的“我”,這個視角的“我”是感性的,帶著我對“爺爺”“奶奶”既有的心理認知去講述,是看似客觀的主觀;畫外音中出現的“我”是發聲者,是理性的講敘者,與畫面敘事承擔了同樣的功能,但比畫面敘事簡潔、理性,是以娓娓道來的口吻述說的,是用主觀形式對過去事實純客觀的追述。電影對原著中“我”的視角的處理方式符合電影敘事的法則,既保留了原著的精髓,又展現了電影獨特的魅力。
相比原著和電影,電視劇《紅高粱》在敘述視角上最大的不同是舍棄了“我”這個第一人稱全知視角。從電視劇的敘事特色來看,攝像機本身就是一個特殊的視點,使故事好像并沒有講敘者,呈現超話語的敘述模式。電視劇將原著中的抗戰這條主線穿插了“爺爺”“奶奶”的愛情故事,輔線交叉敘述的模式變成了單一直線型敘事,前因后果、情節矛盾都是隨著劇情發展而展開的,從邏輯上來看,對敘述者“我”作評論與解釋的需要不像小說和電影那么強烈。從時間長度來看,電影有兩個小時的敘事容量,需要“我”的畫外音來壓縮時空,而電視劇六十多集的敘事時間給了充分的熒幕時間去填充畫面信息,如果此時“我”的敘述與畫面敘述不能起到相互補充的作用,或者體現出一種悖反的張力時,則會顯得敘述拖沓,節奏緩慢。因此我認為電視劇舍棄“我”的敘述是一種討巧的做法,也是符合電視劇敘事規律的。電視劇版《紅高粱》雖然在敘述聲音上舍棄了“我”這個隱含作者的代言人,故事層次顯得不夠豐富、深厚,但在同一個場景中,全知視角和限知視角交叉使用。比如在九兒被張俊杰的爹設計陷害,落到土匪花脖子手上這場戲中,觀眾不知道九兒的命運將會如何,能否逃脫匪窩,以攝像機的視點作為作為隱含的敘述人,畫面給出的是九兒此刻面臨的環境,屬于故事內的內聚焦,后來九兒想辦法自救,用指甲把自己身上抓傷然后去見花脖子,觀眾已經知道了九兒的計謀,因此在看她與花脖子的談判時,就很容易產生趣。觀眾通過攝像機的視點獲得了上帝視角,營造了一種希區柯克式的懸念。
綜上分析電視劇《紅高粱》在敘述視角上與小說和電影的不同之處,原因是他們各自的敘事載體不一樣,媒介不同,其接受群體、傳播方式、敘事容量和表達方式等都有很大差異。小說依靠文字敘事,具有多義性、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文本空白比較多,讀者需要聯想、想象去建構故事。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用鏡頭敘事,且視聽語言是針對感官的直接刺激。電影的熒幕時間只有兩個小時,而小說則不受時間的限制,電視劇又比電影有更充分的敘事空間。從受眾的文化水平來看,從小說到電影再到電視劇,其文化層次是遞減的,因而在改編的過程中電影傾向選取小說的主要片段和場景作為敘事線索,電視劇《紅高粱》則把電影中舍去的高密縣的歷史補全、“我爺爺”“我奶奶”各自的“成長史”和家庭狀況也全部呈現出來,按照事情發生的先后順序平鋪直敘,并且為了劇情的需要,添加了很多新的人物,形成幾組相互牽扯的人物關系,更加寫實,故事性也更強。
針對電視劇《紅高粱》褒貶不一的評價,我認為這是由于現在客觀存在的社會原因造成的。商業主導下的市場規律,使收視率和收視份額成為不得不考慮的首要因素,山東衛視拿到版權后,為了趕在十月份高粱季拍,出劇本大綱到正式開拍只有四個月的時間,因此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精雕細琢每一個人物形象;為了商業利潤而將劇情拖到六十多集,使得敘事策略不得不從九兒與余占鰲的單一線索,裂變為多個線索。電視劇的敘事容量本是電視敘事的優勢,但過多的敘事線索沖淡了原本的人物特色,把抗日戰爭加進去卻又沒有歷史真實感和厚重感,抗戰成了烘托敘事的一個背景。高收視率反映了商業上的成功,這是電視劇版《紅高粱》的“得”,而“失”則在于“紅高粱精神”的缺失。原著通過“紅高粱”這個鮮明夸張的意象,表達了對原始生命力的贊揚和對“種的退化”的隱憂。電影改編成功的原因在于選擇了寫意式的改編方式,通過“我爺爺”和“我奶奶”自立自強、勇于反抗的性格來傳遞“紅高粱精神”。電視劇中的人物更像類型人物,流于世俗化,缺少對原始生命力的渴望和野生野長的土氣,多了些現代人的煙火氣。總而言之,電視劇《紅高粱》講了一個通俗可看的大眾性故事,但已不是莫言的“紅高粱”,缺了一口高粱酒,紅高粱精神便不存在了。
參考文獻:
[1][美]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M].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30.
[2]莫言.紅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
[3]張霞.齊魯周刊專訪——趙冬苓:我為什么重拍《紅高粱》[J].齊魯周刊,2014(42).
作者簡介:
王夢婷,中國傳媒大學在讀碩士,研究方向:廣播電視藝術學電視文藝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