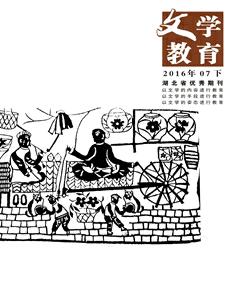《戰(zhàn)后日本的親屬關(guān)系》小論
張宬
『戦後日本の親族関係―核家族化と雙系化の検証―』(《戰(zhàn)后日本的親屬關(guān)系——對核家族化與雙系化的驗證》)一書系旅日中國學(xué)者施利平教授用日文撰寫專著。全書169頁,并不冗長的篇幅集中火力完成了一次對家族社會學(xué)界傳統(tǒng)定論的挑戰(zhàn)。
戰(zhàn)后的日本社會,家族、親屬關(guān)系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按照家族社會學(xué)的通行觀點,由于家戶規(guī)模的縮小、婚后與父母同居率的低下、還有母女之間交往、援助關(guān)系的緊密,關(guān)于家族的制度由家制度——“直系家族制度”,向以核家族為原則的“夫婦家族制度”轉(zhuǎn)換(所謂“核家族化”)。親屬關(guān)系也由優(yōu)先父親與長子關(guān)系的父系、單系,向無論夫方、妻方,無所偏重的雙系性變化(所謂“雙系化”)。施氏指出:這種通論不能吻合地解釋和說明日本現(xiàn)當(dāng)代有關(guān)家族構(gòu)成和親屬關(guān)系的現(xiàn)實。肇始于1980年代的現(xiàn)代家族論以家族的心性——自律性和情緒性等為主要研究課題,分析家族制度的視角有所遺漏,未能嚴(yán)密地驗證現(xiàn)實中的婚后家族、親屬關(guān)系在家族制度這一側(cè)面的情況,因此關(guān)于戰(zhàn)后家族是否由直系家族制度向夫婦家族制度轉(zhuǎn)換,親屬關(guān)系是否由父系向雙系轉(zhuǎn)換,仍不明朗。
為彌補以上不足,正確地理解戰(zhàn)后日本的家族、親屬關(guān)系的存續(xù)和變?nèi)荩緯鴱闹贫鹊膫?cè)面(同居、家的繼承、相續(xù))和情緒的側(cè)面(經(jīng)濟上的和非經(jīng)濟上的援助和交往)兩者結(jié)合起來進行把握。在這種理論框架結(jié)構(gòu)的提示下,以在日本全國實施的針對男女5000余人(1911年—1981年間出生)的家族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為基礎(chǔ),追尋今天的日本家庭中家族、親屬關(guān)系的歷史性變化。此外,將同在儒教文化圈,重視親屬關(guān)系的中國和韓國的家族、親屬關(guān)系進行了比較。
結(jié)果:在制度方面,長子優(yōu)先的直系家族制度仍然殘留,但女兒并非必須被排除在外,亦即非父系性;一子優(yōu)先的直系家族制度(長子雖然仍占優(yōu)勢,子女中的任何一人可以跟父母同居、繼承、傳承家業(yè))仍在持續(xù)的現(xiàn)狀清晰可見。在情緒方面,由于1950年代以后出生的少產(chǎn)少死世代的兄弟姐妹數(shù)量的減少和育兒期(與丈夫)的同居率的低下,妻子和妻方親屬之間的緊密交往、援助情況日趨活躍的傾向得到確認(rèn)。但這并非源自制度上的變化。在情緒方面,日本親屬本來就具有雙方性的特征。可以說時至今日這種基本特征仍沒有變。
亦即:戰(zhàn)后日本的親屬在制度的側(cè)面沒有變化,在情緒的側(cè)面表現(xiàn)得更加活躍,應(yīng)當(dāng)予以關(guān)注。本書揭示了戰(zhàn)后日本的家族、親屬關(guān)系,在經(jīng)歷了高度經(jīng)濟成長期以來的工業(yè)化、都市化、現(xiàn)代化的當(dāng)代日本社會,人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仍然經(jīng)營者直系家族制度,在情緒的側(cè)面呈現(xiàn)活躍化,構(gòu)筑著重視夫妻雙方任何一方的非父系、雙方的親屬關(guān)系。
本書由兩部分構(gòu)成。第一部是對核家族化和雙系化的通論進行探討。第1章將“家”到核家族的變遷從與家族、親屬的法律制度的變遷的角度進行探究,思考從親子關(guān)系到迫使家族、親屬關(guān)系發(fā)生變化的可能性。接著第2章與第3章分別從家族社會學(xué)和社會學(xué)鄰近的學(xué)科分野對家族、親屬的變化進行評論。在此基礎(chǔ)上,第4章以將家族、親屬的制度性側(cè)面和情緒性側(cè)面結(jié)合起來為必要條件,從“時間的相位之下”和“空間的相位之下”接近本書的課題,并分析從孩子之角度見與“實親”和“義親”的關(guān)系,介紹這種研究方法和角度。第二部對是否發(fā)生核家族化和雙系化,用數(shù)據(jù)來進行驗證。第5章關(guān)注日本社會持續(xù)存在的直系家族性要素,即關(guān)注擁有家族的制度性側(cè)面,弄清同居、繼承、相續(xù)的現(xiàn)狀,揭示直系家族制度存續(xù)的可能性。第6章檢視今天日本的家族、親屬關(guān)系的實態(tài),同時對家族的制度性和情緒性的雙方都予以關(guān)注,驗證在同居、援助、會話過程中兄弟姐妹間的差異,探索直系家族制度與雙方親屬制度共存的可能性。緊接著第7章闡明家族、親屬關(guān)系的歷史性變化。關(guān)注子女與父母同居得到育兒方面的援助情況的歷史性變化,通過比較不同出生年齡層的親子關(guān)系,揭示直系家族制度和雙方親屬制度的存續(xù)以及后者的活躍化現(xiàn)狀。第8章為了清晰地呈現(xiàn)日本的家族、親屬關(guān)系的特征,特別對同為儒家文化圈的日中韓三國親子關(guān)系的異同進行關(guān)注,對夫方與妻方以及兄弟姐妹間的關(guān)系進行比較,凸顯了日本的家族、親屬是直系制家族,非父系性、雙方性親屬制度的特征。在《終章》里,以本書通過分析得出的結(jié)果為基礎(chǔ),整理戰(zhàn)后日本的家族、親屬關(guān)系的變化,嘗試描繪新型的家族、親屬鏡像以及至今為止的日本家族、親屬發(fā)展軌跡。在最后的《補論》中記載了從墳?zāi)沟睦^承意識看與祖先祭祀有關(guān)的分析結(jié)果。因考慮到祖先祭祀的繼承意識同為制度性側(cè)面中的一環(huán),為增強本論的說服力收錄之。
[注:三峽大學(xué)青年科學(xué)基金, KJ2014A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