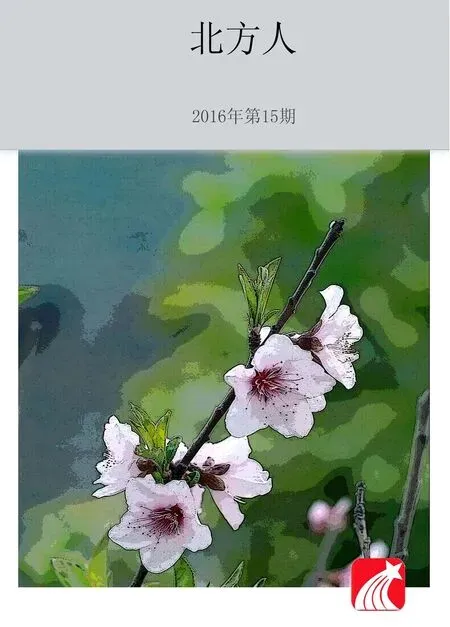中國古今地名緣何善變
文/郭曄旻
中國古今地名緣何善變
文/郭曄旻

近來,因安徽省黃山市是否應該恢復古稱“徽州”,在網上引起熱議。其實,黃山(徽州)名稱的變化,只是古今地名變遷的一個縮影。中國固然也有如同“永恒之城”羅馬一樣建成之后兩千多年名稱不變的地方(譬如無錫),但更多的地方在歷史長河中已是數度易名,這又是怎么回事?
從上海灘的“南京”路說起
眾所周知,上海市區的路名基本來自全國各地的地名。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被稱為“中華第一商業街”的南京路。南京路的路名顯然是來自“南京”這個地名,但以“南京”這個地方命名的上海馬路卻遠不止這一條“南京路”。這是因為上海站南廣場口的一條馬路大名就是秣陵路——早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分天下為郡縣的時候,今天的南京所在就是秣陵縣。
到三國時期,孫權將東吳統治中心遷到秣陵,在此筑起石頭城,又取“建功立業”之意將其更名為“建業”,而現在的浦東,也可以找到這條“南京”路——建業路。三國一統之后,在西晉征服者的眼里,“建業”的內涵就有些政治不正確了,于是改成同音的“建鄴”。因為西晉的末代皇帝叫司馬鄴,為了避諱,此地再度更名為“建康”,雖然與“建業”一樣都是佳名,但“建立安康之地”與“建功立業”的雄心相比,偏安之心已是不言而喻。
東晉南朝都以建康為都,江東王氣,三百年終。隋滅南陳,自然也容不下“建康”之名,遂以“江外安寧”之意貶為“江寧”。于是,以南京為京城的政權滅亡后,江寧往往是來自北方的新統治者最中意的名字,隋代(滅陳)、宋代(滅南唐)、清代(滅南明)俱是如此。
南京在歷史上的名字變化或褒或貶,根本源頭在于統治者的好惡。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隋滅陳后將富麗堂皇的南朝宮殿夷為平地,就是其中一例。同樣原因引發的地名變遷不惟南京,宋廷平定方臘起義之后,深恨江南百姓造反,古今藝術修養最高的皇帝宋徽宗遂在地名上做文章。方臘的兩個活動區域,歙州被改成徽州,取的是“徽”的本意“捆綁束縛”;睦州則被改成嚴州,意思更是不言自明的。相比之下,朱元璋為避國號諱,取“海定則波寧”之義將明州改成寧波,顯得已是很“友好”了。
越變越小的“州”
話說回來,上海灘的“南京”路雖多,卻未能窮盡歷史上的南京名稱。758年,唐代以江寧位置重要,取“升平之地”之意改置“昇(“升”的繁體字)州”,但如今滬上并無“昇州路”(不過南京還有)。再說到“昇州”之“州”,在中國的地名變遷里實在是個有趣的物事。自古就有九州的說法,但“州”真正在政區里出現則要到漢代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正式在全國范圍內推行郡縣二級政區制度,漢代因之。西漢武帝創立十三州,作為監察區域;至東漢靈帝時,黃巾軍起,南陽太守劉焉“以為刺史威輕……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于是改州刺史為州牧,并行使行政大權,地方政區亦由此變成了三級制,劉表是荊州牧,劉備是豫州牧,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例子。此時的“州”幅員廣大,譬如蜀漢一國,其實只及漢代的一個益州,換句話說,諸葛亮以丞相兼領益州牧之后,后主劉禪確實也沒啥事可做了。
可能出于限制州牧權力這個考慮,加上國家分裂,割據政權各行其是(譬如三國魏吳都設荊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州越來越多,轄區倒是越來越小,到南北朝末年,北周和南陳加起來,居然已經有253個州,而下一級的郡不過698個,基層的縣亦只有1562個。這實在是機構臃腫到不能不改的地步了,隋代平陳后罷天下諸郡,等于是把州降級到原來郡的地位,隋煬帝干脆又把州改名為郡,繞了一圈又回到秦代的老路上去了。唐代沿襲隋制,但中央直接管理幾百個州實在過于困難,唐太宗就苦于記不住各地長官名字而將其寫于屏風之上,中唐之后,遂又變成道州縣三級體制。雖然州在唐代的地位下降,但對中國地名卻影響深遠。不像秦漢的郡名毫無規律,唐代州名整齊劃一,一律是單字加州,許多名字今天也是廣為人知的。
但唐代的州制也有例外,自從開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把國都雍州(今西安)升為京兆府,把陪都洛州(今洛陽)升為河南府后,“府”儼然就成了擁有特權的州。到宋代就出現了“州郡之名,莫重于府”。府都由州升遷而成,等級均為上州;比如南宋的“行在”杭州升為臨安府。好名字自然人人向往,于是府就變得越來越多,到明清更是成為主流,故此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諺語。
都是附郭縣惹的禍
明清時期,地方行政基本是省-府-縣三級。通常一個府轄有數個或十數個縣,其中府城所在縣稱為“附郭”,比如寧波府的附郭縣是鄞縣,蘇州府的附郭縣則有吳、長洲、元和三個之多。附郭縣令知縣和知府在同一座城里,一舉一動,都要受到牽制,所謂“趨蹌倥傯,供億紛紜,疲于奔命”,以致有“三生不幸,知縣附郭”的說法。
正是附郭縣的存在,久而久之,府名所指對象也開始變化。一方面,它仍然指的是整個府所轄區域,比如明清時期廣為詬病的“蘇松重賦”,指的就是蘇州府與松江府(相當于今上海市與蘇州市),而揚州府興化縣人鄭板橋也算在“揚州八怪”里。但另一方面,有時府名所指僅是附郭縣而已,譬如晚清的《海陬冶游錄》記載當時的上海青樓,“以蘇常者為佳,土著次之,維揚江北,又其次也”,其中的“蘇”指的就是蘇州府的附郭吳縣(及長洲、元和)與同屬蘇州府的“常”(常熟)相對。
更大的變動來自“市”的出現。近代城市的產生和發展,必然要求行政管理和行政建制與之相適應,即從“城鄉合治”走向“城鄉分治”。1926年,廣州借鑒西方城市體制頒布實行《廣州市暫行條例》,規定“廣州市為地方行政區劃,直接隸屬于省政府,不入縣行政范圍”。隨著《上海特別市暫行條例》和《南京特別市暫行條例》的公布,至1927年出現了上海和南京兩個直屬于國民政府的直轄市和廣東省轄的廣州市,初步形成了城市型政區的體系。
新中國成立后,逐漸形成了地級市管縣(及縣級市)的格局,此時的市實際已是一級行政區而非起初概念。淮安大概是最典型的例子,先是建國初期淮陰縣城析出清江市,1980年代,這個清江市升格為地級淮陰市,管轄原淮陰地區各縣。到2001年,淮陰市再度改名淮安市,清江市變成了清浦區,而舊淮安府府城淮安縣(山陽縣)則被改成楚州區,2012年又一變,楚州區又成了淮安區,實在令人眼花繚亂。
雖然現今的地級市幅員顯得與舊時的州府頗為接近,但畢竟時過境遷,即使現今熱議的安徽黃山市,其實與古代的徽州府也已不是一回事了。舊徽州府的六縣,績溪現屬宣城市,婺源更是別屬江西省,而黃山所在的黃山區(原名太平縣),古時卻不屬于徽州府(屬寧國府)。從這個角度而言,經歷物是人非的變遷之后,倒也不能簡單說黃山市應當“復名”徽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