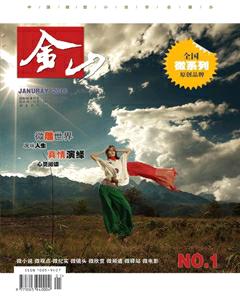打錯了
電話鈴響的時候,陳熙躺在床上看天花板。電話是吳麗嫦打來的。吳麗嫦約他到“利舞臺”去看5點半那一場的電影。他的情緒頓時振奮起來,以敏捷的動作剃須、梳頭、更換衣服。更換衣服時,噓噓地用口哨吹奏《勇敢的中國人》。換好衣服,站在衣柜前端詳鏡子里的自己,覺得有必要買一件名廠的運動衫了。他愛麗嫦,麗嫦也愛他。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到婚姻注冊處去登記。他剛從美國回來,雖已拿到學位,找工作仍須依靠運氣。運氣好,很快就可以找到;運氣不好,可能還要等一個時期。他已寄出七八封應征信,這幾天應有回音。正因為這樣,這幾天他老是呆在家里等那些機構的職員打電話來,非必要,不出街。不過,麗嫦打電話來約他去看電影,他是一定要去的。現在已是4點50分,必須盡快趕去“利舞臺”。遲到,麗嫦會生氣。于是,大踏步走去拉開大門,拉開鐵閘,走到外邊,轉過身來,關上大門,關上鐵閘,搭電梯,下樓,走進大廈,懷著輕松的心情朝巴士站走去,剛走到巴士站,一輛巴士疾駛而來。巴士在不受控的情況下沖向巴士站,撞到陳熙和一個老婦人及一個女童后,將他們壓成肉醬。
電話鈴響的時候,陳熙躺在床上看天花板。電話是吳麗嫦打來的。吳麗嫦約他到“利舞臺”去看5點半那一場的電影。他的情緒頓時振奮起來,以敏捷的動作剃須、梳頭、更換衣服。更換衣服時,噓噓地用口哨吹奏《勇敢的中國人》。換好衣服,站在衣柜前端詳鏡子里的自己,覺得有必要買一件名廠的運動衫了。他愛麗嫦,麗嫦也愛他。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到婚姻注冊處去登記。他剛從美國回來,雖已拿到學位,找工作仍須依靠運氣。運氣好,很快就可以找到;運氣不好,可能還要等一個時期。他已寄出七八封應征信,這幾天應有回音。正因為這樣,這幾天他老是呆在家里等那些機構的職員打電話來,非必要,不出街。不過,麗嫦打電話來約他去看電影,他是一定要去的。現在已是4點50分,必須盡快趕去“利舞臺”。遲到,麗嫦會生氣。于是,大踏步走去拉開大門……
電話鈴又響。
以為是什么機構的職員打來的,調轉身,疾步走去接聽。
聽筒中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
“請大伯聽電話。”
“誰?”
“大伯。”
“沒有這個人。”
“大伯母在不在?”
“你要打的電話號碼是……”
“3——975……”
“你想打九龍?”
“是的。”
“打錯了!這里是港島!”
憤然將聽筒擲在電話機上,大踏步走去拉開鐵閘,走到外邊,轉過身來,關上大門,關上鐵閘,搭電梯,下樓,走出大廈,懷著輕松的心情朝巴士站走去。走到距離巴士站不足五十碼的地方,意外地見到一輛疾駛而來的巴士在不受控制的情況下沖向巴士站,撞倒一個老婦人和一個女童后,將她們壓成肉醬。
(1983年4月22日作,是日報載太古城巴士站發生死亡車禍)
【賞析】香港老作家劉以鬯先生在其主編的《星島晚報》副刊《大會堂》上,發表了這篇新穎別致的微型小說。它用富有凝重韻味的復合結構方式,表述了一次偶然車禍的巧合,寓含著“生命在于瞬間”的藝術意蘊,暗示出人生中偶然的因素也可以決定著一個人禍福和命運的哲理。巧合,是巧在偶然的相合上,或者說,是一種“相合”的偶然。它是小說創作中情節布局的一種重要的藝術手段,所謂無巧不成書。它有利于小說新奇、生動、獨特情節的創造。微型小說《打錯了》的情節開展中,也巧妙地運用了此法。兩則故事都充分運用了巧合的藝術手法,并前后作了比較,前者的巧合,陳熙命歸黃泉;后者的巧合,陳熙逃過一劫。這里,這個偶然性因素就是時間上的誤差。時間,是微型小說的重要因素,因為它是“時間的藝術”。英國作家伊麗莎白·鮑溫在《小說家的技巧》一書中精辟地指出:“時間是小說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我認為時間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時間的巧合,正是小說家經常運用的技巧,敷演出新穎生動的情節,表現出人物的鮮明個性和不同的命運。本文正是利用“打錯了”這個偶然插入事件,對時間作了重新的調整和分配,才產生死與生兩種不同的結局,可見,事件的巧合在這里扮演著何等重要的角色。
當然,巧合的偶然性,也要符合“會有的實情”這樣的可能性與或然性,不能胡編亂造,弄巧成拙,變成不合情理的虛假文字。
(凌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