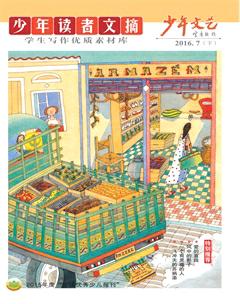青年的責任
蔣方舟
14年前,剛剛退學的韓寒,帶著自己剛剛出版的《三重門》參加央視的《對話》節目。
錄制過程中,主持人咄咄逼人,社科院的專家認為韓寒只是曇花一現,一個扎著麻花辮的女觀眾說他是“土雞”——因為他用聊天室聊天,而不是像她一樣用OICQ和ICQ。甚至,為了反襯韓寒的失敗,他身旁安排了一個成功的范本——考上北大的少女黃思路。
14年后,我去參加央視一檔節目的錄制——“非一般年輕人”的演講,其中大部分是90后,有科學家,有創業者。
演講者都朝氣蓬勃,而我和一群從30后到80后不等的老年人,坐在觀眾席中架得很高的凳子上,腳不著地,舉著一塊寫有自己出生年份的熒光板,帶著慈祥的笑容,聽這些年輕人演講。
當年《對話》節目中的老年人是專家,是年輕人的批評者,而我們這群老年人,卻是年輕人喪心病狂的贊美者。
我們在每個演講之后發言,每個人都生怕溢美之詞被他人搶去,抱著話筒無休止地進行排比句造句:“青春是一顆種子一朵花一棵樹一根蠟燭……”最后聲嘶力竭地以諸如“青春無敵!做你自己!”作為結束,非常累。
那次錄制,我印象最深的是某個應用軟件的CEO,90后,非常瘦小,抱著一個大狗熊玩偶上臺,把狗熊扔到地上,說:“我覺得讓我抱熊的導演特別傻。”
他的演講不乏豪言壯語,例如“明年給員工派發一個億利是”之類。而臺下的大學生,凡聽到“第一桶金賺了100萬”、“阿里巴巴用千萬美金收購”這類句子,都羨慕地齊聲嘩然。
他的演講充滿了明顯的夸大和對他人的不屑,卻獲得了那天最熱烈的掌聲、最熱烈的溢美。
前輩們之所以興奮,在于終于找到了心目中典型的90后——年輕的CEO符合社會對90后的一切想象:輕狂、自我、混不吝。
節目播出后,他的演講視頻在社交網絡上風靡,配著這樣的標題:“90后的話,惹怒所有的互聯網大佬”;“90后的一番話,讓全世界都沉默”。
而播出的節目里,所有被輕視的中年人都大力鼓掌、賣力歡笑,我忽然想到14年前韓寒節目中的那些中年專家,他們依然怒不可遏嗎?還是舉著寫有自己出生年份的牌子,一聽到“追逐夢想”、“初生牛犢”之類,就在煽情的音樂中熱烈鼓掌?
風水輪流轉,中年人在話語權的爭奪中成了弱勢群體。
不久前,北大教授錢理群宣布“告別”——告別學術界,告別年輕人——此前他一直與年輕人為伍、為師。
他以驚人的真誠與坦率這樣寫道:“對60后、70后我有點理解,80后多少有點理解,對90后我完全不理解。網絡時代的青年的選擇,無論你支持他、批評他、提醒他都是可笑的,年輕人根本不聽你的。所以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師的角色,我必須結束。最好是沉默地觀察他們。”
可大部分中年人,依然在吃力地解析青年人。
“年輕人”的形象被廣告公司和商家以動畫、PPT、視頻等種種工具描繪:青春、朝氣、夢想、活潑。PPT里的年輕人,穿著褲襠快貼到地上的牛仔褲,戴棒球帽,腦袋上掛著一個巨大的耳機,背景板上是二次元的漫畫和已經過時的火星文,配以凜冽的潑墨字體:“我就是我!”“我就是任性!”“青春無極限!”
討好年輕人,成了社會的通病。
一方面,青年是巨大的消費群體,他們對文化產品和商品的喜新厭舊與選擇,會對市場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所以商家和媒體企圖用文案大號加黑的網絡流行語,來拉近和年輕人的距離,忽略了網絡流行語已經令人深惡痛絕的事實。
中年人對年輕人毫無原則地贊美,一方面要證明自己未老,一方面大概出于愧疚:沒有為下一代建設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
不久前,“少年不可欺”成為互聯網上熱烈討論的事件——視頻網站巨頭優酷,剽竊了幾個少年的創意。所有人都聲討優酷,不僅是為少年鳴冤,而且因為自己年輕時也有不被重視的經歷。
70后、80后都有過急于獲得認可的青年時期,因此,90后甫一出生就被認同。
作家阿城卻認為:“中年時便認認真真地做一個中年人,為家庭為國家負起應負的責任,非要擠進青年行列,胡子刮得再干凈也仍有一片青,很尷尬。”尊重年輕人與討好年輕人,只有一線之隔。而年輕人將要生活的時代,會因為贊美和認同,就變得更好么?
高校是勵志演講者聚集的地方,年輕人激動地在本子上寫下“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所有人都念叨著馬云的語錄:“夢想是要有的,萬一成真了呢?”汪峰坐在轉椅上,像從阿拉丁神燈里冒出來一樣問道:“你的夢想是什么?”好像你只要敢說,他就能讓你實現。
打開電視或網頁,你會發現滿世界都是“夢想成真”的人:歌唱比賽得了冠軍,創業獲得B輪融資,環球旅行,等等。整個社會熱情地向你伸手,邀你做夢。
時代永遠給年輕人機會,但是,只給一小部分年輕人機會。時代只允許小部分人成功,而讓大部分人像亨利·梭羅所說的那樣——“處于平靜的絕望之中”。
夢想泡沫下的世界,并不是薔薇色的。一代代青年的責任,是從時代中獲益,并改造出一個更好的世界來。如果失敗,下一代再來。
(摘自《新華日報》2015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