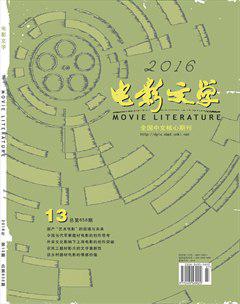彼得·格林納威電影作品的美學意蘊
[摘 要]彼得·格林納威既可以被看作是西方混合藝術領域的開路先鋒,同時也被認為是實驗電影領域的領路人。先鋒性和實驗性再加上其后現代主義的懷疑氣質,使得其作品更加脫俗、自由、新穎,并具有一種持續生長和流動的美感。本文從彼得·格林納威電影作品的敘事結構——根莖圖式、電影影像符號與格氏的“私人百科全書”以及歷史文化角度對彼得·格林納威作品進行深入分析,探討后現代主義的電影美學內涵。
[關鍵詞]后現代電影;百科全書;根莖圖;歷史;媒介
提起后現代電影中最有名的實驗者和先行者,我們不能不提起那位聞名遐邇的英國導演——彼得·格林納威。作為非常有名的當代電影語言導演、一個電影理念先鋒前衛,他總是顯得那樣“與眾不同”——一方面,他敢于創造性地運用電影語言;另一方面,他因不少“出格”的做法而飽受業內外的爭議。整個全球影壇常常為這個“怪才”的種種行為而震撼:他的作品所選取的題材總是那樣怪誕離奇;他的電影中的影像語言又是那樣窮工極態。他的電影作品體現的情緒總是那樣特別:其中既有自我指涉性情緒和質疑權威性情緒,也不乏懷舊非鄉愁氣質情緒,甚至還有無法解決的矛盾性情緒。“格氏”(指“彼得·格林納威”,下同)的一種新的電影敘事結構——根莖圖式是這樣創建的:在對電影的敘事時空進行增加和拓寬時,電子科技的作用在他那里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有了對于橫向的電影敘事進行驗證的基礎,他開始涉獵非敘事性電影。將電影當作百科全書的格氏在對符號王國進行構建時大膽地運用了漂浮影像能指。無論是對于理性社會的權威性和決定論,還是統一、霸權的文化意識形態,在他眼里都不值一提。為了追求真實歷史的嚴肅性,格氏在編著歷史時運用了諸如多元藝術之類的媒介。在分析格氏相關作品的同時,這篇文章所聚焦的后現代主義的電影美學的含義,向傳統的電影語言提出了大膽的挑戰。
一、私人百科全書和影像符號
無論是知識系統,還是審美觀以及道德價值觀,在后現代主義的視域里,都無一例外地具有“三大性質”。 其性質之一是“虛幻性”;其性質之二是“誘惑性”;其性質之三是“穩定性”。之所以如此,和“三大主義”即“人本主義”“求證主義”和“理性主義”有密切關系。這是因為,我們所說的“現代文明體系”,就是由這些存在普世性價值共識的“三大主義”所構成的,并經常被業界所詬病。對于現代主義將多元話語認作是社會組成結構的觀念,格氏并不贊同。他的作品都具有“私人百科全書”這一特征。為了達到觀眾無從找尋熟悉的話語意義和語義之目的,格氏的觀點是:就得讓他們在符號世界里迷失。所以,他對全部理性的整體話語和有機話語進行了轉變,讓這些話語不再起任何作用。對于影像符號的結構,格氏一直在探索;無論是對于人類可能或未知的認知,還是對于人類社會的無限多樣性,他都毫無例外地借助于戲仿策略予以大膽揭露。他的觀點是,無論是事物還是生活,都會有很難理解的地方。其直接結果就是,某些事物和生活是不能索引取證的,因而要還原其原意義和真實也是不可能的。
正是“漂浮能指”成了格氏的“私人百科全書”的源頭活水。在能指的情況下,影像所指之所以能夠做到不斷變化,導致意義變得無法閱讀這一結果的出現,就是因為他熟練地運用了字母符號和數字符號。他的影片作品——不管是《親愛的電話》,還是《崩潰》,抑或是《逐個淹死》,都無一例外地含有數字符號,也就是所謂的“漂浮的能指”。上述第一部作品就有著14位虛構人物,第二部作品就記錄了92位幸存者,第三部作品則將數字1~100作為影片的計時器。對于這些數字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人們都沒有辦法確切知道。就“能指”和“所指”的關系而言,在任何單獨的符號中都無法存在的“所指”的事實導致了前者不包括后者。這在《一加二的故事》和《H代表房子》這兩部作品中都得到了體現。誰能說清楚上述作品中不斷重復命名26個字母的游戲代表什么呢?米特里的觀點是:那些由理據性關系構成的既定體系,在電影中,是跟語言有差異的。因為影片邏輯具有日常邏輯中提煉出來的特征,運用別的邏輯進入的領域只能是既不常見,也不可能。實際上,拓展出跟傳統影像符號不一樣領域的格氏正是處于這樣的境地。
百科全書,在一般人的眼里,常常被認為是可以做到揭示整個世界,就像地圖一樣。分析《崩潰》這部作品,可以發現,為了使得作品有一個條理清晰的完整結構,對于敘事段落,作者大膽地借助了92個以黑色姓名和白色數字為標題這一方式進行細致論述。我們不難看出,格氏的私人百科全書的基礎比較特別:作為持有批評距離的一種重復行為,其認知模式是屬于戲仿理性的。這樣做的結果是,為了充分做到彰顯其正中心,格氏的作品在語氣上使用反諷。另外要說明的是,我們可以從《逐個淹死》這部格氏對1~100的數字構成的三個類別進行講述的電影作品看出:具有不斷浮動這一重要意義的,不光是那些既條理不清又怪異搞笑的所指符號所具有的特性,同時也是那些規則嚴謹、仔細嚴厲的能指符號所具有的特性。作品中,上述的三個類別中的前兩個在數字排列組合時所采用的標準全是“種”。考慮到附于數字1~100上的事物語義上沒有什么聯系,顯得任意而不規則,導致了同種數字不存在的這一事實,對于第三個類別,格氏對規則進行了大膽的變更。通過變革,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使得該劇給人一種“陌生的熟悉感和疑惑的知道的感覺”。
格氏的戲仿策略的效果是雙重的:其一是他本人對模式和結構的迷戀彰顯了出來;其二是他對于一統化的先驗模式既嘲笑又批判的鮮明態度也彰顯出來了。為什么要借助于數字和字母,對目前的世界體系進行辛辣而無情的諷刺呢?格氏目的就是要對在實踐假設基礎上建立的思維模式進行揭露。通過和經驗主義的對峙,格氏告訴人們一個深刻的道理:事實存在的事物和人們直觀看到的東西之間是有距離的。
二、電影敘事和根莖圖
后現代主義電影敘事的主要特征體現為兩大方面。第一大方面是對于電影敘事作品中的各矛盾層面和它的復雜性進行了最大限度的保留。無論是將敘事作品設計成具有連貫性的作品,還是將它設計成具有穩定性特征的作品,格氏都持激烈反對的意見。這是后現代主義電影敘事主要特征的第二大方面。將在各點位置開裂的無中心根莖圖既可以倒置,也可以組裝。無論是哪個方向的開放樹形圖,經過一定的演變,都可以最終形成小的根莖圖。通過對《枕邊書》的細致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格氏把根莖圖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他既做到了對于敘事電影的解放,也做到了對于敘事張力的激發,還做到了對于開放式、多元化和無中心的敘事結構的構建。
這里,我們不妨對根莖圖的各種敘事特點做一具體的闡述:
第一個敘事特點在于根莖圖對于傳統敘事電影敘事結構對于不同時間緯度處理方法的顛覆。這跟根莖圖的特點,也就是其所具有層疊相交的敘事結構,有密切關系。一方面,經緯交錯的結構促使敘事因果進行線性發展。另一方面,敘事時空既能夠相互合并,也能夠穿越,還能夠重疊。這就使得一方面全部的事件在一樣的經度上持續發展都可以得以實現;另一方面,一樣時空的事件也能在緯度上持續地延伸和發展。
第二個敘事特點在于根莖圖對于傳統敘事電影敘事結構對于相同時間緯度處理方法的顛覆。也就是說,與傳統的單向敘事的敘事結構不同,根莖圖可以做到對于既無中心又多元化的敘事時空結構的構建。一個新的敘事時空產生了,因為無論是線性的時空,還是一統化的時空,都被根莖圖所打破了。要使得觀眾既在尷尬狀態接受作品,也在模糊的狀態下接受作品,就要有一種共時、多重時空的敘事結構出現。其前提條件就是無中心、多元化的全新敘事網絡的構建。
第三個敘事特點是根莖圖對于傳統敘事電影在時空結構上的相對開放性。這種開放性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根莖圖在某個點處被中斷和瓦解,另一方面,根莖圖又順著自身管線重組,甚至恢復。對于敘事結構,這種任意性體現了三大方面:第一方面是其分散性,第二方面是其不穩定性,第三方面是其不可預測性。
三、歷史書寫和媒介表征
關于歷史敘事如何對原來的史實進行重大意義的賦予,格氏所持的觀點是:一方面,歷史敘事隨著個人經驗價值變化而變化;另一方面,歷史敘事隨著個人的接受和闡釋變化而變化,這就導致了歷史往往表現為漂浮不定這一現實。在這種觀點支配下,他對歷史事件中具有選擇性特點的情節結構進行了提取,通過整理成電影故事的形式,對歷史進行書寫。以此為觀點背景下的格氏歷史書寫不可避免地表現出矛盾性。一方面,格氏借助了一系列史料,包括黑白影像等,給觀眾以絕對真實的感覺;另一方面,他對于書寫的歷史痕跡的充分展示,給觀眾的感受是,這種呈現出來的東西在真實性方面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首先,對于歷史痕跡的展示,毫無疑問,應該是歷史書寫過程的第一件大事。后現代主義對于歷史敘事是否合法有明確的看法。那就是,能做到對于歷史真相進行揭示的事物,除了那些通過表征事件的歷史痕跡之外,就是那些通過表征事件的文本化材料。與此不同的是,格氏往往在其敘事空間以歷史事件為背景的,著重于對重現歷史錯覺的營造造成了兩種結果:其一是真實的頭銜冠上了虛構文本;其二是對于無中生有的嫌疑的逃脫。在此觀點支配下,他的電影作品中有著諸如書信、黑白紀錄片和地圖等大量史料。
其次,無論是對于歷史痕跡的組建,還是對于歷史痕跡的命名都得依靠影像媒介表征進行。格氏指出,無論是歷史的意義,還是歷史的真相,都不是處于歷史痕跡之中的,而是在其特定的表征方式里面的。我們不能認為歷史書寫與在線性層面上重現因果鏈條事件有什么必然的聯系。作為一種重組活動,它是將脫離語境的材料置于特定語境中得以完成的。無論是編輯的操作過程,還是重組的操作過程,人們不必要有任何的遮掩或是掩飾的舉動。為了達到對影像媒介超媒介性的充分展現,格氏在影像處理上采用了媒介融合做法和多重畫面疊做法。對于直感性和超媒介性這兩個對立的概念,我們是這樣理解的:為了達到為觀眾營造身臨其境的感覺效果的目的,前者起到了消除媒介介質的存在感的效果,也就起到了使作品介質透明化的作用。萬維網網頁、超鏈接、界面及電子游戲等典型代表的是后者,對于表演和過程起到著重強調的作用。無論是對于承上啟下的敘事結構,還是對于讓觀眾處于線性發展、邏輯清晰的敘事空間中的做法,以后者為特征的電影屏幕都是持排斥態度的。
最后一點必須提出的是,借助于后現代游戲精神的支撐,格氏將歷史敘述注滿了想象力和創造力。我們不妨以其代表作《塔斯魯波的手提箱》為例說明這個問題。一方面,借助于混合模擬以及歷史的真實情形,格氏將歷史當作一種既具有開放性,也具有持續變動性,還具有多樣性的事物。另一方面,借助于對不連續體和一系列事態的巧妙利用,對于既具有局限性,也具有偏執性,還具有反神話特征的歷史進行了重寫。
四、結 語
縱觀上文,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以電影選材的跨度較大著稱的彼得·格林納威既可以被看作是西方混合藝術領域的開路先鋒,同時也可以被認為是實驗電影領域的領路人。作為先行者,格氏大膽地將新媒體元素融入他的電影作品之中。既給人們以持續生長的美感,也給人們以流動的美感的格氏電影作品是那樣別具一格。他的作品之所以既顯得脫俗,也顯得自由,還顯得新穎,不但跟其中顯現出來的先鋒性有關,也和其中較強的實驗性有關。
[參考文獻]
[1]王春平.顛覆與背離 反觀與審視——后現代主義電影美學意蘊探究(上)[J].藝海,2009(08).
[2]劉哲含.媒介融合與敘事轉型[D].重慶:重慶大學,2013.
[3]孫琪.電影邊界的行走者——彼得·格林納威作品研究[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15.
[4]王珺,李冀.論現代電影的媒介間性[J].創作與評論,2014(20).
[5]潘秀通,潘源.后現代電影的當代語境及當代性表征[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01).
[作者簡介]劉俊杰(1980— ),女,河南鞏義人,碩士,周口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學及英語教育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