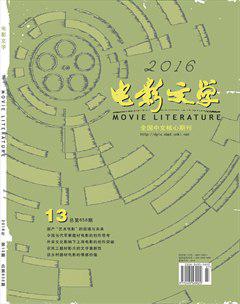今村昌平電影的“底層敘事”研究
[摘 要]今村昌平于20世紀20年代出生在日本東京的一個普通家庭,在不足20歲時便承擔起了家庭生活的重任,這一經歷也成為這位著名的日本電影導演在日后指導影片過程中關注底層民眾生活的重要現實基礎,正是對底層民眾生活的關注使今村昌平成為第一位兩次榮獲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的日本導演。本文將以今村昌平代表性影片中的“底層敘事”為視點,以“食”本能和“色”本能為切入點,對今村昌平電影中的“底層敘事”進行研究。
[關鍵詞]今村昌平;電影;底層敘事;“食”;“色”
一、今村昌平其人其作
今村昌平出生于20世紀20年代日本東京的一個普通家庭之中,父親憑借經營診所來支撐一家人的生活,在今村昌平少年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的兩位兄長均被迫加入了日本侵華戰爭并再也沒能返回日本。與此同時,戰爭影響著日本國內民眾的生活,今村昌平父親診所的倒閉使整個家庭陷入困頓,為了養家糊口,今村昌平在不足20歲時便承擔起了家庭生活的重任,這一經歷也成為這位著名的日本電影導演在日后指導影片過程中關注底層民眾生活的重要現實基礎。20世紀中葉,今村昌平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后便進入松竹公司擔任助理導演。1958年,今村昌平的處女作《被偷盜的情欲》上映,隨即引發了日本電影界的關注。此后今村昌平的電影之旅真正拉開帷幕,在20世紀60年代至21世紀初這段時間內,今村昌平先后執導了《日本昆蟲記》《紅色的殺機》《諸神的欲望》《復仇在我》《楢山節考》《女銜》《黑雨》《鰻魚》《赤紅色的暖流》《九一一事件簿》等多部馳名世界的影片,其中由左幸子主演的影片《日本昆蟲記》憑借獨特的女性故事而獲得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金熊獎提名,也使世界影壇開始關注這位東方導演。[1]此外,《楢山節考》《女銜》《黑雨》等影片還榮獲戛納國際電影節、威尼斯電影節、柏林國際電影節、法國電影凱撒獎、釜山國際電影節、日本電影學院獎等多項大獎及提名。2006年,79歲的今村昌平因病在東京逝世,結束了自己的電影之旅。
正如上文所述,今村昌平曾榮獲戛納電影節的金棕櫚獎,事實上,他是日本電影發展史上第一位兩次獲得此項殊榮的導演,也是世界范圍內第四位兩度折桂金棕櫚獎的導演,由此可見世界影壇對今村昌平及其影片的充分肯定。法國的文化部負責人曾在接受媒體采訪的過程中坦言,今村昌平是日本電影史上最為鮮活的傳說。今村昌平之所以在世界影壇獲得了如此之高的評價,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對日本電影傳統的反叛及其對日本社會現實的批判,這一言說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當時西方影壇盛行的新現實主義之風,所謂新現實主義主要是反叛傳統、拒絕溫情和洗禮批判,從這一層面觀之,今村昌平是一位獨樹一幟的日本導演。相比之下,由于對社會歷史現實的犀利批判以及對日本政府的直接指責,今村昌平在日本影壇并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其秉持的深度批判之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進一步遭遇了冷落。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戰敗的陰霾彌散在日本境內,極端的享樂主義也成為日本民眾逃避現實的重要手段,這種享樂主義在電影領域的主要表現就是不斷強調影片的娛樂性。據不完全統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兩年間出品的本土電影有19%以上為缺乏深度內涵的娛樂電影,由此可見今村昌平的新現實主義影片受到了冷落。但隨著歷史的洗禮,今村昌平的影片卻在日本電影史上乃至世界影壇上獲得了越來越高的評價。[2]本文將以今村昌平代表性影片中的“底層敘事”為視點,以“食”本能和“色”本能為切入點,對今村昌平電影中的“底層敘事”進行研究。
二、今村昌平電影“底層敘事”中的“食”本能
正所謂“食色,性也”,在今村昌平的“底層敘事”中,我們能夠看到的是那些游走在社會生活底層的民眾,他們關于“食”和“色”的最基本的需求均無法得到滿足。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中,個體的需求被劃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3]在大多數呈現社會底層生活的日本電影中,導演關注的是底層生活中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難以滿足,真正致力于呈現底層民眾難以滿足的生存需求的日本電影卻并不多見,而今村昌平正是將“食”本能的呈現融入電影創作中的代表。
影片《楢山節考》是今村昌平創作于20世紀80年代的作品,當時日本的社會經濟已進入高速發展的階段,大部分民眾的生存能夠得到保障。即便如此,今村昌平依然深入到了日本社會的最底層,直面食不果腹的殘酷現實,雖然在《楢山節考》中,導演將故事背景設置為古代時期的日本山村,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關于“食”本能的探討對當時的日本社會也具有一定的影射意義。這部影片憑借新穎的題材和令人動容的故事背景包攬了日本電影學院獎的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多項重量級獎項和提名。在影片《楢山節考》的故事中,貧困的山村一直延續著活祭山神的習俗,用來活祭的對象就是村中六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年逾70的男人和年逾60的女人會被子女送到深山之中,以等待死亡的方式祭奠山神。事實上,這種祭奠并非單純地出自宗教習俗,更為根本的原因是這個山村極端貧困,沒有足夠的食物供養老人。由坂本澄子飾演的女主人公阿玲婆已經年近60,即將要走上祭拜山神之路的她并沒有為自己生命的終結而感到惋惜,而是擔心自己離去后兒子辰平與利助的生活。在幫助大兒子辰平續弦后,阿玲婆還為患有精神疾病的二兒子利助安排了一次云雨之歡,同時身體健朗、胃口不減的阿玲婆還磕掉了自己的門牙以示祭神的決心,甚至認為以身祭神就是村中老年人應盡的義務。影片著力刻畫了阿玲婆與大兒子辰平祭祀路上的一段故事,大兒子辰平背著自己的母親上山祭祀,面對著母子從此陰陽兩隔的事實,二人雖然心存傷感,但卻未過分悲痛。大兒子辰平甚至認為自己是完成山神旨意的仆人。在上山的路上,曾經的“祭品”,即村中的老人們的骸骨散落在山石之上。辰平將阿玲婆放置在了一塊較為干凈的石頭上便遵守著不回頭的傳統快速離開了,而此時阿玲婆的內心并無不甘,對于迫在眉睫的饑寒交迫以及生命終了坦然相對,甚至認為天降大雪表征著以身祭祀的成功和天神的恩賜。
在《楢山節考》中,村民們的生活都是圍繞著“食”本能展開的,無論是成為山神活祭的老人們,還是衣不蔽體卻終日勞作在田間的成年人們,他們所有的奮斗都是為了獲得有限的食物。即便如此,村中的生活依然是朝不保夕,難以吃上一頓飽飯,甚至經常以蟲子為食來維系生命。就最令人震驚的老人活祭而言,這些老人也是以自己的死換取了后代的生,當自己為“食”奮斗了一生后,不能再產生價值的老人便甘愿為后代節省食物,以祭神為名受凍受餓而死。由此可見,在這部影片中,今村昌平不僅對極端貧困的生存境況進行了披露,還對村中老人能夠摒棄“食”本能而換取后代生存可能的奉獻精神進行了贊揚。
在今村昌平的另外一部影片《二哥》中,導演為我們呈現了一家孤兒的故事。在影片主人公的父母死于礦難后,兄妹三人的生活陷入了朝不保夕的境地,缺乏責任心的大哥為了逃避撫養弟弟和妹妹的職責而將他們送給了同樣貧困的邊見源大叔。然而融入邊見源大叔的家庭生活并不容易,尤其是在邊見源大叔也死于礦難之后,兄妹二人更是遭遇了邊見源一家人的奚落和侮辱。為了擺脫這種侮辱,二哥帶領幼妹獨立謀生,但拼命工作的二哥并沒有改變自己和幼妹食不果腹的生存處境。在影片《二哥》中,我們在對個體“食”本能難以得到滿足的境況扼腕嘆息的同時,還看到了在苦難中奮力生存的兄妹形象,在“食”本能的刺激下,他們發揮出了與年齡不相適應的力量,其堅毅的品質值得贊揚。
三、今村昌平電影“底層敘事”中的“色”本能
在呈現“食”本能的同時,今村昌平還在影片中體現了個體的“色”本能,即對性的需求。在上文提到的影片《楢山節考》中女主人公的二兒子利助就在長期的性壓抑中走向了性倒錯,甚至為了滿足這一本能的宣泄需求而與動物發生性行為。這部影片所講述的是一個貧窮而落后的山村的故事,貧窮使村人難以撫養過多的子女,而落后又使他們沒有掌握避孕的方法,這使村中的許多居民均生活在性壓抑之下。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性一直被視為禁忌話題,即使是在思想相對開化的現代社會中,性也是較為隱私的存在,甚至會被所謂的道德衛士冠以骯臟、下流之名,[4]但是在今村昌平的電影中,性這一敏感的問題卻被導演自本能的角度加以闡釋。在今村昌平的另外兩部影片《日本昆蟲記》和《女銜》中,就放棄了以傳統的道德視角來書寫妓女的生活,從而為觀影者呈現出耳目一新的觀影體驗及深刻的思考空間。
影片《日本昆蟲記》上映于1963年,講述了女主人公富米的故事,富米是母親與父親忠次二人未婚先孕的女兒,23歲時,富米進入工廠工作,在一次被迫的性行為后,富米生下了女兒信子,信子出生后的第七年富米便將女兒寄養在娘家遠赴東京謀生。對于一位身無所長的女性而言,在繁華都市中謀生十分艱難,而富米也在來到東京不久后變成了依靠出賣身體謀生的妓女。在從事妓女這一行當的過程中,富米遇到了批發商人唐澤,為了長期占有富米,唐澤為其出資開設了一家妓院。雖然這使富米的生活逐漸脫離了貧困,但與唐澤之間沒有愛情的性生活卻使富米的“色”本能受到了壓抑。不久之后,違法開設妓院的富米被關進了監獄,而其女兒信子卻重復了自己的道路,為了籌集資金開墾荒地,信子成為唐澤的情婦。在《日本昆蟲記》中,我們看到的不是導演對道德淪喪的女性的批判,而是對“食”本能和“色”本能的審視,這兩種個體的本能在妓女富米身上同時得到了體現,滿足他人的“色”本能成為妓女富米實現自身“食”本能的途徑,而自身的“色”本能卻難以得到實現。在影片《女銜》中,今村昌平依然書寫著日本妓女的故事。影片男主人公村岡伊治平在20世紀初來到了香港,并跟隨上原大尉輾轉至當時的奉天,在日本人開設的妓院中利用妓女探聽俄國的軍政情報。在此期間,一位受村岡伊治平指使的妓女阿留被俄國人公開處死,但這并沒有使村岡伊治平對自己將女性視為發泄“色”本能工具的這一行為進行反思。在回到香港之后,村岡伊治平繼續混跡于妓院之中,并將妓女倒賣到東南亞,在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后開設了多家妓院。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和社會法律的完善,村岡伊治平的妓院也逐一倒閉,此后,村岡伊治平召集了四個妓女與自己開始了所謂的家庭生活,并要求這些“妻子”努力地為自己繁衍后代。通觀整部影片,不難發現無論是妓院中的女性,還是村岡伊治平“家庭”中的女性,均被視為滿足男性“色”本能的工具,她們對于性的認知中永遠缺失自我,在男性絕對主導的性愛觀念中俯首稱臣,這無疑批判了男權思想對女性“色”本能的無情扼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日本電影人均試圖借助電影的娛樂性來驅散戰敗的陰霾,而今村昌平卻拒絕了人云亦云,他一直在不同題材的影片中體現日本社會中的陰暗一面或禁忌話題,事實上,這種呈現的意義遠比同時期的娛樂片深遠。在訪談中,今村昌平曾闡釋自己的電影創作理念,即探索人之為人的道理和趣味,這一頗具內涵的哲學問題在今村昌平的光影世界中被以本真、自然的方式呈現,這種對于人的探索的執著也正是今村昌平影片中的核心價值。雖然今村昌平已經逝世,其尚未完成的影片《新宿櫻幻想》也成為永遠的遺憾,但正如別林斯基所言,那些最為真實和富有個性的藝術作品將會永存。
[參考文獻]
[1][美]克莉絲汀·湯普森,大衛·波德維爾.世界電影史[M].陳旭光,何一薇,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77.
[2]鄭洞大,謝小品,主編.藝術風格的個性化追求——電影導演大師創作研究[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2:275.
[3][法]埃德加·莫蘭.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M].陳一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223.
[4][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選[M].林塵,張喚民,陳偉奇,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59.
[作者簡介]門娟(1983— ),女,寧夏銀川人,碩士,北方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日語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