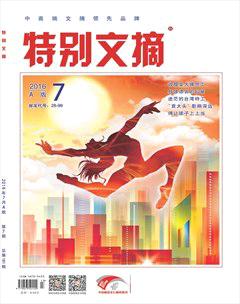對死神的嘲笑
跟八九十歲的老人家在一塊,常能聽見他們彼此打聽。
“喂!某人還在不在?好久沒看到了!”
“那個誰誰誰,早該死了!還拖著呢?”
死,明明是個避諱的字,但是對于他們似乎已經沒有什么刺激,遇到朋友駕鶴西去,一群仍在的老人們,齊赴靈堂,談笑風生,絲毫不見傷慟,倒真像餞行,托死者先去另一邊打點,等等大伙就跟來的意思。
甚至聽一群老人,瞻仰遺容之后走出來,笑說:“擦胭脂抹粉,比活著還漂亮呢!”
“她那壽衣,是跟我一塊兒去做的!不錯吧!挺體面!”
也不知,老人心里是真不感傷?到了這個年歲,在山上的朋友,要比城市里多得多。對死亡已經看淡?還是覺得自己得了上壽,已經活夠本,而處之泰然?抑或活著年老多病,本已沒了意思,反不如駕歸道山?
而那些子嗣們,則在老人故去之后,掛紅貼金地稱為喜喪。那喜之意,是感念上天,已經賜予老人上壽?還是暗慶總算脫了這個包袱?畢竟是死去,難道因為老人長壽,生者就能不傷心嗎?
倒是有一位“孝男”說出道理:
“想想!老人家死,已經九十多,而我也快七十了!七十的人,自己都不知哪天,而把死看淡了。再說老媽媽能走在老兒子之前,得個死后哀榮,正該為她高興才是,如果我先死,讓九十老母送葬,才可悲呢!”
又聽過一位老先生,笑呵呵地說:
“死?對年輕人是回事!當年三十多歲見朋友早死,又害怕,又傷心,后來死了祖父母、死了老爹老媽,又送了一大堆老朋友,心早麻痹了!所以上天是有美意的,讓我們由死親人、死朋友,到自己死,一步一步學著認識死!看得淡!”
記得讀過一個西方的真實故事:
一群老先生集資買了一瓶珍貴的老酒,約定由活到最后的人獨自享用。
老人紛紛去了!終于傳到最后一人的手上,但是當他打開包裝,才發現那美酒已被換為清水,其中夾了一張字條:
“對不起!我偷喝了!但你要同情我,因為我自認活不過你!話再說回來,現在只剩你一個,喝也沒意思,不如別喝,改天過來再一塊兒喝吧!”
死,竟是可以如此豁達,且帶有一份自嘲、幾絲幽默的!
(摘自“劉墉新浪博客” 圖/李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