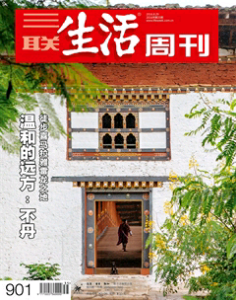徒步喜馬拉雅雷龍之地溫和的遠方:不丹
陳曉
在被想象的遠方里,不丹是一種更溫和的存在。

廷布一所小學的學生們在晨會上做禱告
樸素的美感
喜馬拉雅山區(qū)因為絕高的地理位置,被稱為地球上的第三極,也是距離工業(yè)文明最遠的地方之一。在這片山脈中的小國們,一向被視為現(xiàn)代世界之外的異域。以我的個人印象,傳統(tǒng)山區(qū)與現(xiàn)代文明對接時,總免不了受傷的命運。依靠宗教、王室等精神因素來維系的人類共同體結構,會被以資本驅動的經(jīng)濟紐帶所代替,兩種主導力量更替拉扯的過程中,有些地方會表現(xiàn)出失去秩序感的躁動,有些地方則就此成為沉寂的死地。我見過的喜馬拉雅山中城市,大體可以分為嘈雜的城市、凄涼的城市,或者嘈雜和凄涼共存一體的城市。那里的古跡,要么已經(jīng)失去了現(xiàn)實功能,只是給游客呈現(xiàn)異域風情的古董展品,要么雖然還竭力延續(xù)著自己古老的使命,但已陳舊不堪,讓人感覺到與現(xiàn)代城市的距離。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近在咫尺地鮮明對立著。
對立和撕裂中當然也有美感。比如加德滿都的嘈雜,自有其濃厚的煙火氣和生命力,而巴德崗城外殘存神廟的凄涼,云際低回夕陽西下時,也自有其意蘊深長的詩意。但這些美感都是碎片化的,一個被現(xiàn)代文明拉扯破碎的世界的陰影更濃重地籠罩著城市,處處可見凌厲的傷口:污水橫流的街道,機動車尾氣和灰土攪起漫天煙塵,如廢墟一般的貧民窟,神態(tài)萎靡的原住民……總的來說,是不整潔的,飽含激烈沖突或者絕望情緒的。從現(xiàn)代世界初來乍到的游客,前兩天難免感覺失望和不適。如果無法完成心理調試,建立起新的情感聯(lián)系或者審美標準,多半就會有一次失敗的旅行。
雖然被稱為是世界上最封閉的國家——1999年才開放有線電視信號,還是世界上最晚開放互聯(lián)網(wǎng)的國家,即便是和并不處于工業(yè)文明前端的其他亞洲國家相比,不丹在技術上也幾乎落后了20年,但它卻并不給外來者“分裂的異域”那種隔閡感。從加德滿都登上不丹的飛機,就感覺從無序的色彩汪洋和嘈雜的灰塵中脫身出來。機艙內顏色清爽分明,黑色小皮椅線條簡潔,襯著白色機艙和疏疏落落的乘客。餐盒里放著一瓶明黃的芒果汁,幾根乳白色芝士條,透明小袋里是幾枚棕色堅果,食物的擺放有種帶靜氣的美感。下飛機等待入關的地方像個兩層樓高的小天井,傳統(tǒng)圖案的幾道花飾破開整面白墻,光線從屋頂自上而下充滿了整個空間。明亮但不艷麗,有著我們熟悉的現(xiàn)代審美元素:干凈,簡潔,溫暖。
這樣的美,我還在富比卡山谷的民房中看到了。那是一個通往不丹中部的一個碗狀冰川峽谷,黑頸鶴們每年來峽谷內鋪滿綠草的濕地越冬,濕地邊就是附近村民們種土豆的土地,人類和鳥類的領地毗鄰卻互不侵擾——至少村民是這么告訴我們的。清晨穿過山谷邊的樹林散步時,看到一棟棟鄉(xiāng)間民舍的院子里繁花似錦。其中一家尤其茂盛,碩大的芍藥像小樹苗似的組成一堵花墻。房屋的墻根下和窗臺邊,層層疊疊擺滿了花盆。女主人德瑪穿著旗拉,捏著織了一半毛線腰帶的織針,站在院子里聞早晨的花香。里屋第三層,她的媽媽正在一塵不染的神龕前祈禱。一層客廳的木地板上,鋪著小毛毯,放著奶茶和早餐。她的姐姐正在一邊吃早飯,一邊看電視里穿著傳統(tǒng)長袍的主持人,做出嚴肅專業(yè)的姿態(tài)和嘉賓就某個事件侃侃而談。廚房的燃氣灶上,黃銅茶壺里的早茶咕嚕咕嚕冒著熱氣,新打制還未上漆的原木櫥柜,襯著淡藍色地磚,散發(fā)著隱約的木香。
1961年,印度軍官LT GEN進入不丹執(zhí)行軍務時——這也是自1907年不丹首任國王加冕以來,印度第一次派兵進入不丹,對不丹的印象是樸素(simplicity):“有的人將不丹描述為貧窮,但我認為不如說樸素更合適。貧窮指的是缺乏必需品,而樸素,是摒棄了不必要的物品。”這間富比卡山谷中的普通民居,讓我想起了這段話。播放著訪談節(jié)目的電視,顏色淡雅的瓷磚,裝著自來水管的白色洗手臺,這些代表現(xiàn)代基本生活方式的物品,與不丹的傳統(tǒng)審美結合在一起,有一種具備年代感的樸素潔靜之美,給人一種身在世俗世界卻又時光倒流的感覺。
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從民居到宗堡,現(xiàn)代生活的細節(jié)正一點點滲透進不丹人的日常中,但還保持著相對統(tǒng)一的沉靜和美感。帕羅、廷布是不丹城市化走在最前端的城市,按常理應該是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沖突最劇烈的地方,但空氣里仍有一種秩序感:沒有摩天樓,房舍高矮大致相同,外形花飾也幾乎一樣。即便是電視塔,也沒有高過山頂叢林的佛像或者寺廟。建于幾百年前的政教合一的宗堡,如今仍然是僧侶生活和政府機關辦公的地方。汽車既不鳴笛,也沒有爭搶。在車流量最大的中心路口——世界上唯一還用人力指揮的交通樞紐,交警做廣播體操那樣慢悠悠擺動著雙手,動作像沉靜的水流一樣連貫但緩慢。城市中不見乞丐,也少有衣衫襤褸的人。即便是菜市場的肉鋪,也規(guī)規(guī)矩矩在一格格裝著玻璃門窗的房間里,水泥臺砌成的肉臺上,魚頭和魚身子整整齊齊排在一起,長條的豬肉薄片有條不紊地掛在肉鉤上。

辣椒是不丹人最喜歡的食材
城市中也不乏一些外形粗陋的現(xiàn)代建筑,不那么體面的雜亂角落,但它們并不引人注目。遠處云煙繚繞、植被茂密的青山,以及行走在街頭身著民族服飾的不丹人,足以彌補城市外觀上的漏洞。廷布街頭的不丹女人大多身穿寬袖窄身的“旗拉”,男人不少則穿著過膝長袍“幗”,服裝的布料都是織造的,用的是自然布料,且以傳統(tǒng)自然染料染成,即使遠看也有一種韻味。身著如此粉紅深藍暗紫亮綠等不同顏色服裝的不丹人,在疏朗的街道上,幾乎足不出聲靜悄悄地往來穿行,光景煞是好看,尤其是清晨和黃昏時分的情景,確有一種什么在撫慰人心。
自我保護與自我塑造
旗拉和幗,是不丹在西方文化的強勢浪潮下,為自己保留下來的一個共同體標識。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文明》一書中寫道:“服裝處于整個西化進程中的核心位置。很久以前,被歷史學家們稱為‘工業(yè)革命那場偉大的經(jīng)濟變革,就發(fā)端于紡織品制造,它是早期技術革新浪潮引發(fā)大規(guī)模生產(chǎn)所創(chuàng)造的一個奇跡。但是,如果沒有對廉價服裝需求無限增長的消費社會的發(fā)展,‘工業(yè)革命就不會在英國發(fā)端,更不會蔓延至西方世界的其他地區(qū)。”在紡織工業(yè)技術與消費社會的相互促進下,服裝工業(yè)的發(fā)展既是一次全球化的服飾革新,也是一種文化掠奪。1909年,法國猶太裔銀行家阿爾伯特·卡恩曾著手制作一本有關世界各地人民穿著的彩色照片簿,以記載20世紀初人類在地球表面居住以及開發(fā)的情況。20世紀初還是個國如其衣的年代,7.2萬張照片,包括來自50多個國家的各式民族服裝:愛爾蘭地區(qū)身著羊毛服飾的農(nóng)民,阿拉伯披掛長袍的酋長,達荷美一絲不掛的武士,印度戴花環(huán)的王公……但一個多世紀后,照片中的絕大部分服裝已經(jīng)消失了,牛仔褲、T恤、夾克衫等西式平價服飾一統(tǒng)天下。
不丹是少有的保留下民族服裝,并讓它在現(xiàn)實生活中依然還有生命力的國家。首都廷布曾立法規(guī)定,如果不穿傳統(tǒng)服飾進入這座城市,將面臨罰款甚至被捕的危險。現(xiàn)在雖然沒有這么嚴格,但所有公務人員在公共場合或是執(zhí)行公務時,仍然必須穿民族服裝。這一規(guī)定,不僅讓不丹城市中的平常街道因為身著旗拉和幗的人們,顯出獨特的美感和韻味,也拯救了不丹的紡織工業(yè)。這個產(chǎn)業(yè)關系著散布在高山草場上的牦牛牧民們的生存,還關系著這個國家的紡織工藝和審美文化。
不丹有一系列針對消費社會的禁令:它是全球第一個全面禁煙的國家,也一度對入境的旅游人數(shù)進行限制,并設定每天200美元的最低消費額度,以免游客大量涌入不丹。即便國外登山隊愿意付出極高的費用,甚至使用一些政治外交手段,不丹政府仍然不允許他們攀登境內最高的雪山。為了不成為消費社會里廉價的原材料供應地,不丹拒絕砍伐森林,也拒絕發(fā)展采礦業(yè)。上層的意愿同樣傳遞到民間。澳大利亞記者邦蒂·埃維耶森(Bunty Avieson)曾為不丹媒體《Bhutan Observer》做過顧問,她在自己的書中寫道,《Bhutan Observer》的主編曾經(jīng)拒絕刊登印度汽車等消費品廣告,因為覺得會給那些買不起汽車的村民制造出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這不是件好事。而少量的廣告客戶,愿意花錢在媒體上表達的不是“我的產(chǎn)品有多好多便宜,快來買吧”,而是“我們有多么熱愛我們的國王”。不丹因此被認為是個封閉保守,難以用現(xiàn)代經(jīng)濟規(guī)則與之溝通的國家。但如果追溯到上世紀初王國初建時,會發(fā)現(xiàn)不丹很早就有選擇地向外求索,探尋自己的現(xiàn)代化之路。在這條路上,西方世界的影子一直在其中閃現(xiàn)。
“現(xiàn)在的不丹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前些年它飽受國內紛爭之苦,城市遭到重創(chuàng),人口不斷減少。現(xiàn)在,和平的歲月終于到來了。在你們的保護之下,一個穩(wěn)定的世襲政府已經(jīng)建立起來。”這是1921年9月5日,不丹第一位國王烏顏·旺楚克寫給英國駐印度總督的信,希望“在不丹發(fā)展成為一個文明國家的進程之中”,英國治下的印度能和不丹建立起更加緊密的政治和貿(mào)易聯(lián)系,并且?guī)筒坏づ嘤枃倚枰默F(xiàn)代化人才。
“首先要克服的障礙就是國民的愚昧無知。”國王在信中寫道,“在7年前,不丹的寺廟之外沒有任何人能夠讀書寫字。1914年,我把45個男孩送去噶倫堡上學,他們中有33個達到了中學畢業(yè)的水平,還有4個將參加18個月后的大學入學考試。現(xiàn)在的問題是,怎樣讓這些小伙子在不丹的發(fā)展中最大限度地發(fā)揮作用,有大批空缺職位等著他們。”
“我們急需醫(yī)學知識來治療頻繁奪去人們生命的流行病,解除人們的病痛,幫助降低死亡率,因此,我希望至少兩個孩子接受培訓,成為醫(yī)生。”
“能有兩個孩子進入獸醫(yī)大學最好不過,過去那些年中,大片國土上的牛因為瘟疫幾近滅絕。”
“為了在更大的國民范圍之中開創(chuàng)普通教育的系統(tǒng),還有一些孩子應該接受科學和教學方法的深入培訓,有6名小伙子之后可能會被任命掌管一所培訓學校,培訓不丹的小學教師,并管理各個地區(qū)中心的學校。”
“國民經(jīng)濟的核心是農(nóng)業(yè)(還包括畜牧業(yè)和乳品業(yè)),我們的全部人口幾乎都從事這些行業(yè)。我相信,如果采用了那些我聽說應用于其他很多國家的現(xiàn)代化手段,農(nóng)作物和牲畜的狀況都將大大改善。如果能有3個孩子得到農(nóng)業(yè)和乳品業(yè)(包括制酪)方面的科學、實用的課程訓練,他們能引進先進的方法,建立示范農(nóng)場,教給人們。”
這封信像一個生活在山中的淳厚長者,為家族的未來向山外強大的鄰居求助,誠懇謙卑,卻頗有見識,表現(xiàn)出對西方現(xiàn)代知識的了解和信任。老國王烏顏·旺楚克在信中對不丹未來人才和產(chǎn)業(yè)的規(guī)劃,被認為是“撒下了不丹現(xiàn)代化的種子”。在過去100多年,這個國家沒有劇烈的動蕩,旺楚克王室已經(jīng)穩(wěn)定地傳承到第五代,現(xiàn)代化之路在一個基本統(tǒng)一的思路下發(fā)展著。
郵票是不丹現(xiàn)代化之路上值得一提的另一個故事。1951年,美國人伯特·克爾·托德去不丹參加牛津校友格桑卻登的婚禮,結識了格桑卻登的丈夫——不丹王子吉格梅·多吉·旺楚克。后來王子加冕成國王后,想要對世界宣傳不丹,托德做了一些調查,認為在那個集郵風行的時代,郵票有助于提高不丹的國際知名度。1962年,托德開始幫助不丹設計郵票,既展現(xiàn)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也將它打造成獨一無二的藝術品。1967年,不丹發(fā)行了世界上第一款3D郵票,這一年不丹靠賣郵票賺了5萬美元,接下來兩年的收入翻倍增長,大部分買主都在國外。1969年3月,不丹成為國際郵政聯(lián)盟的成員,這是聯(lián)合國下屬的一個機構,不丹因此順理成章?lián)碛辛嗽诼?lián)合國貿(mào)易和發(fā)展會議中的一個席位。

1.不丹郵局2.郵票上的四世國王形象3.第五任國王和王后成為郵票上的標志性人物
與對外隔離不同,郵票以及后來基于不丹佛教理念提出的GNH(國民幸福指數(shù)),都是不丹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自我塑造的方式——既符合外部世界的某些需求,又立足于不丹的傳統(tǒng)。因為這種自我塑造中與現(xiàn)代世界的聯(lián)系,當現(xiàn)代世界的種種進入這里時,也像細流融入大河,不至于激起巨大的浪花。不丹從2008年實行民主選舉,但這個國家并沒有明顯的政治分歧,沒有“左派”或者“右派”,沒有“保守主義”或者“激進主義”,甚至連宗教分歧都沒有——信仰藏傳佛教的國民占據(jù)絕大多數(shù)。競選也不搞金錢戰(zhàn)術,選舉委員會甚至禁止活動會議上提供啤酒、奶酪和米飯。每天晚上唯一的國有電視臺會播放電視辯論,兩個黨派候選人主張的政策差異很小,相互間表現(xiàn)得彬彬有禮。與其說選民是為政策或者意識形態(tài)投票,倒不如說是為參選人本身投票。現(xiàn)代世界的“政治舶來品”,在這里也被染上了不丹氣質:清淡、干凈、溫和。
過渡階段
迄今為止,這個國家的自我塑造是成功的。它符合全球化大世界對“小而美”事物的期待,符合一個物質膨脹的消費社會對純粹精神的渴求。世界記住了不丹——它得到了很多贊譽,也得到了很多幫助。當發(fā)達國家想要表達“建設一個更美好世界”的愿望時,常常會把不丹當作聊表心意的對象。
“不丹人已經(jīng)習慣外部世界向他們‘扔錢了。日本付錢給他們買保持市容整潔需要的垃圾車,澳大利亞送來消防員培訓和優(yōu)種綿羊,丹麥在這里投資了保安業(yè),瑞士幫助發(fā)展土豆種植,奧地利拿出幾百萬用作鼓勵良好的社會治理……還有個階段,歐洲國家的聯(lián)合財團捐贈了一些昂貴的機器幫不丹人發(fā)展伐木業(yè),希望當?shù)厝艘虼双@得更多的收入。若干年后,斯堪的納維亞的一些國家又捐贈一大筆錢,用來關閉伐木業(yè),以挽救森林并補償失業(yè)的工人們。”澳大利亞記者邦蒂在自己的書中寫道。
這些幫助究竟是不丹真正需要的,還是外部世界對這塊“香巴拉之地”的各自想象,我們無法做出評判,但過多的幫助和過多地倚靠幫助,確實給不丹帶來一些麻煩。“我們得到了很多國家的幫助,但這些外部幫助常常又破壞了人們的意志,因為人最后變得非常依賴,沒有勤奮工作的想法了。美國人因為勤奮所以強大,中國人更是勤奮,所以我很感激來自外部世界的幫助,但這些幫助同時有一個奇怪的效應,讓人無法獨立。”宗薩欽哲仁波切在接受我們采訪時,這樣講自己對不丹社會的擔憂。
邦蒂在不丹媒體《Bhutan Observer》做顧問時發(fā)現(xiàn):“有大量30歲左右的年輕人還待在家里,和爸爸媽媽生活在一起,而不愿意自食其力。如果他的親戚恰好有點什么產(chǎn)業(yè),他們就順便在那里打點毫無職業(yè)前途的零工。”“這是很可怕的,因為他們不愿意學習獨立。對成功來說,獨立是非常必要的。他們沒有被鼓勵或者被施加壓力從家里走出去承擔責任,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如果不丹人能在佛教教義中找到一條既維系家庭紐帶,又發(fā)展獨立和自我價值的中間之道就好了。”
“幫助”不僅軟化個體的意志,甚至也影響著國家的獨立性。不丹和印度的關系就是在“幫助”之上建立起來的。從20世紀初開始,不丹第一任國王寫給英國駐印度總督的求助信得到了正面的回應,此后印度一直在不丹的經(jīng)濟成長里起著重要作用。印度軍官LT GEN的書中曾記錄:“不丹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費用預算是1.6億盧比,第二個五年計劃是2億盧比,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總支出為3.55億盧比,相當于前兩次五年計劃的支出總額。其中3.3億都來自印度——3億贈送,3000萬作為貸款,不丹自己只拿得出2500萬盧比。”這種狀況到今天仍然沒有太大變化。水電是不丹第一大產(chǎn)業(yè),到2020年,又有10座10萬千瓦大型水電站投入使用,將成為不丹未來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但讓經(jīng)濟學家煩惱的是,這些水電的修建必須在印度的支持下才能進行,目前僅有三座水電站開工,時間拖得越長,修建水電站的成本就升得越高。過去印度為水電站給予接近全額的補助,但現(xiàn)在他們更多以發(fā)放貸款的方式。而且印度是不丹水電的唯一購買者,“債主”和“買家”的雙重身份,將會影響電力交易時的正常定價。但不丹為保護森林和環(huán)境,拒絕發(fā)展工業(yè)的一個后果是,它不得不長期依賴這個強大的鄰居。國內大部分建設工程由印度的10萬勞工完成。大部分商品,包括食物,經(jīng)由印度進入不丹。英國《經(jīng)濟學家》雜志曾撰文稱:“不丹的經(jīng)濟和政治政策實際上是在德里制定的。它對自己的未來的話語權是有限的。”

不丹中部布姆塘一所村莊學校的孩子們在課堂上
將幾乎所有產(chǎn)業(yè)交給外國的另一個危險是,國內就業(yè)崗位不足,年輕人沒有足夠的自立和上升空間。不丹每平方公里只有18個人,大量的土地被森林占據(jù)或是被閑置。這讓整個國家在寧靜溫和的美感中,又帶著一種清冷之氣,它或許是社會活力不足的一種暗示。年輕人如何在這樣的社會中找到未來,確實是不丹要面臨的社會問題。
“如果不丹人能夠擁有自信,不丟掉它的傳統(tǒng)特性,同時又能搞好教育,不斷進步,那么不丹是可以發(fā)展強大的。”宗薩欽哲仁波切這么對我們解釋一個“小”國的生存之道:在被工業(yè)革命變成扁平的世界里,“小”既是對一個國家的保護——因為市場有限,不是資本強攻的重點,所以可以保持一種相對平和的狀態(tài)。但“小”也是最大的軟肋——它太脆弱,與現(xiàn)代世界可交流的點非常有限,稍不注意,就可能有巢傾卵覆的危險。不丹如何在郵票、GNH、香巴拉的夢幻之外,找到新的同時具備安全性的與現(xiàn)代世界接軌的點,或許是這個國家在平和外表下正艱難摸索的問題。
離開不丹的前一天下午,我坐在帕羅城外的酒店花園里,打量著周圍的風景。院子里繁花似錦,圍繞著一小塊籃球場。幾株蘋果樹結滿了青紅相間的果實,每天餐桌上的水果就是從這里摘下的。一大堆柴火堆在酒店的土黃色矮墻邊,墻外面一大片綠油油的稻田延伸到青山下,田地中間立著幾幅白色經(jīng)幡,遙遙呼應著青山上的宗堡。沒有一種元素壓倒另一種元素,沒有一種色彩壓制著其他色彩,這讓人內心覺得安穩(wěn)。不丹是否需要更強勁地走向現(xiàn)代社會的動力,這種平靜下是否隱藏著危險的暗流,我無從判斷,只是確定地知道,在2016年7月這個夏天,我感受到的還是一個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尚未完全撕裂、有著溫和世俗之美的不丹。(感謝實習記者周緣對報道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