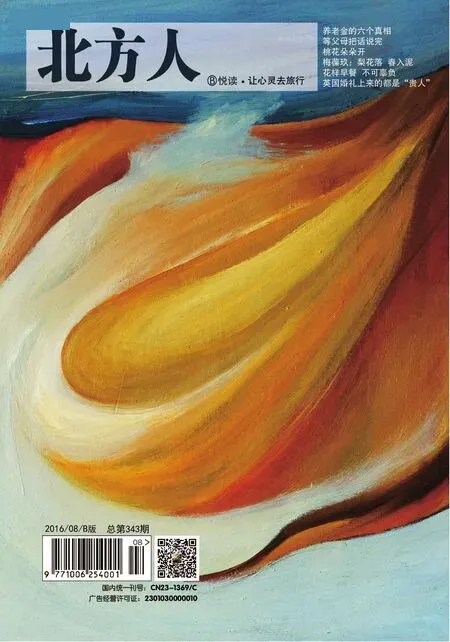梅葆玖:梨花落 春入泥
文/溫天一
梅葆玖:梨花落 春入泥
文/溫天一

今年的3月29日,是梅葆玖82歲的生日。
在生日當(dāng)天,他還參加了兩個與戲曲有關(guān)的活動,一是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xué)進(jìn)行表演示范講座,二是為昆劇名伶沈世華女士的傳記《昆壇求藝六十年》新書發(fā)布會擔(dān)任特約嘉賓。
而在之前進(jìn)行的全國兩會上,梅葆玖也全程參會,他的提議是希望今天的孩子們多聽京劇、練習(xí)書法,并且能夠認(rèn)識繁體字。
而就在生日之后的兩天,梅葆玖在一次與戲曲界老友的聚會上,突發(fā)支氣管痙攣,導(dǎo)致腦缺氧送醫(yī)院搶救。
父親的兒子
梅葆玖是梅蘭芳與夫人福芝芳的第九個孩子,所以小名叫做“小九”。
在他之前,梅福夫婦二人只有三個孩子真正避免了幼年夭折的命運,所以幾乎從“小九”一出生,就成了這個家庭中備受寵愛的小兒子。
梅葆玖成長在上海,與他那位北平梨園世家出身、南城胡同長大的父親不同,他似乎天生就沾染上了一點洋氣。
對于中國來說,上世紀(jì)三四十年代,是戰(zhàn)火紛飛的亂世,面對國恨家仇,父親梅蘭芳也背負(fù)著巨大的壓力,他曾數(shù)次在時代的轉(zhuǎn)折點做出艱難的抉擇,但對于滬上少年梅葆玖來說,他的童年時光在父母的庇佑之下,過得相對安詳平和。
梅家的教育很洋派,梅葆玖的小學(xué)與中學(xué)都在有著教會背景的震旦度過,他在那里,學(xué)會了流利的英文與簡易的法語,并養(yǎng)成了洋派紳士的禮貌與儀表。
在學(xué)生時代,梅葆玖的興趣與愛好并不局限在文學(xué)與藝術(shù),事實上,他最感興趣的事情是制作航模與汽車模型,還有研究電子管收音機(jī)。生活中,他自己做過立體聲音響設(shè)備,對機(jī)械汽車極有研究,甚至,他還學(xué)會了如何駕駛飛機(jī)。
梅蘭芳并不是一個專制的父親,雖然早已認(rèn)定京戲是自己一生的方向與信仰,但他并沒有嚴(yán)格規(guī)定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從事這行,但當(dāng)梅葆玖決定繼承衣缽的時候,梅蘭芳還是顯得由衷地開心。
1949年,梅葆玖陪父親一起來到北平,參加第一屆全國文學(xué)藝術(shù)工作者代表大會。那是這個上海少年第一次見到這個他日常長久生活的古都。
他第一次走進(jìn)了北京城的老劇場,見識了父親從小生活的地方,也在父親的引薦下,見到了大批父親的老前輩與老朋友們,那是梅葆玖青少年時代藝術(shù)成長最受益的時間,他幾乎天天守著父親,甚至跟隨父親去朝鮮慰問演出。
傳承者
1961年,梅蘭芳突發(fā)心臟病去世。那時,梅葆玖還不滿30歲。失去了父親的庇佑與護(hù)航,梅家最小的兒子在倉促中承擔(dān)起了繼承與發(fā)展梅派藝術(shù)的擔(dān)子。
真正作為藝術(shù)家與梅派傳承者,而并非僅僅是梅蘭芳之子的梅葆玖,真正走入大眾視野,是在上世紀(jì)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
梅葆玖開始一邊演出,一邊收徒。他一出一出地恢復(fù)起父親的經(jīng)典代表作,在全國范圍內(nèi)尋覓著適合演繹梅派的好苗子,絕不是僅僅局限在梨園世家的內(nèi)部。
李勝素是梅葆玖在 1987年發(fā)掘出的梅派新秀,在跟隨他學(xué)習(xí)七年之后,在1995年正式拜師,成為入室弟子。
李勝素對于梅葆玖的最初印象,是他的“斯文、儒雅與帥氣。”“第一眼看上去,他并不那么像是我們印象中從事傳統(tǒng)戲曲藝術(shù)的人。他很洋氣,非常有風(fēng)度。”
上世紀(jì)80年代的中國,正是傳統(tǒng)文化開始復(fù)蘇的年月,而對于京戲界內(nèi)部來說,彼時的舞臺大部分由張(君秋)派青衣統(tǒng)領(lǐng)風(fēng)騷,張派的甜、嗲、媚、脆風(fēng)靡一時,甚至有了“十旦九張”一說。
雖然梅葆玖從無門派之見,但他對于梅派藝術(shù)的傳承與努力,某種程度上,不僅僅是繼承并發(fā)展了一個京劇的流派,更像是復(fù)興了一種審美:謙和、優(yōu)雅,沒有大江東去的悲情與炫技的演繹,一切都圓融隨意、波瀾不驚,卻在暗香浮動中流露出骨子里的堅持與韻味。這是梅派藝術(shù)的審美,也是梅家父子做人的修為。
在李勝素的印象中,梅葆玖并不是一個因循不變的守舊者,“因為他從小接觸的東西,以及外來文化的影響都能在他身上體現(xiàn)出來,老師的作品,有時代感,不保守。”
梅葆玖將自己從父親處繼承來的梅派代表劇目一出出傳承給了李勝素以及其他的學(xué)生。
李勝素還記得,自己第一次學(xué)完《生死恨》后,在劇場首次公演。按照一般的規(guī)律,她5時來到劇場上裝,穿戴好之后,7時30分大幕正式拉開。但她沒想到,梅葆玖先生4時多就來到了劇場,手里拿著錄影錄像的設(shè)備,他親自把場,給學(xué)生信心,并且從頭到尾自己錄完了整出戲。“我的第一次《生死恨》,是老師親手錄下的。”如今說起來,李勝素依然滿心感動。
二十一世紀(jì)初,一出融合了梅派經(jīng)典劇目《太真外傳》的大型交響京劇《大唐貴妃》創(chuàng)作上演,它的導(dǎo)演是出身梨園世家的著名戲劇導(dǎo)演郭小男,編劇是海派京劇學(xué)者翁思再,梅葆玖與張君秋之子、馬派老生張學(xué)津,梅派第三代傳人、梅葆玖的學(xué)生李勝素與于魁智,還有上海京劇院的史依弘與李軍分別飾演楊玉環(huán)與李隆基。
在融合了交響音樂的京劇舞臺上,梅葆玖盛裝亮相,雖然只有最后短短的一段,但他的一把聲音,褪盡虛火,顯得非常明凈舒揚。
“梅老師也有遺憾,他在人生最黃金的時期,沒有站在舞臺上,他一直很想創(chuàng)作一部屬于自己的新戲,但一生都沒有實現(xiàn)。”李勝素說。
不落幕
梅葆玖沒有子女。
除了演出、教學(xué),他的閑暇時光,喜歡與貓為伴。在自己家的老房子中,他養(yǎng)了幾十只貓,每一只都有名字,比如“小黑”,“每當(dāng)給它們準(zhǔn)備好一大盤食物,就連街坊的貓都會跑來蹭吃。”梅葆玖先生曾說,“人生一大樂趣就是看貓吃飯。”
他依舊保持著上海時期遺留下來的生活習(xí)慣,喜歡吃蛋糕,開汽車,教學(xué)生在演出前吃一個蘋果,潤喉又順氣。
在任何場合看到他,梅葆玖永遠(yuǎn)都是樂呵呵的樣子,在上海他講一口斯文的老式上海話,其中很多用詞今天的年輕人已經(jīng)不再使用;在北京,他講一口柔和輕松的京腔,帶著點隨意灑脫的味道。
按照梅葆玖的設(shè)想,在前年和去年,完成在世界范圍內(nèi)紀(jì)念梅蘭芳的巡回演出之后,今年年底,他要再次集合《大唐貴妃》的團(tuán)隊,在重新打磨精修之后,再度上演此戲,以紀(jì)念父親梅蘭芳。但一切還沒來得及,他就匆匆入院。
對于大部分接觸過梅葆玖的人來說,他的謙遜與溫和最讓大家所印象深刻,這是人所公認(rèn)的、梅葆玖除了似幻還真的長相之外,對于父親最大程度的繼承與發(fā)揚。
梅蘭芳從來都是一個不爭不搶、愿退一步為他者讓出一條生路的人,但最后卻成為了象征中國戲曲藝術(shù)最高審美理想的一代宗師。梅葆玖也是一樣,盡管他沒有像父親一樣,在京戲最繁華的時代創(chuàng)造出無數(shù)經(jīng)典的角色,但他卻用自己的努力,在時代的變遷中盡量維護(hù)著京戲的尊嚴(yán)。
在郭小男的形容中,梅葆玖是一個“大家之氣,不拘小節(jié)的人。”“他的脾氣溫和極了,從來不霸道,在我們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梅先生總是以這樣的語氣和你商量:看看這樣合不合適?不成就還是聽你的,我就隨便一說。”
在上海昆劇院的典藏版《牡丹亭》演出之時,有年輕觀眾第一次見到了梅葆玖的風(fēng)姿,當(dāng)時他在謝幕時款款而來,清唱了一曲《皂羅袍》。
那種帶著舊時代斯文氣息、無比優(yōu)雅的風(fēng)度讓年輕人看呆了,有觀眾默默說,覺得看到一個時代走了出來。
但我們不知道,梅葆玖的離世,是不是也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jié)。
在梅葆玖入院期間,翁思再專門赴北京看望梅葆玖先生,當(dāng)時,為了刺激梅葆玖的心臟與神經(jīng)反應(yīng),醫(yī)護(hù)人員與家人學(xué)生特意在他的枕邊播放《大唐貴妃》的主題曲“梨花頌”,“梨花開,春帶雨,梨花落,春入泥”,這次,溫潤舒展的梅派四平調(diào)在病房中響起,在翁思再的回憶中,當(dāng)時聽到曲子,梅葆玖的心臟有所反應(yīng),但相當(dāng)微弱。
但最終,“梨花頌”沒有喚醒他的神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