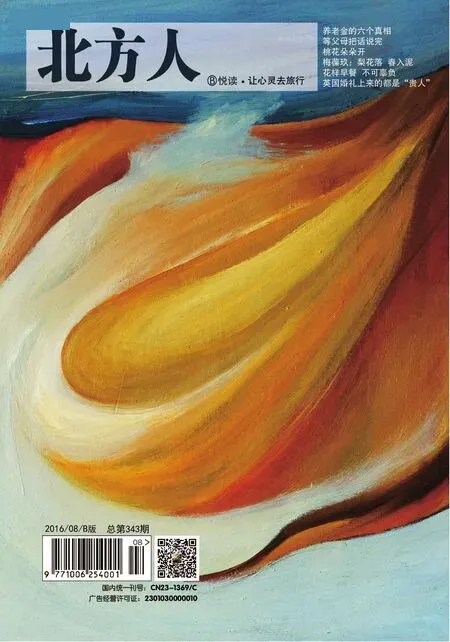旅館情結
文/惠 客
旅館情結
文/惠客

人們有多少時光陶醉于住一間旅館的“嶄新的開始”,就有很大程度上不停喜歡一種“在路上”的感覺。據建筑學理論來說,人對空間的依賴主要體現在視覺空間、觸覺空間、運動空間和心理感受。這種審美方面的需求解釋了我們有時對于某一旅館產生的直覺性喜愛和住久后滋生的依賴。這也是人們為什么覺得自己應該始始終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的原因。
如今讓我比較難忘的一間旅館是當時在愛丁堡的一間可以望見古堡的青年旅社Hostel。那是我第一次去蘇格蘭。當時據點在曼徹斯特。某個周日任性地拎一個紙袋,就從曼城中產階級的郊外社區,去往市中心的火車站。買了一張單程票。坐上了4個小時闊大車窗掠過濃蔭綠色的英國荒野旅程。在利茲的時候上來一個北愛爾蘭作家。男子。坐在我對面。憂郁陰沉的雙眼,一臉喬伊斯風格的絡腮胡子雜草叢生。總覺得在英國遇到的北愛爾蘭人似乎都是有著某種天生的敏感和自身的沉重的。或許是因為這個民族本身就背負了太多。然后他開始說話。北愛爾蘭口音也是很難懂的。他說他正在寫一部小說,坐在英國各個地方的咖啡館。開始說人生,開始說moment,開始說對人性是怎樣一種失望以及在這世間是怎樣一種痛苦。講到暮色西沉。火車服務人員開始推著小車過來賣東西了。清貧的北愛爾蘭作家請我喝了一杯咖啡和鹽醋味道的薯片。遙遠的去蘇格蘭的旅程。作家以一種并不令人討厭的搭訕方式說著自己的故事。我不知不覺也被聽入迷了過去。心想這一切多好。心想這一切遠離世俗是多么好。
然后我就在愛丁堡下車。瞬間走入一個感覺所有人都很高的城市。確實到英國北方了,我想。身高都隨著海拔而滋長。一處人們自稱是蘇格蘭人而永不愿稱是“英國人”的地方。我拎著小紙袋來到“游客中心”。問服務人員有沒有旅館可以介紹,以及在愛丁堡應該怎樣玩。
英國一個比較好的地方就是這種公共設施很完善以及服務人員真的不會不耐煩。所以縱使是外國人,縱使是一場只拎著一個紙袋的單人旅游,也不會讓你覺得孤寂和沒有歸屬感,反而是自由和遼闊。人生的那個階段十分享受那種成為Global Citizen的感覺。絕對自由。絕對討厭被貼標簽。
黃頭發的英國女孩為我推薦了她說“能看見愛丁堡古堡景觀的Hostel”。價格不很貴,能交到很多朋友,而且,景觀真的超級好。
我住在一間屋頂是斜的閣樓間。躺在床上,透過半透明毛玻璃的舊式貴族宅邸改建的hostel,可以看見愛丁堡晴朗湛藍的天。晴朗,沒有一絲迷惘,又充滿著一種嶄新、屬于星星的期望。那時一切在這種瞭望中分明明晰起來。一種我們人生下一步應該怎么辦以及很想迫不及待擁抱生活的沖動。
晚上從一間教堂改建的夜店歸來。走進公共休息區域連接WiFi,上傳旅行照片。休息間是那種典型的英式起居室樣式。深黑色鐵格子的歐式長窗房,邊配紅色天鵝絨曳地窗簾。維多利亞時期的燭臺以及壁爐,古老三角鋼琴。一個來自芝加哥的青年,在彈一首莫名哀傷的曲調。人們,或面對電腦,或三兩談笑,或拿一杯香檳獨自站在窗前。古老的城堡,晚間被一種黃的綠的光打的,突然涌生出巍峨之感。
“我來自美國。”彈琴青年說,“從歐洲背包旅游至今。賣過熱狗、當過酒保,在吉普賽人的房車里一連住幾個禮拜。我不明白生存以及明天。我只知道,活在當下。當下很快樂、很溫暖,是不是就夠了?為什么要完成那么多世俗的任務?”
我的眼里突然涌出熾熱的淚水來。然而卻并沒有讓任何人看見。有多少時候,我們生命中其實就是要追求一些極簡單的東西,然而卻被更復雜的世界,所吞沒了。
第二天,坐旅游巴士出游。曠遠的蘇格蘭高地。一切有種被洞悉的夢幻。藍到近乎于無羈的天。綠到無涯的青草。開旅游大巴穿Kilt的蘇格蘭司機,在車廂內一輪一輪播放自己燒制的CD。用超難懂的蘇格蘭口音為我們介紹當地原創音樂。不那么被世界所熟知卻又有著自己獨特味道的高地音樂。也是一個,有夢想然后不得不屈服于世俗及生存的靈魂。我閉上眼,聽著蘇格蘭風笛,一切有種綿軟而化不開的憂郁。
半夜有女孩簌簌回來的聲音。三三兩兩,抱著啤酒瓶,在走廊里吃吃的笑。各個國家涌匯而來的年輕背包客。每個人人生都有大把選擇橫在前面無數條路可以選的感覺。任何事似乎都可以在一天之內發生也可以在一天之內結束的年紀。一種你可以發現自己無限潛力、有多遠就能闖多遠的階段。可悲哀的是,很多人沒有意識到,有時這種任性,往往只有幾個夏天而已。
在康沃爾住過臨海懸崖的一處旅館。一片鏤空接近于無的空曠向海長廊,早上在其間的桌椅上吃早餐。云、渺淡的天、昏藍的海水。一杯黑咖啡喝了過去,能讓人產生那么舒長的擁有人生的欲望。路易莎跟我說她和丈夫的“婚禮早餐”就是在這座旅館吃的。新西蘭過來的移民女子,遇到了眼前這個英國丈夫,居然順理成章地結了婚。在他之前,她人生所經歷的一切苦難、不甘、不屑,都成了過去;而在她之前,他也覺得自身靈魂仿佛從未完整。他們年近60才結婚。人生各自已經經歷了太多。可是那天我看著她新婚的戴著戒指的臉,卻是那種無可比擬的幸福的。如此滿足、如此幸福。這樣從容的幸福,是不是也只有歐洲才有了吧。
威尼斯的斯拉夫河岸大道上有喬治桑住過的一處旅館。巴洛克風格的扶手椅和沙發。穆拉諾吊燈自挑高天花板垂下。大理石壁爐。推開長窗,來到露臺,即是臨河的絕美景色。夜間在這里喝一杯香檳再望著夜光下泛著淚光的威尼斯流水,是驚詫,還是唯美,這是一件不需要解釋的事。
然而,每離開一座美好的旅館,就有一種不可知的傷痕烙刻在身上。就跟很多人每搬一次家就會抑郁一樣。雖然“在路上”的靈魂是永遠不能永久居于一個地方的,但是,每次收拾行李,還是會有不可描述的飄零之感。然而,這,也是自由靈魂所需要承受的代價。
我們的人生,無數次在路上。無數次住過那么多曾讓自己如此難忘的旅舍。今夜我們到來,明朝我們離開,而生命中的爛攤子,永遠不需要自己收拾。在任何旅館所體會到的一切的美,都是短暫的,而正因為這種即將逝去的短暫,才將一切旅館所能體會到的美的極致,無比勾勒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