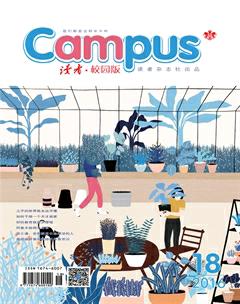英國首相怎么跟人吵架
安光系
差不多每隔一周,我都要上BBC的網站去看一個節目——《首相問答》。在大約半個小時的時間里,英國首相卡梅倫像吵架似的跟坐在會議室的議員們爭辯問題。多數議員都會提出問題,大到有關國家發展、民主民生,小到有關首相本人及家庭對某些事件的態度。大多數時間,這個并不太大的會議室里發生的事情,簡直令人不可思議:起哄、嘲笑、站起來反對……主持會議的人不得不多次提醒大家:“安靜!安靜!首相的回答必須要讓大家聽到!”
應付反對黨和其他議員的質疑不是個好差使。首相當年競選時說過的某句話如果沒有兌現,就會被他們當眾翻出來,拿腔捏調地念上一通。念完之后,反對黨領導人通常還會送上一個輕蔑的眼神,再加上一句質問:“首相先生,這是不是你說的?要不要再念一遍?!”
我最開始看這個節目時,覺得英國人簡直不可救藥。一個首相,貴為一國政府之首腦,每隔一段時間來議會,就大家關心的問題一一解答,再怎么也不至于在這個鬧哄哄的會議室里紅著臉,一次次解釋、溝通和辯駁,至少大家應該很有禮貌地聽他講完。但現場往往并非如此。節目里,每當首相回答一些問題時,總有人起哄、嘲笑以及憤怒地跺著腳,甚至退出會場以示抗議。
最初的時候,當反對黨議員質疑首相時,我總是會站在反對黨的一面。反對黨領導人每周提出的問題大多來自工薪階層甚至弱勢群體的郵件,都是涉及具體、實際的民生問題。對此,我至少是同情的。比如,某一家建筑公司的員工要失業了,面臨著諸多生存困難。再比如,某個家庭婦女掙的錢不足以撫養孩子。這些群體有可能是被政府忽略的部分。
但看的時間長了,我的態度慢慢有了一些改變:一個國家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處理。卡梅倫強調:沒有好的經濟基礎,你即使眼下許諾給民眾很多的福利,但最終都很難持續。所以,你可以經常聽到他說“不”。作為一個在倫敦居住多年的局外人,我也慢慢地從一個跟反對黨一樣痛恨、反感現任首相的人,變成了同情者、理解者和支持者。
每周閑下來的時候,我也會去附近的教會里喝茶,同社區里的那些英國老人聊天。有一次談論工黨和保守黨孰優孰劣時,幾位老人表達了相同的觀點:工黨一味給窮人爭取利益,看起來是為人民著想,但實際上,很多利益訴求都超出了這個國家的承受能力。最后,受傷的還是這個國家;而保守黨扎扎實實地搞經濟建設,表面上看沒有工黨那么照顧窮人,但可以讓這個國家走得更遠,讓窮人能享有更多的福利。“解決他們的就業,比直接給他們錢有效。”卡梅倫曾在辯論中強調。
“他們(工黨)執政的時候,就把這個國家弄得亂七八糟的。”一位老人跟我說。
我是一個局外人,起初常常以看笑話的心態來觀看這個節目。但看的時間長了,也慢慢理解了這個國家政治方面的一些運作流程。比如,即使有議員提出某個項目需要增加撥款,首相提議,相關財政預算也需要大多數議員審批。另外,遇到有一些更大的事情,如英國是否還留在歐盟,首相的任務只是把條件談好,最終的決定權還是交給英國民眾。在這樣的事情上,首相當不了家,當家的是議會、是民眾。
媒體成了政府和民眾之間的重要橋梁。在英國境內,像BBC這樣主流的電視臺,沒有任何廣告,每年靠收取每個電視用戶144鎊的費用(1鎊約為9.4元人民幣)來維持運作,但它在政府和民眾的溝通中,無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后來我還發現,不光是首相每隔一段時間會參加BBC的這類節目回答各種問題,英國的每個地方都有這樣的節目,由當地政府的相關負責人來接受議員的詢問并做出解答。
這是英國政府跟民眾之間溝通的一個重要渠道。這個渠道至少把政府領導人的一些治國理念和對一些熱點事件的思考與回應,都通過媒體及時地反饋給了民眾。
不僅是電視,報紙也會做相關的工作。比如,我就在英國當地的報紙上,看到過反對黨領導人的日記。日記里講述了他們每天做的事情,以及自己對政治和生活的見解。
在英國看報紙,也會看到一些相關部門的廣告。比如,希思羅機場會刊登一個整版的故事,告訴你如果現在不及時擴建機場跑道,幾十年后的英國將會落后于歐洲其他國家。他們用講故事的方式,預設英國下一代有可能受到的影響,從而讓民眾理解擴建機場跑道的意義所在。而現實中的報道是,機場擴建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為它的噪音會影響周邊居民的生活質量,民眾要求增加由此帶來傷害的補償費。
我家附近的Bakeloo地鐵線即將朝南延伸。地鐵里可以看到相關部門的廣告:規劃之前,有關部門會請各界民眾參與他們的規劃設計,在會上你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你可以寫郵件、留言、打電話或參加討論會。有了這些討論,至少不會出現一些低級的錯誤。前年,我曾在國內坐高鐵,帶著1歲左右的兒子進站時,竟然找不到一個可以給孩子換尿片的專門空間。蹲在廁所里當眾給孩子換尿片,怎么都不會覺得有尊嚴。國內新建的高鐵站都很氣派,但跟國外相比,卻少了這些人性化的設計。如果,當初這些設計者在設計時,能夠像英國這樣公開向民眾征求意見,情況恐怕就會好很多。
除了政府,英國女王也會不停地會見各界人士,甚至包括小學生。幾年前,我女兒在讀小學時,有一次憤憤不平地跟我傾訴:英國女王要到我們的小鎮上來,學校里只有一個代表名額。按照公平的原則,所有的學生都會參與抽簽,結果,一個年紀只有三四歲、正在讀幼兒園的孩子抽到了。女兒有些不甘地說:“他去干什么?他連話都說不清楚!還不如讓我去呢!”
我聽了大笑。
在英國的學校,也會有政府官員參與一些事情。比如,在我女兒小學的畢業典禮以及當地中學的年度頒獎典禮上,都能看到政府官員的影子。
去年夏天回中國時,也聽到周邊的朋友熱議當地電視臺的問政節目。如果能將這些溝通方式經常化和制度化,也許能起到和英國一樣的效果。這個社會,不信任的成本最高。有了溝通,就會降低信任成本,能讓人看到更多的希望。
而在英國看卡梅倫吵架,成了我生活中的必修課。它讓我能更清醒地認識英國、理解英國,最終也許會愛上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