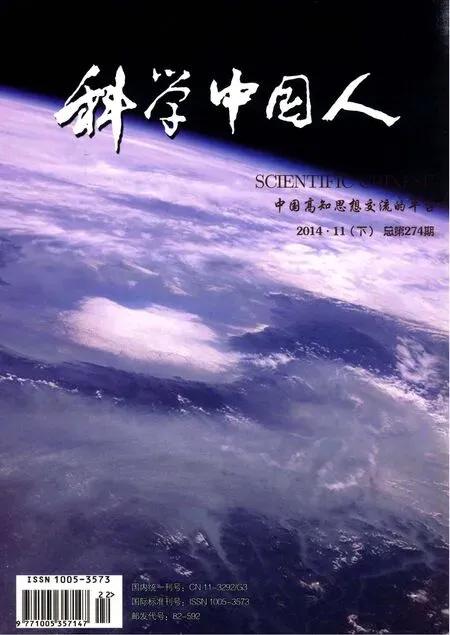開啟光明的事業
——記長沙愛爾眼科醫院院長林丁
本刊記者 張 姝
開啟光明的事業
——記長沙愛爾眼科醫院院長林丁
本刊記者張 姝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北宋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曾論述:自然界的災異不必畏懼,前人制定的法規制度若不適應當前的需要不能盲目繼承效法,對流言蜚語無需顧慮。改革與國家發展行進相伴隨行。時至今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擲地有聲: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唯改革創新者勝。
林丁,就是這樣一位改革者,敢為人新,站在醫療改革發展的前沿,以醫者的擔當和銳氣,繪就出民營醫院管理發展的范本。
然而,改革向來不易,他飽嘗“嘗試、失敗再嘗試”的心酸與艱辛,時間作證,實踐為解,他終以前沿的理念打破了舊觀念的窗戶,引入一泓明亮。
一鳴驚人——結緣眼科
林丁生于60年代初,成長在動蕩年代。1977年,他成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雖是醫學世家,但當時的林丁對學醫并無興趣,他喜歡更加抽象的物理學。然而,有限的資源使得林丁別無選擇,最終被江西醫學院錄取。那年,他是學校考上大學的“第一人”。后來,在專業細分時,林丁選擇了眼科,全因“眼科設備多,和物理有聯系”,就此在理想和現實間他找到了平衡點。
5年的醫科學習生涯在“邊下放,邊學習”的日常寫照中轉瞬即逝,畢業后的林丁被分配到當地一家縣醫院。幾年后,他又經歷了考研、讀博。1995年,林丁博士后出站,留任于北京同仁醫院眼科。同年,也就是在他35歲之際,林丁成為了副主任醫師。
當大夫,林丁兢兢業業。他保留的最高青光眼專科門診量記錄——1天120個號,至今無人打破,主刀的手術數量也迅猛上升。病患經過治療恢復健康,他很高興;治療效果不盡如人意,他會不斷地再為病人想其他方案;對于目前醫學尚不能醫治的疑難病例,他會為自己幫不上忙感到遺憾……對待患者,林丁極為耐心,總會為他們詳細講清病情,做到溝通有效。就這樣,林丁在臨床上做得風生水起。4年后,他晉升為大眼科行政副主任。
百折不回——在改革中受挫
行政工作在醫院體系中,可以說是“牽一發,動全身”。“倒票的人竟把一個號最高買到1000多元!”在指責黃牛黨低劣行為的同時,林丁開始思考問題背后的原因,以尋求突破方法。
一號難求,說明供小于求。是因為我國眼科醫生數量少?其實不然,國際眼科理事會(ICO)調查顯示,2012年,在各國眼科醫生數量排名中,我國以28338名名列第一,第二名的美國25152名,俄羅斯14600名位居第三……數萬名眼科醫護者分布在各個醫院,為何還會出現“大醫院爆滿、小醫院冷清”的現象呢?
林丁一語道破癥結所在,“我國未實行‘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導致醫生水平層次不齊”。殊不知,在美國、英國、加拿大等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以美國為例,一名醫學院畢業生從院校畢業后,想要成為醫生,起碼要經過三關:首先通過一次全國性執照考試,并面試申請醫院,獲得住院醫師的機會,其次是為期3~4年培訓,最后通過培訓考試,成為一名合格醫師。“同批次醫生的水平近乎相同,所以在哪看病都一樣,不必擠大醫院”。但在我國的情況是:學生從醫學院畢業后,只是在工作崗位接受所在醫院的培訓后就成為醫生,醫生的成長受限于醫院層次。
在林丁的“患者就醫模式”改革中,改革教育制度是其中關鍵的一環。如今,許多變革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然而隔靴搔癢到頭來還是無濟于事。林丁卻能夠透過想象看清本質,他要做的是切中要害,將問題拔根而起。然而,船大難掉頭。“改革需要時間,甚至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固有模式一旦形式,很難改變。”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林丁也嘗試過一些新措施,比如“開放掛號”。考慮到老專家精力有限,他就讓年輕的醫生也沖在前線,“至少讓到院的病人都有醫生看”。但最終實施的效果十分有限,“很難,需求太大了!”
激流勇進——力促醫療服務改革
解決“護士配備不足”是林丁提升醫療服務的另一個切入口。
“醫生110名,護士只有90名”,二者數量嚴重倒掛,“這就造成護士服務范圍不能遍及全部,服務質量也遲遲得不到提升”。然而在國際上,通常要求護士的數量至少比醫生多一倍以上。林丁再次直面改革痛點,向醫院申請增加護士數量,但他最后得到的反饋卻是:限定的人數不能改變。
林丁沒有放棄。此路不通,另尋別路。他通過勞服派遣的方式引進護士,然而收效甚微,很多不可抗因素就像絆腳石,使前進的道路再次被阻斷。
“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一旦認準的事,林丁就要進行到底!深思熟慮后,他決定到其他醫院再繼續嘗試。離開后的林丁,先后跑了很多家醫院,公立、公私合營,但無一例外都推行受阻。最后,他把希望寄托到了全民營醫院——長沙愛爾眼科醫院,是愛爾眼科醫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國100多家連鎖醫院的其中之一。
2005年起,林丁成為長沙愛爾眼科醫院院長,在那里,他高屋建瓴,運籌帷幄。愛爾醫院對林丁來說就像夢想的溫床,很多想法都得以萌生發芽。
林丁最先提出“局部預約掛號”,所謂的“局部”就是從老醫生開始試施行。預約意味著把醫生綁定,醫生需要根據先前預約的時間而安排工作,但醫生總會因為加手術、科研任務、會議等各種不可預知任務的出現而不能如約出診。于醫生是失約失信,于病患是耽誤診治,無論對哪一方都是損失。所以,林丁審視奪度,并沒有全面開放預約掛號。
事與愿違,出發點很好的“預約掛號”不成想卻引發了患者更多的不滿。因沒預約號而沒掛上號,有爭吵;雖然都是預約號,但有先后之分,又有爭吵;按預約時間前來就診,但沒排到自己,同樣有爭吵……林丁也很無奈,漸漸地他發現“患者也要培訓”,這無疑是個格外新奇的想法。
“只有當患者有被服務意識時,我們的服務才能讓他感到溫馨”,林丁一語中的。新的服務模式對接患者的固有思維模式,想必會發生錯位,“他們會覺得我們做的不夠好”,實則林丁是殫精竭慮。也許是還沒搭建起溝通的橋梁,而“患者培訓”就是告訴病患醫院做了什么、遇到問題如何解決。經過長時間的磨合,病人與醫院之間的隔閡明顯得到緩解。
在林丁看來,行政工作就像患者與醫生之間的橋梁,在充分了解雙方訴求后尋找解決辦法或制定新規,他也總愛強調“行政職工服務一線,一線服務患者”的服務觀念。他解釋道,服務在院內層面以醫生為核心,對社會層面以患者為核心。林丁相信,以這種理念做出的改變,一定是合理的改變,也一定是有益的改變。

破釜沉舟——揚民營醫院風帆
產生于上世紀80年代的民營醫療體系,自誕生之日起就常常被外界認為“是以盈利為目”,患者不愿選擇到民營醫院就診也緣于此。林丁為此也十分苦惱,他說服集團總裁,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降價。他只想用實際行動告訴患者,“我們注重的是服務”。
林丁的一個決定,竟使價格降得比公立醫院還低。盈利嗎?林丁深諳資本投資的本質是滾動再擴大,社會資本進入醫療體系畢竟還要以回報作為資本流動的前提,所以他的“降價”并非“慈善”,而是借鑒“薄利多銷”的經營模式。林丁認為,唯有做到可持續才有發展,若要把醫院變成“商戰場”,就不必談生存的立根之本。
就這樣,醫院在不斷的爭議中逐漸完成了轉型,如今業績增長幾近10倍,已成為一家產值達2.5億、在湖南頗具影響力的眼科專科醫院。可以說,是林丁最初的高瞻遠矚和堅持不懈才有了醫院今天的發展。在一次長沙民營醫院院長論壇上,他自豪地說道,“我們在譜寫中國民營醫院的歷史,我們是開端!”這是一份可以給林丁帶來快樂的工作,為此他干勁十足。
2006年,在林丁的帶領下,愛爾眼庫(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深圳380區愛爾眼庫)成立,它是目前省內唯一獲得政府批準并正常運作的眼庫。眼庫,匯集了眾多捐獻者的眼角膜,以移植于有需求的病患。在我國,由于人們對“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愿意捐獻角膜的志愿者少之又少,也正如此,每年有數以千計的患者因沒有角膜來源而喪失了重獲光明的機會。其實,我國也有很多名義上的眼庫,但實際都是有名無實的空殼子。而在愛爾眼庫,每年輸出并成功移植的角膜能達將近200例——這些都是醫護人員一個一個勸捐來的。未來,林丁希望把愛爾眼庫打造成為一座國際化眼庫。
后來,林丁還首創先河,給予科主任免單權利。他們始終崇尚,“使所有的人,無論貧富貴賤,都能夠享受到眼健康的權利”。他還在門診樓里設立便民信箱、便民雨傘、書報架、茶水供應點、患者候診椅、重癥救護綠色通道;建立“先療病,后結算”服務模式,實現了掛號、收費、取藥等窗口服務時間不超過10分鐘;采取多種形式,組織老百姓對醫院各項服務進行滿意度測評。

乘風破浪——做醫療改革前行者
作為愛爾眼科醫院集團在地方設立的連鎖子醫院,長沙愛爾眼科醫院目前運轉良好,年病人就診流量也位于湖南省前列。但林丁還在不斷地更新完善團隊,廣納賢才。在他看來,這是長線化的努力。
身為院長,他習慣先布好全局,之后隨時發現問題隨時解決,具體的工作則分配給合作伙伴,他更多做的是“監控者”,這樣就可以留有大段的時間給病人看病、做科研。隨著愛爾眼科學院的成立,林丁又重新成為導師,要騰出時間“認認真真做學術“。有先前扎實的理論基礎,加上豐富的臨床經驗,林丁對他的“二次起航”很有信心,這次他會飛的更高更遠。
和林丁同時期的學者,現在大多數都成為頂尖科研者、帶頭人,以林丁的學術造詣本可以與他們比肩,但因為一次轉彎,他們的道路從此是兩個不同的方向。心中存有一絲信念,不知道路的盡頭是不是光明,林丁只是固執地堅持向前。回顧他身后走來的路,過程中林丁就像推著一塊巨大的石頭,每前進一步都無比艱難,但進一步就是漫漫歷史長軸上的一大步。林丁也深感未來腳下道路不會平坦,但他總是樂觀地堅信“不能全面改變,先改變一點,從小事做起,慢慢會更好。”
書寫民營醫院之歷史,開創民營醫院之未來。改革的歷史長河會深深烙印下“林丁”的名字,以醫療改革探路者之名,更是以救助數以萬計病患的醫者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