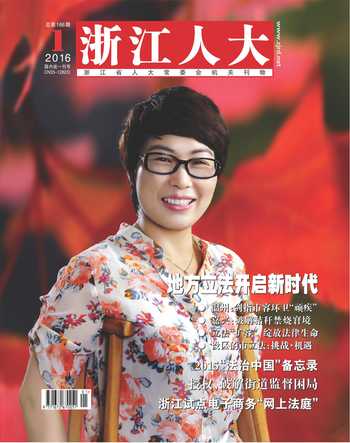用法律為文學作品正名
曲三強
任何不勞而獲盜取他人精神勞動果實的行為都是缺乏正義的,從法律的層面上都應給予否定的評價。
2015年12月20日,曠日持久的“瓊瑤訴于正著作權侵權案”終于隨著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法槌的敲下而塵埃落定。法院判定駁回各上訴人的請求,維持原判。而恰好在此一年前,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原告瓊瑤勝訴,認定5名被告構成共同侵權,并責令被告于正公開道歉,停止傳播所涉侵權作品《宮鎖連城》,連帶其他5名被告共同賠償原告損失500萬元人民幣。
文學藝術作品是人類文明智慧發展的結果。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文學藝術成果都是作為公共資源為社會公眾無償使用和消費。只是到了近代,由于生產力結構的變化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才產生了對文學藝術成果私有化的訴求。隨著版權制度的出現,文學藝術作品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財產,進入到商品經濟的市場,稱斤論兩。
接踵而來的問題是,文學藝術作品的公共性與私有性的界限在哪里?人類文明歷史幾千年,創造了眾多輝煌的文學藝術成果,成為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然而,“弱水三千,須取一瓢飲”,今天的任何創作活動,都無可避免地會利用已有的文化資源,在與歷史的互動中展示自己的品格。著作權所能保護,或者所要保護的,也只能是作者獨創的那個部分。
按照著作權法的要求,只保護思想的表達而不及于思想本身。著作權法之所以采取這樣的原則,原因很簡單,思想作為一種精神活動及其成果,邊界是難以框定的。況且,人權的觀念也要求思想自由不應受到羈絆,更不能被專有和獨占。因此,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獨創性,只能是表達某種思想的特定形式和方法。由于表達形式和方法是具象的且可以被把握,因此,獨創性便有了它的軀殼和依歸。運用著作權來保護文學藝術創作成果,是制度設計者不得不采用的謙抑原則。從這種意義上說,“思想與表達”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科技文明的發展,人們的表達形式會越來越豐富,手段越來越多樣,樣態也越來越繁復。
“瓊瑤訴于正案”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給我們提出了有益的啟示:
首先,作品的“思想與表達”的界限在悄悄變化。劇本和小說同屬于文學作品,而文學作品中“思想與表達”的界限是不易劃定的。在本案中,法院在詮釋法律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立場,于傳統定義而言,已經有所突破。在其看來,確定文學作品保護的表達是不斷抽象過濾的過程。文學作品的表達既不能僅僅局限為對白臺詞、修辭造句,也不能將文學作品中的主題、題材、普通人物關系認定為著作權法保護的表達。文學作品的表達,不僅表現為文字性的表達,也包括文字所表述的故事內容,但人物設置及其相互的關系,以及由具體事件的發生、發展和先后順序等構成的情節,只有具體到一定程度,即文學作品的情節選擇、結構安排、情節推進設計反映出作者獨特的選擇、判斷、取舍,才能成為著作權法保護的表達。
其次,判定某個行為是否構成著作權侵權,其標準是要看該行為是否具有盜用他人權利作品的實質。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把握:一是行為人主觀上有盜用他人作品的意圖。二是行為人客觀上已經侵入他人作品著作權的邊界。三是行為人所實施行為的方式是剽竊,而不是獨立創作。
雖然世道在變,然而公平正義的價值觀沒有變。著作權將文學藝術作品納入私權保護的范圍,是對那些用辛勤汗水換來的智力成果的尊重。任何不勞而獲盜取他人精神勞動果實的行為都是缺乏正義的,從法律的層面上都應給予否定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