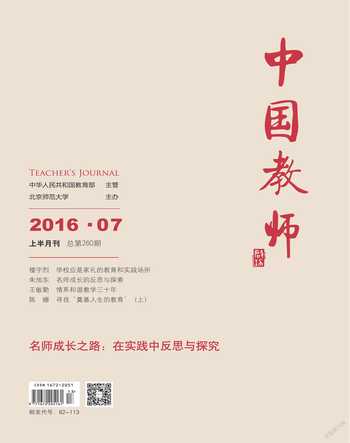從“名師”到“明師”
李瓊 裴麗
近年來,各地紛紛啟動中小學名師培養工程、名師工作室或名師工作坊項目,旨在促進有經驗的優秀教師突破原有零散、直覺的個性化經驗,走向經驗的系統化、概念化與理論化,從而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學主張或思想。從這個角度講,成為“名師”不僅僅是擁有外在的稱號、頭銜或地位,而是從感性的實踐者轉變為理性的研究者、從經驗豐富的“名師”轉變為有教學思想的
“明師”。
北京師范大學與重慶市教育委員會、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政府協同共建“重慶市教師教育創新實驗區”,開展“名師工作坊”項目,體現了上述設計與行動理念。該項目從重慶市江北區的中小學校遴選具有發展潛力但又處于發展瓶頸期的經驗型教師,以課例行動研究為載體,通過創建“大學-政府-教師進修學院-中小學校”的合作伙伴關系,提升有經驗教師的教學反思與探究能力,促進教師凝練自己的教學風格和思想,發展其教育教學的個人理論,從經驗型教師走向有自己教學思想的“明師”。那么,“明師”到底“明”在哪里呢?
一、透過日常反思與探究使教與學有理有據
一位20年教齡教師的教學實踐,可能是一份教案的20年重復,可能是多年熟練技巧的掌握,也可能是20年的日常實踐反思與行動研究。后者與前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對教與學本質的認識深度和把握不同。前兩類教師僅僅將教與學看作知識傳遞的操作性、技術性過程,是重復經驗的“教書匠”,很少進行實踐反思與理論探究,如“為什么要進行學情調研”“為什么同樣的教學設計在兩個班級中的教學效果不一樣”“學生錯誤概念理解的原因是什么”等,缺少對教與學有理有據的深入研究。而面對同樣的日常教學實踐,真正的名師則“明”在善于運用研究性思維,對在紛繁復雜的教學實踐中遇到的問題進行審慎地思考、發現、分析與解決。杜威在《我們如何思維》中闡明了進行科學思維的五種步驟,即從經驗中感覺到困惑;分析困惑所產生的原因和背景;通過觀察、檢驗、探究、分析等方法澄清需要研究的問題;提出可能的假設;通過反復的“實驗”檢驗假設的正確
性。[1]名師基于自己在實踐中的困惑或問題,運用各種方法不斷嘗試,推動思維的進程,以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獲得新的知識,重新從學生學習的角度理解教學,從學生生活經驗建構的角度理解學習。
例如,為什么需要進行學情調研?需要調研些什么?調研的方法有哪些?參加名師培養工作坊的教師們寫下了自己的所思所想:
“以前我們進行課前學情調研,沒有想過為什么,因為區里或學校要求這樣,我們就這么去做了,還真沒有想過為什么,可能就是更加了解學生吧……”
“在這次工作坊的學習中,我發現學情調研原來有深層的理論支持,就是知識建構的理論。人類建構知識,總是以自己原有的知識為基礎,而學生建構新的知識,同樣是以自己已有的知識或生活經驗為基礎,這就是我們教學的邏輯起點。有時教師講了好幾遍,有些學生還是不理解,這是因為教師的教學是建立在成人認知基礎上的,沒有結合學生已有的認知,特別是沒有深入了解和分析不同層次學生理解的個體差異。可見,學情調研是多么重要。”
教師們真正理解了學情分析的真諦,正如心理學家奧蘇貝爾所說:“如果我不得不把教育心理學的所有內容簡約成一條原理的話,我會說:影響學習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學生已知的內容。”[2]教師在實踐反思與研究中找到了有效教與學的理據,使自己的教與學更加理性。從“名師”到“明師”,教師不僅要知道教什么、如何教,更重要的是要知道為什么這么教,使教學有理有據。
二、概念化、系統化地表達自己的教學思想
優秀教師在多年的教學實踐中會形成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策略,對教與學也會形成自己的看法、判斷、認識和觀點,這些看家本領與個人化見解,往往內隱于教師個人化的經驗中,具有很大的零散性與隨意性,是碎片式的,是相對淺層與模糊的,不具備系統性、深入性與清晰性。[3]一些經驗豐富的優秀教師會感到自己處于發展的高原期,難以將自己的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提煉教學風格與教學思想,就是引領名師把個人化的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或者用理論來解釋、改造與發展自己的實踐經驗,將自己內隱的、甚至難以言傳的經驗轉化為個人實踐理論,最終成為外顯的、普遍性的公共知識。只有經過有意識的研究、提煉與理性分析,教與學的實踐直覺才能轉化為理論自覺,教學思考才能概念化為教學思想,形成共享的教學理論與實踐。
提出情境教學的特級教師李吉林曾說:“我不敢說自己是一個思想者,但我覺得,即便是小學教師,也應該有自己的思想和教育主張。”[4]沒有自己的教學主張與教學思想,不能稱其為思想者,也不能說是名師,更談不上教育家。目前,教育教學實踐中涌現出許多教學風格與教學思想,如“詩意語文”“童趣數學”“人文素養的歷史教學”“自學·議論·引導的數學教學”“融錯教育”等。參加此次名師工作坊的教師們也在逐漸明晰自己的教學風格與教學思想,如“以寫促讀”閱讀教學、“回歸歷史教育本源”歷史教學、物理教學中的“自我教育”等。可以看出,這些教學風格或教學思想都源于日常教學實踐,又是對實踐經驗的理論概括與提升,最終都指向促進實踐中的教與學。不同于學術研究的概念化,這些教學思想根植于教師的實踐智慧,經過了實踐理論化,理論實踐化,最終指向實踐的提升,經歷了“實踐—理論—實踐”的持續互動過程。[5]
名師需要有理論素養,在實踐反思與研究中,不斷凝練與學理化自己的教學風格或教學思想,讓個人化的經驗從零散走向系統,從經驗的隨意性走向結構化,從經驗的直覺走向理論的自覺,成為教育教學知識的發現者和建構者。這種理性思考的品質與理論素養,是“明師”的高明所在。
三、將教學思想內化為對學生的生命關懷與精神引領
從“名師”到“明師”,教師不僅要探究教與學背后的理據,提煉自己的教學思想,其生成的個人理論更要通過名師的育人表現出來,將教學思想內化為教育理想情懷,實現對每一個學生的生命關懷與精神引領,這是“名師”成為“明師”的最高境界。教學風格或教學思想本質上講的是名師在日常教學的經歷、探究、感悟中形成的對教與學的一種觀點、一種見解、一種思想,這種教學觀如果不內化為對教育生命的關愛,只能是沒有生命力的教學思想。名師不僅要有豐富的知識、技能、實踐智慧與思想,更要用人格魅力與教育情懷感染學生。教學是教師的專業道德實踐,這種內在的精神力量是名師獨特的專業性所在。
研究者區分了教師的兩種工作信念與投入狀態:“用腦工作”與“用心工作”。當把教學理解為一種專業技能層面的工作時,教師做好這項專業技能工作,“用腦工作”即可;但教師若要充滿工作激情并對學生產生感召性影響,則必須“用心工作”。[6]名師”走向“明師”的前提就是“用心工作”,就是對教育工作的意義有深刻的理解,而且這種理解不是抽象的思辨或理論的推演,而是真正浸潤教師心靈的真知灼見。“明師”的這種對自我、對工作、對學生、對使命的認知,是一種人格化的教育精神。這種人格特色體現了對真、善、美的自覺追求,是思想、情感、道德、審美凝聚而成的教育情操,是名師真正成為“明師”追求的最高境界。[7]
有教學思想的“明師”勝于有經驗的“名師”或優秀教師,是因為他們善于進行日常專業實踐反思與行動研究,能夠在教學中做到有理有據,在教育教學實踐中不斷凝練自身的教學風格和思想,發現教育實踐知識,建構教育實踐理論,促進自身專業成長。許多經驗型教師在教育教學實踐中遇到發展的瓶頸,是因為他們往往只停留在技術層面的課堂反思上,也僅僅局限于經驗層面的教學寫作,沒有凝練出自身的教學風格,也沒有孵化出自身的教學思想,更無法將教與學融于對學生生命的關愛。從“名師”到“明師”,教師要在日常專業實踐中進行持續不斷地研究,不斷凝練自身的教學風格,構建自身的教學思想,并將之融于對學生的生命關懷與精神引領,才能超越經驗,成為真正有教育思想與教育情懷的教育家。
參考文獻
[1]杜威.我們怎樣思維[M].姜文閔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美]奧蘇伯爾.教育心理學:一種認知觀[M].佘星南,宋鈞譯.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
[3][5]余文森.論名師的教學主張及其研究—以福建省為例[J].教育研究,2015(2):75-81.
[4]成尚榮.名師應當是思想者[J].人民教育,2009(1):43-46.
[6]馮大鳴,誰是今日美國的好教師?—2003年度全美優秀教師評選結果分析[J].中小學管理,2004(1):
21-23.
[7]李源田.論教師專業發展的“五度”境界:名師的素質表征[J].課程·教材·教法,2013(2):86-91.
(作者單位: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江麗莉
jiangll@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