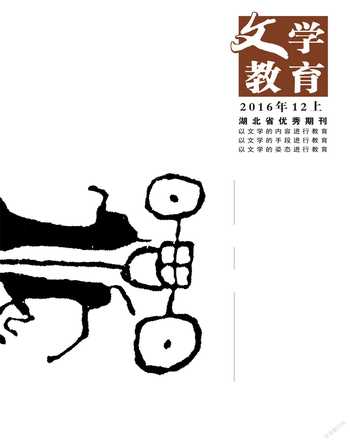方方《奔跑的火光》中英之形象的悲劇性
內容摘要:著名作家方方筆下的《奔跑的火光》為讀者描述了現代鄉村婦女所面臨的生活境遇,反映了一個生活在鄉村的婦女的悲劇人生。這部中篇小說通過講述一位農村婦女英芝的人生悲劇,由此來映射出處于社會改革時期偏遠窮困地區鄉村婦女的人生悲劇性。而在此之中,自身的缺陷和環境的影響是造成英芝悲劇一生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奔跑的火光》 英之 悲劇性
作為“新寫實”小說的代表作家——方方,她繼承了張愛玲和蕭紅等作家的文學傳統,善于描寫人類瑣碎的事物和日常生活,并一直關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尤其專注描寫日常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她的作品以現實主義寫實為特征,側重于對現實生活的描寫,著重描寫人物的命運以及看似病態、骯臟、丑陋的人性,從而來闡釋當代人們的生存狀態。方方的中篇小說《奔跑的火光》通過對于一個鄉村婦女英芝形象的刻畫,反映了在社會大變革的背景下,在新的經濟觀念的刺激下,在偏遠鄉村一部分婦女的生活狀態。小說主人公英芝是一位出身于鄉村的年輕女性,她高中畢業,家境也相對富裕。后嫁為人婦,但她的丈夫貴清卻是一位身上存滿了缺點的鄉村青年。作者用細膩的筆觸為我們展示了農村婦女英之的生活由希望直至絕望的全過程,以及最后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悲劇。究其原因,我認為,造成英芝的悲劇性的原因主要有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
一.自身內部的性格弱點決定了其悲劇性
在小說人物塑造中,人物的性格缺陷往往是構成他們悲劇的重要原因。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曾談到:“整個悲劇藝術包含形象、性格、情節、言詞、歌曲與思想。在六個成分里,最重要的是情節,性格占第二位。”[1]由此可見,亞里士多德認為,性格是悲劇僅次于情節的第二個因素。個體的性格和生存環境之間的沖突往往會扭曲人的本性,而這些又使他們要么走向自我退化,要么就在斗爭中滅亡。毛澤東的《矛盾論》認為:“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2]外部的事物只有通過人自身的吸收和消化才能變為個人改變命運的條件。也就是說,是英之自身中所存在的問題導致了她的人生命運的最終悲劇。英芝人生命運的悲劇是與她自身的性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的。
首先,在英芝的世界觀體系中存在著金錢崇拜思想。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大眾經濟地位的不斷提高,人們的道德觀已變得越來越薄弱,取而代之的則是“拜金主義”的原則。生活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英芝也不可避免的陷入金錢崇拜的漩渦。英芝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對于家境相對于較好的她來說,生存并不是很艱難。但是就算如此,在英芝的心里對于金錢還是充滿渴望的。高中畢業的英之在農村中可以算是以為一位農村新女性,雖然剛剛走出學校,但她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物質的追求。在她的觀念中,“錢”是通向幸福生活的唯一途徑,城鄉差別在英芝眼中就是金錢的差別。于是,當三伙問她是玩牌還是賺錢的時候,“英芝心里‘咚’了一下,暗道那還用說,哪個不想賺錢呀。”[3]即是在結婚以后,英芝也并沒有改變“金錢崇拜”這一觀念,于是便引發了一場“蓋房運動”。回到娘家的英之看到鄉親三伙蓋得房子,于是她也動起了蓋房的念頭。在英之看來,房子是與幸福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所以她要用自己的經濟力量去蓋一所房子。經由這一事件,英之對于金錢有了深一層的認識,她認為,金錢不僅可以給她帶來物質享受上的幸福,還可以使她擺脫依賴,翻身成為自己的主人。另一方面,她為了使自己更好更快的賺錢,她將自己的身體化為一種賺錢的工具,身體和金錢成為一種商品關系,此時的英之已經完全被金錢所控制。更甚者,她把金錢看得比自己的親生骨肉還重要:“有錢沒兒子,你照樣活的好好的,生老病死,錢都能幫上你,可是沒錢有兒子,卻是沒有活頭”。[4]因此,在金錢至上的思想下,英芝漸漸地迷失了自己,錢財成為了她衡量人生所有價值的一切標尺,而這一“標尺”最終也使他墮入了悲劇的深淵。
其次,愛情的誘惑也是將她推進悲劇漩渦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說金錢使英之喪失了生命的價值,那么愛情則是導致她悲劇人生的另一惡魔。十八九歲豐華正茂的英芝未婚先孕,她不想讓別人指指點點,迫于壓力,只好草草嫁給貴清。但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反而讓英之的公婆對她產生了厭惡之心。公婆在生活中對于英之的傷害與不公正待遇,這些都給英之的婚姻帶來了傷害。婚后的貴清只知道喝酒打牌.沒有家庭責任感,英芝看清丈夫的本來面目,但她卻又不得不伺候好他,還要替夫勞作。婚后的生活與英之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樣,她不愿這樣委屈的過活,同時她也不能丈夫與公婆對她身心上的折磨,英芝提出離婚。與此同時,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毒打之后,英之的父母也并沒絲毫要對她伸出援助之手之意,所有的這些致使英芝日日處于生活的痛苦與絕望中,最終將她推入了深淵。
再次,在英芝思想中一直存在著對于讀書與知識的嗤之以鼻,從而造成她精神上的愚昧無知。例如:“英芝沒有考上大學,大學對英芝來說沒有什么特別的吸引力。花費那么大的勁頭去讀書又是何必?出了校門她知道自己這輩子再也不會走進學校,心理倒是松了一口氣,不去上大學是她本來的心愿。”[5]正因為她的愚昧無知,導致了她擁有錯誤的價值觀,把金錢作為衡量一切的尺度,把自己的痛苦歸結為是失敗的婚姻造成的。春慧是作品中一個與英芝形成鮮明對比的人物形象。在此之前,英之一直視春慧為一個沒用的人,但接受高等教育后的春慧“電腦玩的溜熟,大學還沒有畢業,就被一家大公司相中,暑假里成天開著個小汽車去人家公司上班,風光的不得了”,“一頓飯吃下去,硬是花了她一千多塊錢,她眼皮都不眨一下”[6]由此與英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于知識不同的態度使春慧和英芝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生活之路,同時也是使英芝走上悲劇之路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外部環境造就了人物的悲劇
仔細分析小說文本可以發現,英芝的悲劇不僅僅只是由英芝自身的性格缺陷造成的。同時外部環境的影響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正如方方所說:“改變人的因素其實就是兩方面:一方面是人自身,人不能離開自身的基因遺傳、興趣、性格以及天性的東西;另一方面是文化環境、生活環境的影響。人擺脫不掉這兩種因素對自我存在的困擾。”[7]對英芝命運造成影響的外部環境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社會環境,二是家庭環境。
就社會環境來講,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科技與物質文明也在隨之高速發展,而精神文明則一直處于較為弱勢的地位。精神文明社會的衰退自然會造成大眾文化素質的嚴重質量問題,如欺騙等。正是由于社會環境中的爾虞我詐,使主人公英之逐漸走向悲劇的宿命。當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時手足無措時,三伙用金錢引誘英之進了吹唱班。但這就像一個沼澤地一樣使英芝漸漸的陷進去不能自拔。在吹唱班里,英芝為能夠輕松賺大錢而欣喜萬分;她認識了只知玩樂,不思進取的貴清并與他產生了糾纏不清的感情,由此導致了她的失敗的婚姻;她遇到了以色取人的文堂,在他的唆使下,最終她背離了道德倫理,公然與文堂茍和。也由于英之的這種行為遭到了丈夫對她的毆打,為她的人生造成了毀滅性的悲劇。可見,社會文化環境是造成英芝悲劇的原因之一。
家庭環境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家庭是社會中最常見的單元,是個體發展最早也是最持久的環境。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認為,家庭環境與教養方式對個體人格的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通過對文本的分析可以發現,英之的父母對她的教育始終是一種不在乎的態度,對于她不去上大學而是去吹唱班這一行為,不僅不反對,更是積極鼓勵,并為女兒能給家里交錢而沾沾自喜:“我家英芝就是精,得虧沒有去上大學,要不就跟村里春慧一樣,成了個賠錢貨”。[8]這種思想竟是如此的愚昧無知。在英之隨后的婚姻中,丈夫和公婆并沒有給她任何應有的關心,相反總是用高壓政策來約束她,甚至歧視和虐待她。例如迫使她去果園里工作,晚回家時就沒有飯吃,經常斥責和毒打她等。在這種家庭環境和家庭關系中,英之沒有感受到絲毫的溫暖和愛,由此也導致了她的悲劇命運。
方方筆下的英芝可以看做是一個追求女性解放的一個形象,她的人生悲劇也是在追求解放的過程中形成的。在男權社會下,女性一直處于一種被壓抑的狀態。中國女性一直在為基本的生存、為能像一個“人”一樣的活著而掙扎。在《奔跑的火光中》,英芝并沒有太多奢望與追求,只是在爭取一份“人”的生活。她認為時代改變了,認為社會的商業化可以給她更多的生活選擇,未來有更好的生活在等待她。正是這些“以為”喚醒也誤導了她,將其一步步驅趕到慘烈的人生境地。同時,英芝的悲劇命運是由于她在男權文化以及傳統道德觀念仍然強盛的鄉村不甘順從而造成的。“在中國討論婦女解放,女性的政治地位、經濟能力、社會價值等都還在其次,更為首要的是傳統道德對女性無所不在的束縛,這種束縛構成了一種深層次的價值制約。”[9]主人公英芝在在最開始的時候是對新生活懷有無限的憧憬的,但是由于農村封閉保守的思想以及她自己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促使她加入了吹唱班,也由此開始了她悲劇的一生。方方在《奔跑的火光》中用真實的筆法描述了英之的生存處境,講述了她心中由希望至絕望的心路歷程。英芝這一形象是具備當代鄉村婦女典型特征的代表性形象,方方通過這一人物形象,以悲劇形式揭示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問題。
參考文獻
[1]方方:《奔跑的火光》,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2]周群:《英芝的墮落史——評方方新作《奔跑的火光》,語文學刊
[3]方方:《我們的生活中不知有多少個英芝》,小說選刊
注 釋
[1]亞里士多德:《詩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
[2]毛澤東:《矛盾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方方:《奔跑的火光》,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4]方方:《奔跑的火光》,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5]方方:《奔跑的火光》,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6]方方:《奔跑的火光》,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7]方方:《我眼中的<風景>》,小說月刊
[8]方方:《奔跑的火光》,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9]李有亮:《20世紀女性文學中男權批判意識的流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介紹:劉幸,云南民族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