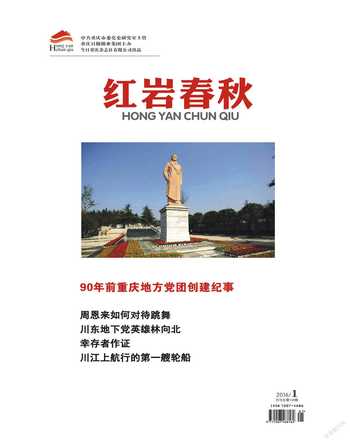寫給一座城的情書
2016-09-10 11:17:44馬拉
紅巖春秋
2016年1期
關鍵詞:重慶
馬拉
我把《重慶晨報》“城與人”專欄《重慶攝友愛拍門》那一期,攤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里一張比半邊城門還大的會議桌上,請同樣有城門情結的研究員楊筱確認一個細節。當讀到“通遠門對面的街上,有個好像叫‘一四七’或是‘三六九’的小酒館,玻璃櫥窗后面擺起鹵得黃桑桑、香噴噴的豬耳朵、鴨腳板,坐著一些老頭在喝酒。”楊筱一拍桌子說:“我可以肯定,不是‘一四七’,是‘三六九’。因為小時候我經常去那里給我們老漢(四川方言,即父親)打啤酒。”
“三六九”正對通遠門
“三六九”正對通遠門,按老重慶的話來說,是抗戰時期來自江蘇的“下江人”開的館子,跟城里古籍書店旁邊那個有名的“陸稿薦”屬于一路的風味,素菜精致,招牌菜有鹵汁豆干和烤麩,烤麩是一種很好吃的面筋。“當時我就背著軍用水壺去打啤酒,老漢是軍人,家里有的是軍用水壺,全身披掛,一去就打兩水壺”。
這是楊筱對通遠門最初的感覺,帶著夏天和啤酒的味道。當時她的家并不在通遠門邊,通遠門只是她日常生活地圖上的必經之地,在媽媽教書的南紀門和爸爸工作的重醫之間。
重慶晨報副刊曾連載楊筱的長篇學術隨筆《通遠門》,里面的《柔軟的城墻》《校場》《楊柳街》《城內心事如麻》等多篇城門故事,是一個重慶女兒寫給母城的一篇篇情書。當年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副館長田大畏,是抗戰時期曾在通遠門和九塊橋之間遛達的田漢之子,對楊筱《通遠門》的評價是“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么柔軟的城市史”。……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環球人文地理(2022年8期)2022-09-21 03:49:42
公民導刊(2022年4期)2022-04-15 21:03:14
當代黨員(2022年6期)2022-04-02 03:14:56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11期)2019-12-30 06:08:38
當代黨員(2019年19期)2019-11-13 01:43:29
重慶行政(公共人物)(2018年5期)2018-11-06 07:42:18
城市地理(2016年6期)2017-10-31 03:42:32
今日重慶(2017年5期)2017-07-05 12:52:25
海峽旅游(2015年8期)2015-08-22 15:43:40
漢語世界(2012年2期)2012-03-25 13: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