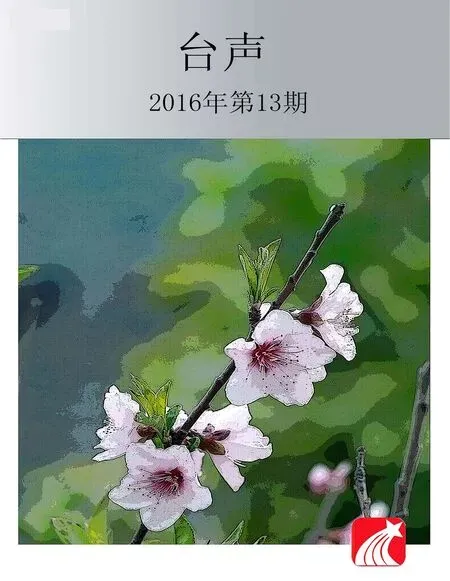美麗胭脂扔上了天
美麗胭脂扔上了天

吳鈞堯WUJUNYAO臺灣文學雜志《幼獅文藝》主編
出生金門昔果山,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火殤世紀》寫金門百年歷史,獲文學創作金鼎獎。曾獲《聯合報》《中國時報》小說獎及梁實秋等散文獎。著有《遺神》《熱地圖》等十余種,繪本作品《三位樹朋友》獲第三屆臺灣出版獎
住農村,按句大陸的流行語,就是更好“接地氣”,農民根據節氣耕種、收獲,經常祭祀,以感謝天地作育。科學不發達的年代,功與過,老天都有份,但一般百姓,豈敢質疑“天”?比如初播種時遭冰雹落擊、臨收割前遇大雨攪局……埋怨免不了,但還是一步一步踏上田,抬頭看天。
父親等老一輩的莊稼漢,跟“天”有秘密聯系的,他們能讀懂云層變化,知道風向代表的意義,連濕度、溫度,竟然聞了聞,就能知曉。日前,接到一位教授朋友來電,他說常跟某轉角的一金門人開的水果攤買水果,忍了多時,這次終于問他,“認識一位金門籍作家吳鈞堯嗎?”老板聞言大驚,“那是我的小學同學”。教授欣喜來電。同學姓周,小學畢業至今,都沒見過。他的父親正是神明的代言人,俗稱“童乩”。
“童乩”這詞,有一度帶貶意了,當他與詐騙信眾的神棍合一時,害苦許多人家,但在古早的鄉下,他的地位崇高,雖說科學昌明,但仍有科學無法抵達之處。我想起周同學的父親,許多回在廟會祭拜時,以鐵刺穿鑿雙頰,鮮血直流,竟似無感。
每一個人都有咬破口腔的時候,我有一回,疼了快兩周才痊愈,一口咬痕已經疼得如此,鐵刺鑿穿,又該多疼呢?
農村民俗中,我很喜歡七夕的“拜七娘媽”。七娘媽祭祀牛郎與織女,這個美麗的中國民間故事,戀人靠喜鵲搭橋,才得一年一會。小小年紀,自然不懂人間悲歡離合,但我喜歡祭祀的氣氛。不喧嘩、不很隆重,在三合院前擺兩條長板凳,安置祭祀的菜肴,最有趣的,是祭拜時會擺上紙跟竹架繪制的七娘媽亭,里頭不多不少,正是七仙女。
我喜歡數她們。一二三、五六七,果然不多不少。我總淘氣地想,萬一多放了一位或少放了,天庭會大亂嗎?仙女的臉蛋用糯米捏塑,再妙筆勾勒眉眼,七仙女長得一模一樣,偏偏我跟堂妹、弟弟說,“第二排第三位,肯定就是織女了”。他們齊聲問理由,“你們看哪,她長得最美”。他們爭看、比對,“哎呀,真的,那位仙女長得最漂亮”。
祭祀后,輪到我最愛的習俗上場了,丟胭脂上三合院屋頂,媽媽說,胭脂是給七仙女妝美用的,我拿著銅板大小,但厚了點、潤了些的胭脂,心想只要扔上了天,七仙女該有仙術,把平凡的胭脂變成厲害的化妝水。我滿懷想象跟感動,丟胭脂上樓頂。
農民對于“天”,不只是祈禱、敬求,他們看到“天”也有它的不足,祭胭脂天庭,正是推己及人,不以自己的滿足為滿足。搬遷到臺灣之后,大約沒有屋頂可以投擲胭脂,這項祭拜,慢慢就沒了。有一回我下榻金門水頭村,在民宿主人的辦公室看到“七娘媽”,主人說,金門舉辦的民俗活動,有一項正是教導怎么溫習舊文化,主人就敬卑地,糊制了她的“七娘媽”。
我猜想,主人也有她扔上天庭的胭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