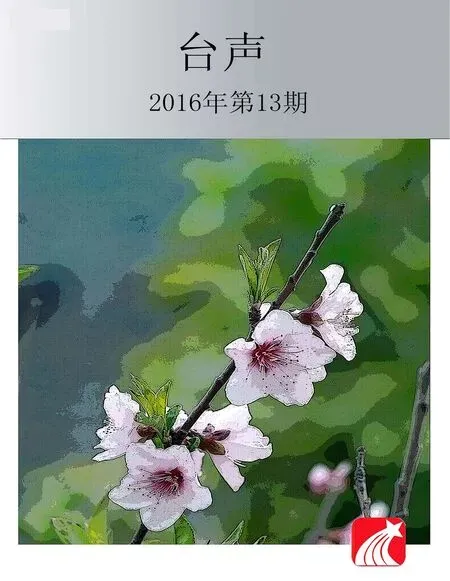“我們要回國”
口述||陳蕙娟 整理||記者 易靖茗實習記者 昌校宇
“我們要回國”
口述||陳蕙娟整理||記者易靖茗實習記者昌校宇
· 編者按
為他們鼓掌
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出生于臺灣或籍貫臺灣,因為歷史的因緣際會,最終定居于大陸幾十年。多年來,在大陸這片熱土上,他們愛國愛鄉,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增磚添瓦,為祖國和平統一事業嘔心瀝血。如今他們多已進入暮年,在他們身上,有太多的寶貴財富需要留存,有太多的人生感悟需要傳頌,更有太多的兩岸記憶需要載入史冊。為此,本刊編輯部與北京市臺聯聯合開辦《口述歷史》專欄,系統深入地報道這一代老臺胞們的人生精彩故事。也歡迎各地臺聯和廣大作者踴躍供稿或提供報道線索。
采訪時間:
2015年7月24日(星期五)上午
采訪地點:
北京市朝陽區東三里屯中14樓11—2
記者札記:
電話約訪時,陳蕙娟老師爽快答應,這讓我們頓覺心曠神怡。
果然,采訪當天,我們剛出電梯,就看到85歲高齡的陳老已在家門口等候。她精神非常好,親自泡了壺龍井茶,并將我們面前的茶杯一一斟滿。坐定后,面對鏡頭,陳老還不忘用雙手捋了捋滿頭白發,“小女生”的情結一覽無余。
“我們要回國。”采訪中,陳老的這句話對我印象最深。她在日本出生、長成,父親時常教導他們“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當父親于1945年中國抗戰勝利后要回中國時,她沒有一絲猶豫,毅然決然地跟隨父母回到了故鄉臺灣。
陳老攤開一桌子的照片,隨著講述不時地抽出一兩張配合著展示給我們看。那都是最珍貴的歷史。
陳老會說3種語言,中文、俄語、日語。因配合采訪,她向我們展示的書籍資料竟然全是日文版,不時還會說兩句俄語逗笑我們。難以想象,年過8旬的老人竟然思維清晰,幽默感十足。
臨別時陳老跟我說,如果有需要再打電話。
(注:文章標題及小標題均為編者所加)

陳蕙娟

陳蕙娟及其家人
父親總是教育我們“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
我叫陳蕙娟,1930年8月16日在日本東京出生。父親陳文彬是臺灣高雄人,母親是臺灣嘉義人。他們兩人在日本留學時相識、相戀、結婚。當時父親在日本夜校教中文(學校中國人居多),母親是藥劑師。
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發動侵略中國的全面戰爭后,賣國賊、大漢奸汪精衛在日本人的幫助下,成立了偽政府。那時候,我已經記事了。當時家里總是來人,來人都講中國話,與父親談論一些問題。大人講話我們小孩子不好上前聽,但遠遠地我常看見,講著講著父親突然憤怒地站了起來,邊用手指劃著,邊大聲說著。我知道,父親一準兒是生氣了。待來人走后,全家坐在一起時,父親才告訴我們說,這些來人都是汪精衛派來的,汪三番五次地這樣做,就是想邀請他回國當教育部的領導。父親講,他哪能給這個大漢奸賣命呵,更不愿做大漢奸的幕僚,每回他都是堅決地給予拒絕。
還有,在日本那些年,每逢各種節日,日本的家家戶戶都要掛上日本國旗,據說是日本當局要求的,但父親則嚴禁我們家掛日本國旗。在我們家,我們都說普通話、中國話。對外,我們則稱我們是福建人(父親講我們祖籍就是從福建到臺灣的),不說自己是臺灣人,因為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有不了解臺灣那段歷史的日本人會認為我們跟他們一樣。種種生活中的細節,父親都在教導我們一個真理,那就是“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
久而久之,父親在華僑中漸漸有了影響力,大家都清楚父親的愛國心是堅定的,所以在日本投降后,華僑總會就找到父親,并通過選舉父親當上了華僑總會的新一屆會長。
在日本,我們總要受到日本政府方面的敵視,每天都要接受日本的軍國主義教育,感覺很不舒暢。特別是戰爭爆發后,更變本加厲。但盡管如此,兩國人民之間的情誼并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鄰里之間的關系相處融洽。戰爭后期,戰火燒到了日本本土,城市空襲比較多了,我們就住到了農村一個農民家里。為了我們能有住處,農民因此而停止養蠶,把養蠶房騰出來讓我們住。我覺得,日本人民對中國人民還是友好的。直到現在,我在日本還有一些朋友,閑暇時間我沒事還會去日本游玩,他們還會特別歡迎我。

陳蕙娟三姐妹
父親在臺灣秘密加入中共,到大陸后教授馬列主義課程
1946年2月,因為父親擔任華僑總會會長后,跟日本政府常常要再“交手”。雖說日本是戰敗國,但在日本國內對待華人的歧視程度,甚至說偏向迫害,一點兒也未減少。由此,父親對日本政府越來越厭惡。所以,在這個時候,正好趕上日本按照戰敗協議,正把被日軍抓來做勞工的中國人送回國這個契機,父親毫不猶豫帶領全家人,坐上了第三批回國的輪船。那次,船上有不少臺灣鄉親,船到大陸后放下大陸的同胞,接著把我們送回到了臺灣。
回臺后,父親先在臺灣大學做了一名普通教師。并通過《人民導報》結識了宋斐如、鄭明祿、蘇新等人。1946年,《人民導報》因刊登有關國共和談敏感文章,引發陳儀不滿,宋斐如被迫辭去社長職務。后來,宋斐如被任命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是戰后初期行政長官公署高層官員中唯一的臺灣籍人士。“二·二八事件”前(非“二·二八事件”當年),父親辭去臺大教師工作,接受宋斐如的邀請,去建國中學當了校長。父親和宋斐如的關系非常要好,因“二·二八事件”影響,宋斐如成為首批被捕人士之一而遭害。許多年之后,父親還特地將他的兒子接到深圳并幫其打點好一切。
“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父親學校的好多學生也因搶武器被抓,國民黨聲稱只要父親出面就放了學生。為了學生的安危,父親決定用自己換回被抓的學生,因而被捕入獄。可學生在什么情況下,為什么要搶武器等等,這些我就不知道了。那時,父親回到臺灣后做的很多事情從來不在家里說,他什么時候加入的中共地下黨,我們全家都不知道。所以,他之前的事情我們一概不知,他教育子女的方式仍是那句經典話:讓我們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后來,時任臺灣省政府首任主席的魏道明聲稱不能太激怒知識分子,所以父親被釋放。出獄后,中共地下組織遭到了破壞,出了叛徒,1949年5月份,父親經香港到了北京。經廖承志同志介紹,他在北京人民大學教書,主講馬列主義等課程。
此時,我和母親、妹妹還留在臺灣。
我從臺灣到大陸,投身旅游事業時間最長
1949年9月,我19歲,高中畢業。在新中國成立前,母親帶著我和大妹妹從香港坐船到天津,然后坐火車到了北京。當時是中央統戰部接待了我們,住在遠東飯店。后經過廖承志的介紹,母親到鐵道部的鐵路醫院藥房當藥劑師。17歲的妹妹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工作。我則到華北大學工學院讀書,俄文專業,畢業后當俄文翻譯。所以,我現在還會說俄語。
1957年,因要照顧父母的身體,組織上把我調回北京,之后安排我在國際旅行總社工作。我在那里的工作時間最長,直至60歲時退休。
由于我是在日本出生,日文特別好,總社就把我安排在日本部外聯處任副處長,主要接待日本人。這么多年來,我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交給了祖國的旅游事業,特別是對中日人民間的友好往來、對增進兩國人民間的友誼,不遺余力。剛開始時,我工作的主要任務就是和日本旅行社聯系,洽談業務,讓他們帶領日本旅游團到大陸來旅游。當時的數據,1949年時,日本只有一個團6個人到大陸旅游,到1965年的時候,日本旅游人數達到了一個高峰,到1979年每年就增長至5萬多日本游客。
后來,我開始編制大陸的旅游線路。我前后共編制過60條旅行路線,有的直到今天仍在延用。這是因為這些路線,每條的價錢、線路、人文景觀、中華文明古跡等都是我精心計算過的,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旅游路線,里面更飽含著我對祖國的熱愛和對日本人民的真誠。正因為如此,這些路線才得到了日本游客的青睞。
隨著大陸的改革開放,為了打通更大的日本市場,我通過自身關系,和當時日本成立最早的旅行社——日中旅行社聯系上了,并達成了合作事宜,雙方合作一直到現在。再后來,為逐漸拓展業務,合作的日方旅行社達到了40多家。現在我估計更多了。
我現在還覺得,當時在工作中,我最高興的事就是日本游客回去后,寫信告訴我,他很喜歡中國。
我和丈夫都是臺灣人,青梅竹馬、恩愛有加
我的丈夫莊德潤,臺灣嘉義人,大我5歲,我們的結合可以用青梅竹馬來形容。由于時局所致,為了深造,當時愛人去日本留學,并在我父親所教學的學校學習。從那時起,他便擔任我父親的秘書直至回到臺灣。

工作中的陳蕙娟
在日本生活了16年的我,隨父母、莊德潤一起回到臺灣后,父親在臺灣大學教中文,莊德潤也隨之在臺大繼續讀大學,而我在臺北第一女中讀中學。后來莊德潤考取了公費生,到了武漢大學繼續求學。
1950年,因為武漢要解放了,比較亂,莊德潤未畢業就到了北京投靠我父親,后經廖承志介紹到部隊總參工作,再后來分配到廣州的一個部門。1951年夏天我從華北大學工學院畢業,同年8月,我和莊德潤在廣州結婚。
在廣州待了五六年,1957年因為先生調回北京,我們全家就都回北京了。在廣州期間,我們的第一個兒子于1953年9月25日出生,現今62歲了。因為“文革”期間不敢懷孕,所以第二個孩子女兒出生在1973年,現今42歲。相隔了整整20年。
我和先生一直沒有結婚照,年輕的時候照相機會不多,就沒什么照片。現在留下來的照片我都能認識照片里面的人和當時發生的事。我女兒現在一家日本的旅行社工作,可能受我的影響吧,大學時讀的專業是日文。
相隔60年后,2009年,我回到臺灣,住在先生的弟弟家,南投。然后驅車趕到高雄。我還有一個妹妹,當時在臺灣,剛出生沒幾個月的時候,受奶奶之命,送給了姑姑。妹妹小我5歲,一直在臺灣。后來,大概在中年時,妹妹來過北京。我們姐妹3人才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相聚,因為妹妹長得像我,相見時第一眼我們就認出了對方。
姑姑現在已經去世了,就剩妹妹一人在高雄。我和小妹妹的聯系方式均以書信為主。而父親直至去世時都沒有再見過爺爺、奶奶和妹妹,這可能是他唯一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