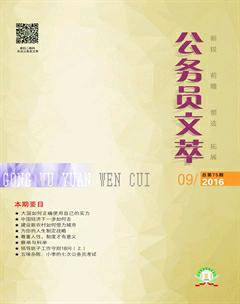北大團(tuán)委書記和他的白洋淀
李少威
拍單人照,北大團(tuán)委書記陳永利還是用一種大合影的姿勢(shì):身體筆挺,頭部上揚(yáng),標(biāo)準(zhǔn)地微笑著。
生于改革開放啟動(dòng)的1978年,從白洋淀到北大,從“土老帽”到一個(gè)不著痕跡的北京人,從鄉(xiāng)土中國(guó)到現(xiàn)代中國(guó),這個(gè)青年干部完整經(jīng)歷了兩個(gè)不同“世界”的轉(zhuǎn)換,其中還有一些區(qū)別于一般人的偶然性。
這條社會(huì)嬗變的軌跡,陳永利體驗(yàn)豐富,外在的和心理上的,民間的和體制的。這個(gè)過(guò)程,可以折射在更多的人身上。
一個(gè)好學(xué)生
工作人員送過(guò)來(lái)兩瓶飲用水之后,我們結(jié)束了寒暄。
“我原來(lái)想了一下,要談的有三個(gè)部分。”他說(shuō),“對(duì)個(gè)人經(jīng)歷,主題是對(duì)生活永遠(yuǎn)充滿感激,充滿熱愛;對(duì)在北大的工作,主題是‘與青年一起成長(zhǎng),為北大再創(chuàng)輝煌;至于未來(lái)的工作,‘為國(guó)求學(xué),努力自愛,多元發(fā)展,集體成才,是我對(duì)北大學(xué)生發(fā)展的期望。”
我悄悄地把寫滿懷疑主義提問(wèn)的兩張紙揉成了一團(tuán)。我說(shuō),你是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的好學(xué)生。
“在老師的眼里還真是,所以我獲得的榮譽(yù)很多,北大所有的榮譽(yù)我都得過(guò),一些還是全國(guó)性的榮譽(yù)。”
一個(gè)能在頂尖大學(xué)留校,并當(dāng)上學(xué)校團(tuán)委書記的人,肯定是一個(gè)“榮譽(yù)等身”的人,但陳永利說(shuō)“所有”的時(shí)候還是讓我驚訝。這意味著,除了社會(huì)活動(dòng)能力的考驗(yàn)之外,表現(xiàn)在數(shù)字上的成績(jī)還要足夠好,而這恰恰是許多學(xué)生干部不能兼顧的。
“你是不是對(duì)榮譽(yù)看得很重?”我問(wèn)。
他說(shuō),的確,在學(xué)生時(shí)代成績(jī)和榮譽(yù)是自己至高的追求,主要是為了用一種形象的語(yǔ)境來(lái)報(bào)答父母。
“他們?cè)谵r(nóng)村省吃儉用地供我上學(xué)不容易,如果我學(xué)得不像樣,沒(méi)法向他們交代。小學(xué)、中學(xué)都有成績(jī)排名,那時(shí)就是拿著成績(jī)單回去,大學(xué)就沒(méi)有了,他們只能通過(guò)證書、獎(jiǎng)?wù)聛?lái)判斷你的表現(xiàn),五四獎(jiǎng)?wù)隆?yōu)秀大學(xué)生……各種紅本,挺大一本,蓋著北大乃至全國(guó)性的大紅章,他們看著開心。”
“全班第一名、年級(jí)前三名”,是陳永利小學(xué)、中學(xué)時(shí)代最醒目的標(biāo)簽。沒(méi)有參加高考,直接保送北大,本科畢業(yè)后又以綜合得分第一、專業(yè)得分第二的成績(jī)保送研究生。專業(yè)是越南語(yǔ),屈居第二是因?yàn)榈谝幻呐菑V西人,廣西口音和越南語(yǔ)更相近。碩士畢業(yè)后留校,6年后跨專業(yè)讀了博士。
看得出來(lái),陳永利對(duì)這一過(guò)程很自豪。一刻不放松的努力,既需要智力,也需要意志力,一同構(gòu)成人的主觀能動(dòng)性。看上去,這是一個(gè)十分個(gè)人化的過(guò)程,然而當(dāng)把個(gè)人經(jīng)歷放進(jìn)整個(gè)社會(huì)前行的主流趨勢(shì)中去,又會(huì)發(fā)現(xiàn),人在其中,依舊是身不由己。
陳永利說(shuō),幾十年來(lái)我們的生活是沿著一種城鎮(zhèn)化和現(xiàn)代化的趨勢(shì)在行進(jìn),我們自己追求個(gè)人發(fā)展,也要有意識(shí)投入這一進(jìn)程當(dāng)中。
新北京人
陳永利是保定白洋淀人。從地理上看,白洋淀離北京直線距離僅100公里左右,但如果要從一個(gè)白洋淀的農(nóng)家孩子變成一個(gè)北京人,這100公里就成了社會(huì)階層流動(dòng)的最極端的試驗(yàn)。
個(gè)人的城市化,人們最熟悉的途徑有兩種,一是“學(xué)而優(yōu)則進(jìn)城”,讀書,就業(yè);二是做生意,賺很多的錢,買房,落戶。
陳永利走的是“第三條道路”。他的母親是北京人,1975年作為知青去到白洋淀,經(jīng)人介紹嫁給了他的父親,一名當(dāng)?shù)貪O民。1989年,作為一種解決歷史遺留問(wèn)題的方式,知青的孩子中可以有一個(gè)人代替返城。
一個(gè)北京戶口從天上砸了下來(lái),這一年陳永利12歲,弟弟7歲。長(zhǎng)子優(yōu)先,而且性格安靜的陳永利在預(yù)期中會(huì)更有前途,于是他就去了北京。
“我其實(shí)不想去,因?yàn)閺膩?lái)沒(méi)有離開過(guò)家,我弟弟呢,好動(dòng),貪玩,自小也不那么聽大人的話,聽說(shuō)能去北京就特別開心,但最終父親的權(quán)威把這一機(jī)會(huì)給了我。”
在北京,陳永利和姥姥兩個(gè)人生活;而在他5歲以前,由于父母在外,也是和奶奶一起生活。
我說(shuō),你的童年基本屬于“留守兒童”,從在農(nóng)村留守,變成在北京留守。他在一閃而過(guò)的愕然之后笑起來(lái):“確實(shí),差不多那個(gè)意思。”
劉姥姥帶著板兒進(jìn)大觀園,只是臨時(shí)性的,被人笑話一番之后就離開了,而陳永利則要成為北京這座“大觀園”中永久性的一員,他必須在十幾歲的年紀(jì)進(jìn)行一番脫胎換骨的自我改造。
“你必須去適應(yīng)它,否則你永遠(yuǎn)擺脫不了內(nèi)心的自卑。”讓這個(gè)新北京人最為焦灼的是河北鄉(xiāng)村口音。在班上,因?yàn)榭谝魡?wèn)題,他在明里暗里都被稱為“土老帽”。他內(nèi)心暗暗起誓,兩年內(nèi)完全改掉河北口音,如今陳永利已經(jīng)不會(huì)說(shuō)家鄉(xiāng)話,普通話標(biāo)準(zhǔn)。
城鄉(xiāng)教育的差異也讓他深受震撼。農(nóng)村學(xué)校初中才有英語(yǔ)課,而城市里的孩子小學(xué)三年級(jí)已開始學(xué)英語(yǔ),別人可以進(jìn)行日常對(duì)話的時(shí)候,他連英文字母都認(rèn)不全;北京孩子多有文藝特長(zhǎng)、體育特長(zhǎng),而自己一樣也不會(huì)。
陳永利的特點(diǎn)是,小小年紀(jì)就有一種主動(dòng)的努力意識(shí),任何一門文化課都可以后來(lái)居上,比如第二學(xué)期開始,他的英語(yǔ)就能考100分。“但體育課和音樂(lè)課就沒(méi)法補(bǔ),以前在農(nóng)村沒(méi)有體育課,唱歌基本靠嚷,這些東西很難從頭再來(lái)。”
分化的命運(yùn)
脫離了親緣社會(huì),又沒(méi)有朋友,初到北京的陳永利,獨(dú)立,但也很孤單。
他是帶著鄉(xiāng)愁告別白洋淀的,但這鄉(xiāng)愁只是少小離家的不舍,和今天城里人的浪漫想象無(wú)關(guān)。
“白洋淀”,這個(gè)詞在外界印象中對(duì)應(yīng)著一個(gè)美麗的魚米之鄉(xiāng),而在陳永利的記憶中,則是一片干涸見底的景象。記憶中,白洋淀一直沒(méi)有水,也就沒(méi)有魚,蘆葦蕩也長(zhǎng)不起來(lái)。而他家所在的村子是漁村,人們的謀生之道有二:打魚,編葦席。漁民們賴以生存的條件消失了,結(jié)果就是貧窮,甚至饑餓。
5歲以前,他之所以成為“留守兒童”,就是因?yàn)楸镜責(zé)o以為生,父親去了天津海河打魚,而母親則在縣城上班。他離開后,白洋淀就有水了,不過(guò)對(duì)于當(dāng)?shù)厝硕裕昂蟮膮^(qū)別也僅僅在于是否能吃飽肚子。
兄弟倆一走一留,命運(yùn)開始分化,直到很久以后,陳永利才領(lǐng)會(huì)了這一去一留之間對(duì)人生的意味。
碩士畢業(yè)之后,陳永利留在了學(xué)校,從學(xué)院團(tuán)委書記,到北大學(xué)生就業(yè)指導(dǎo)服務(wù)中心主任,再到北大團(tuán)委書記,其間又讀了博士,評(píng)上了副教授;他的妻子也是北大教師,留美歸國(guó)的博士后。
而弟弟初中畢業(yè)以后就沒(méi)有繼續(xù)讀書,如今在家鄉(xiāng)開著一間理發(fā)店。這間理發(fā)店的鋪面,是陳永利出資買的。2004年開始工作,他把自己將近10年的收入,全部用于“反哺”弟弟,除了幫他買鋪面,還幫他買房子,資助他結(jié)婚、養(yǎng)孩子。
“我心里覺得欠著弟弟一個(gè)很大的人情,但我是對(duì)得起他的。”為了對(duì)弟弟進(jìn)行物質(zhì)輸送,他在畢業(yè)后不買房,不買車,不結(jié)婚,直到實(shí)現(xiàn)心理上的自我平衡。
“人的成長(zhǎng)過(guò)程都是慢慢越來(lái)越現(xiàn)代,關(guān)鍵看到了一定程度,還能不能保留你原來(lái)比較淳樸、真摯的一面,不忘初心。”“初心”是對(duì)過(guò)去的回應(yīng)。被“選”為北京人,對(duì)他而言是關(guān)鍵性的一步,后面還有很多偶然因素,一起將他推入社會(huì)精英階層的行列,比如,遇到一個(gè)好老師。
初中畢業(yè)時(shí),父親患了重病,家境艱難,陳永利打算讀高職或中專,早一點(diǎn)就業(yè),是語(yǔ)文老師王建國(guó)勸他繼續(xù)讀高中,考大學(xué);上高中第一年就湊不齊學(xué)費(fèi),又是王建國(guó)老師發(fā)動(dòng)全班捐款資助。
陳永利最大的“初心”就是當(dāng)一名老師,這一定程度上基于他對(duì)教育與人的命運(yùn)之間的關(guān)系的認(rèn)知,這種認(rèn)知直接來(lái)自王建國(guó)老師。王老師在36歲時(shí)因病去世,陳永利就一直有一種延續(xù)這一角色的使命感。
本科即將畢業(yè),老師問(wèn)他的打算,他說(shuō)想去中學(xué)教書,老師便笑了:“你可以留在北大,當(dāng)一名大學(xué)老師。”
讀書有用論
陳永利特別提出,自己并不想過(guò)多渲染兒童時(shí)代鄉(xiāng)村生活的艱難。我說(shuō),了解只是為了理解,白洋淀當(dāng)時(shí)的貧乏其實(shí)就是構(gòu)成人的命運(yùn)的一部分社會(huì)要素。
沃倫·巴菲特有一個(gè)著名的“卵巢彩票”比喻,先天是不可控的,像一場(chǎng)抽獎(jiǎng),幸運(yùn)者“在恰當(dāng)?shù)臅r(shí)候出生在一個(gè)好地方”。白洋淀,顯然不是好的“卵巢”,所以從白洋淀到北京,是一個(gè)個(gè)體像鮭魚一樣逆水“洄游”的時(shí)代縮影——給自己一個(gè)新的位置,也給下一代尋覓一個(gè)好的“卵巢”。
現(xiàn)在城市里70后、80后這兩代人,大多數(shù)人來(lái)自農(nóng)村,父母沒(méi)有為其積攢下任何社會(huì)資源(這顯著區(qū)別于90后和00后),在后來(lái)中國(guó)的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他們無(wú)所憑依,最有效的“抓手”就是讀書。陳永利是其中一個(gè)很特別的個(gè)案,他的童年和少年經(jīng)歷,呈現(xiàn)了一個(gè)多元因素交織的“洄游”過(guò)程。
但這個(gè)過(guò)程無(wú)法復(fù)制,今天乃至更早以前,對(duì)于教育在社會(huì)流動(dòng)層面的意義的認(rèn)識(sh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明顯的松動(dòng)和分化。人要怎樣擺脫在抽取“卵巢彩票”失利后的先天不公處境,在今天更加值得思考。
很自然地,我便提出了這個(gè)問(wèn)題:北大的學(xué)生當(dāng)中,來(lái)自城市與農(nóng)村的比例在發(fā)生著怎樣的變化?
“絕對(duì)數(shù)量上看,農(nóng)村生源的學(xué)生比例肯定是不高的,重點(diǎn)大學(xué)尤其如此。”陳永利說(shuō),但這不一定都?xì)w因于政策是否公平,而是有方方面面的社會(huì)因素在起作用。
“第一,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加速,農(nóng)村生源本身在大規(guī)模減少;第二,讀書無(wú)用論在農(nóng)村還是有一定市場(chǎng),很多家庭主動(dòng)放棄了孩子的學(xué)業(yè);第三,家庭條件好的學(xué)生更容易考上重點(diǎn)中學(xué),重點(diǎn)中學(xué)的學(xué)生更容易考上重點(diǎn)大學(xué),所以其實(shí)中學(xué)階段已經(jīng)決定了大學(xué)生源的結(jié)構(gòu)。”
陳永利想強(qiáng)調(diào)一個(gè)常識(shí)性的道理:讀書永遠(yuǎn)是有用的。
在當(dāng)校團(tuán)委書記之前,他當(dāng)了8年北大就業(yè)中心主任。“這么多年的感受是,越是學(xué)習(xí)好的、專業(yè)精通的,在社會(huì)上就發(fā)展得更好。學(xué)完覺得沒(méi)用,不是知識(shí)本身沒(méi)用,是你自己沒(méi)把它用好。”
對(duì)陳永利的采訪是在電話和敲門聲的不斷打擾中完成的,活動(dòng)的安排、學(xué)生內(nèi)部矛盾的處理、領(lǐng)導(dǎo)的詢問(wèn)……瑣細(xì)的忙碌貫穿著他除了睡覺以外的所有時(shí)間,他卻樂(lè)在其中。
“人剛要上大學(xué)的時(shí)候,立志當(dāng)總理,后來(lái)發(fā)現(xiàn)只能當(dāng)經(jīng)理,甚至最后只是當(dāng)助理。這不意味著理想磨滅了或者變得現(xiàn)實(shí)功利了,而是一種成長(zhǎng)。畢竟,這個(gè)社會(huì)需要的總理很少,更多的是平凡的人。”
“你這個(gè)位置上可是出過(guò)很多大人物的。”我說(shuō)了幾個(gè)響當(dāng)當(dāng)?shù)拿帧?/p>
他說(shuō),沒(méi)有想那么遠(yuǎn),只想一心一意做工作,“以此感謝北大和國(guó)家的培養(yǎng),讓我能通過(guò)學(xué)習(xí)改變命運(yùn),取得現(xiàn)在的進(jìn)步”。
(摘自《南風(fēng)窗》)
- 公務(wù)員文萃的其它文章
- 多少往事
- 經(jīng)過(guò)
- 著眼于長(zhǎng)處
- 本事
- 戒律和自由
- 司空見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