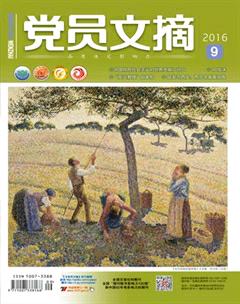文字和我們的生活
李少威
我喜歡古文,喜歡它的美感。
《三國演義》里,語言藝術上最絕的莫過于“罵死王朗”,一段氣勢如虹的現場教訓,酣暢淋漓,諸葛先生簡直就是在唱歌嘛。同樣令人擊節贊嘆的還有“舌戰群儒”,除了言辭犀利,雄辯滔滔,里面還包含了很多儒家倫理原則。
歷代文章,都能把意境寫得極美。在經典當中最美的當然是《詩經》,寫對美女的單相思,“求之不得,窹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愛情意境無過于此。在《論語》中,孔子的徒弟曾點也是個有情懷的“文青”,他說自己的志向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短短27個字,卻有大片的美感。
至于歷代散文,當然更是各盡妍美了。有時寫景,有時寫情,有時寫人生心得,有時則闡述“聞道有先后”這樣的道理。墓志銘也是散文的重要形式,一個人死去,一篇好文章出現,經常寫得墳頭生花。
對文字的藝術化使用,讓多少人名動天下。
如王勃,在滕王閣上,別人飲酒他寫文章,寫一句別人就抄一句拿去讀,讀得滿座雅士心潮起伏。到了“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這一句,人們驚訝得幾乎掉下巴。
還有苦吟詩人賈島,是“僧推月下門”還是“僧敲月下門”呢?糾結猶豫,十分痛苦。他寫了一首詩形容自己對詩的沉迷:“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
不勝枚舉了。年輕時的我對這樣的文字癡心熱愛,對傳統文化十分自豪。
年紀漸長,我就在想,一生苦學,只給后人留下一些美麗的意境,能頂什么用?
古文的意境之所以可以如此之美,美得登峰造極,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它語意的不確切。就像人們去黃山,一定要有霧,霧一散就覺得差很遠。古文里便到處是霧。
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陳偉說,我們的傳統文化里只有人生哲學,沒有太多的政治哲學。這樣的言論我已經聽過很多,也在一定程度上認同。很明顯,我們幾千年來根本找不到一本有嚴謹體系、有理性的方法論的哲學思想著作,而在西方,從比孔子更早的古希臘前期就已經汗牛充棟了。
文字是日常生活必須的表意符號,而沒有清晰表意的文字,許多事情就無法確定下來。反映到社會生活當中,就是規則不明晰,人際相處需要互相揣摩,辦事干活常常要彼此試探,偶有明確的規則,也不敢相信,還要另想門路疏通。
回到“舌戰群儒”的場景。在一個梟雄并起、詭計橫行、隨心殺戮的時代里,一堆斯文君子坐在一起講道理,講的還是明明誰也不當回事的教條。說話最真實的是薛綜,他說的就是“誰有權勢跟誰混”的現實道理,被諸葛亮罵得最厲害。
定下一些人人做得到而且必須做到的規則公之于眾,然后大家依照行事,越軌的就要受到懲罰,我們向來不在意,而是對“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這些潛規則津津樂道。所以,今日那些真正有擔當的人文知識分子,在社會建設上所做的事情大多是想實現這兩者之間的扭轉。
(摘自《南風窗》2016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