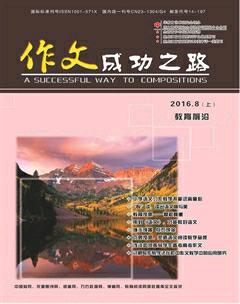一棵樹
王浩宇
少年時代。
“在下一次火燒云際到來之際,我想把樹葉漆成金色”,在觀察報告中寫道。
這本是母親給我長達一年的觀察任務,而我在草地上鋪上紅藍線條桌布,躺著想維多利亞·希斯洛普的問題“在一棟棟建筑下都埋藏著什么?”
正值春末,棉襖都退下了,樹還是一口碗粗細,報告還是一張白紙飄飄。馬爾克斯在樹上他說他不抓鳥,不像馬爾比諾醫生,但時間還是像生銹了一樣。我說因為我和樹都沒長。在他說過這是少年時代呀,之后再也沒見過他。
一天一天,樹葉搖曳搖曳。一個又一個星辰錯落的夜晚,一場又一場無法出門的大雨,一次又一次愛看的火燒云。
它是把天分成兩片的魔法,藍色一邊由淡藍到靛藍,淡紅到赭紅。樹也是部分金黃,不是那種燦爛奪目的,是老舊的暗金。
不知不覺,時間開始小跑了起來,在夏末,詹姆斯·喬伊斯也在看火燒云,他說“我聽見整個空間的毀滅,玻璃稀里嘩拉的砸啐,瓦片也紛紛倒塌,而時間則成了慘淡無光的最后一道火焰”。
秋天樹葉為什么會掉,只剩寥寥幾片。少時,我對波德萊爾并不感冒,我不準他接近我的樹,他有《惡之花》,腐朽的巴黎,但他那樣憂郁,他站在樹前看著樹冠,“啊”的嘆氣,我深知不是震驚。他說“不要把一個階段幻想的很好,而又去幻想等待后的結果,那樣的生活只會充滿依賴“,我不準備聽他的,因為樹枝上出現白色的花朵,是雪花。
冬天來了,那是一條白色的巨大桌布。我不能躺下來,地面那樣冰冷,于是我說,春天不遠,不對嗎?
別讓我再看到戈爾丁,好比三倍偉大的撒旦,他說人本性惡,總會出來,但不一定太壞,總歸是惡。
不過他委實嚇到我了,我想到火燒云不再來臨,樹不再生長,我跪在現實面前瑟瑟發抖。
一切都很好,直到建筑物拔地而起,埋沒我的樹。
唉,埋藏的是我的回憶呀。雖然記錄空白,但全在腦子里根深蒂固,樹在腦子里生長又戛然而止。
桌布不能鋪在馬路上,不能闖紅燈,有這個規定,規則。達達主義的我不在了嗎?波希米亞的我呢?樹在哪個建筑里被壓著,壓斷主干!就像我,我想要的自由!被現實壓斷脊骨。
波德萊爾來了,他幫我寫了報告,我又加上火燒云到來之際的那句話。
當我看到題目時,我被打暈了一樣,它叫《象征主義的樹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