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光無影的空間
王大鵬
在當下如果你問開發商或者市民,一個好的房子先決條件是什么,不出意外他們會連聲說:地段,地段,當然還是地段!但是當你問建筑師什么才算好的建筑,估計他會猶豫一下,答案可能不像“地段”那么唯一,但是空間和光影一定是繞不過的,而且也基本不會有人反對。
為什么建筑師對建筑的空間和光影效果會如此的癡迷和情有獨鐘?且不說那穹頂宛若飄浮的圣索非亞大教堂,也不必說至今屹立在雅典衛城光影交織的帕提儂神廟,更不必說那具有八點九米直徑圓洞光影游移不定的萬神廟,從古希臘、古羅馬以降,歷經中世紀、文藝復興以及工業革命,教堂風格雖隨時代有所變化,但亙古不變的是那讓人感受到宛如上帝存在的一縷縷光影,這些教堂使得眾人膜拜不已,上帝的存在就不再顯得虛無縹緲。上帝只存在于眾人的心中,而設計建造的建筑師卻是實實在在的,他們憑借天才般智慧的頭腦和工匠鬼斧神工的技藝鑄就了一座座教堂,動輒幾百年的建造周期可謂雕刻時光。
雖然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在西方古代社會條件下要建造出一座具有空間和光影魅力的教堂或者別的公共建筑絕非易事,因為能用的材料基本只有磚石和土木,有限的跨度,粗壯的柱子,厚重的墻體,要有光就要開窗,可是在什么地方開窗、開多大的窗,絕不是一件隨便的事情。那時的建筑師基本上既是雕塑家、繪畫家、科學家,又是技藝高超的工匠,某種程度上還是可以和上帝對話的巫師,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是其代表。人的力量和才智雖然有限,但當穹頂那不絕如縷的光線傾瀉而下并且彌漫開來時,人也就變得崇高偉大起來,尤其是設計建造了教堂的建筑師,變得猶如神一般的存在。
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的傳統建筑日漸式微,現代建筑應運而生,柯布西耶那句“房屋是居住的機器”,可謂現代主義建筑的宣言。雖然現代建筑與傳統建筑貌似決裂了,但是現代主義的建筑師卻欣然接過了“空間與光影”的大旗,形式、風格與材料可以千變萬化,只要抓住了空間與光影似乎就有永恒的可能。青年柯布西耶花了很長時間游歷了歐洲的經典建筑,他從帕提儂神廟的廢墟中看到了光影的魅力,還看到了人性的光輝,甚至看到了科學與理性的偉大。雖然他早年激進狂熱的謳歌推動著現代建筑的發展,并且明確提出了現代建筑的五點要素,可是在晚年他卻游離于現代建筑之外,無論是靜謐粗獷的拉圖雷特修道院,還是神秘夢幻的朗香教堂,它們都把空間與光影的變幻演繹到了極致。大器晚成的建筑大師路易斯·康也是運用光線的頂級高手,他的每個建筑都在試圖建立人與宇宙的秩序與關系,埃克斯特圖書館、薩克爾研究所、金貝爾美術館、孟加拉國議會大廳等建筑盡管功能與規模各異,但卻都是光影魅力無窮,都是能讓人感受到永恒性精神存在的建筑。
莫非現代主義的建筑大師都為光影所俘虜?同時代的建筑大師密斯更在乎空間的通用性和流動性,而不是光影的變幻。他設計的建筑秩序明確,材料構造精準,相對柯布西耶的建筑來說更具有“機器性”,他的絕大多數建筑的維護外墻幾乎全是玻璃,可謂有光無影。鄉村的夜晚是黑暗的,而城市的夜晚燈紅酒綠,密斯的建筑在夜晚才睜開了自己的明眸善睞的眼睛,他的建筑是屬于城市的,所以這些大師中對世界城市建筑影響最大的無疑當屬密斯。
說到二十世紀的建筑大師,賴特當然是繞不過去的,他的草原式住宅受日本傳統建筑影響很大,舒展深遠的水平挑檐導致光影效果并不明顯,窗戶基本都是處在陰影里,這樣的氛圍正符合谷崎潤一郎筆下的《陰翳禮贊》。日本或者中國傳統的建筑開窗大小和位置雖然要遠比歐洲的石砌建筑自由,但是高大的屋頂和深遠的出檐使得窗戶幾乎永遠處在陰影里,從外面只能看到金碧輝煌或者櫛次鱗比的瓦屋面,室內的光線經過屋檐的遮擋與過濾總是隱約朦朧的,這樣的建筑是離不開院子的,因為院子提供了光線,并且人在屋中可以通過院子感受到晝夜交替與四季的輪回,在我們的傳統中時間的概念就是光陰,所謂“一寸光陰一寸金”。
啰嗦了這么多,并非要講什么建筑史或者建筑大師,只是想在簡要的梳理過程中回顧一下歷史建筑中的空間和光影是如何存在與變化的,而當下被建筑師奉為神明的空間與光影又是怎么存在的呢?要講清楚這個問題并不容易,不妨先用傳統詩詞類比看看,唐詩宋詞是我們傳統文化的兩座高峰,至今讓人流連與仰止,好在大家都有自知之明,基本沒有人試圖通過填寫格律詩詞來加高山峰,因為詩詞描寫的生活早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曾經的事物也已滄海桑田,屬于田園牧歌的時代一去不返,盡管我們內心很難接受。尼采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高喊“上帝死了”,可多數現代建筑師卻接過傳統建筑師“巫師”般的衣缽,試圖借助來自上帝的光影而不朽,在當下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這個極度消費與娛樂至死的社會中,什么才是不朽的呢?那些曾經神秘而神圣的光影還存在嗎?光影還是當下建筑存在的基礎嗎?
我們傳統的建筑中無論是皇家宮殿,還是民居院落,或者文人園林,都沒有西方傳統建筑中那樣對光影的極致追求,當然也不存在上帝般的神性,我們建筑的光線可以說是彌漫與詩意的。我們的現代建筑可以說不折不扣的是來自西方,完全繼承西方建筑的形式心里總過意不去,但是空間和光影似乎是抽象無國界的甚至沒有文化差別,何況也被西方現代建筑師奉為神明。姑且不說這種東西方建筑中光影的精神性是否存在差別,在當下的城市中還存在產生這樣光影效果的環境和條件嗎?
首先,傳統的建筑尤其是公共建筑相對來說都是獨立存在的,基本沒有什么遮擋,建筑的光影隨著自然環境而變化,而當下的城市建筑因為土地條件和密度制約,許多沿街建筑基本以一個正立面存在著,并且還不一定有最佳視距,這樣的城市環境導致建筑光影變化大打折扣。其次,當下城市里的建筑白天也基本都是依靠人工照明,尤其是大量的辦公樓,只要在工作狀態,無論白天還是夜晚都開著燈(這讓人想起那些生活在24小時人工照明的籠子里,至死都沒有機會接觸地面的雞),一個晝夜開著燈的建筑空間何談那種自然的光影變幻效果?還有城市的公共建筑立面懸掛著大量的商業或者公益廣告,這些廣告基本都是可以發光的,傳統建筑中無論內部還是外部空間的光影效果都被極大地削弱了。另外當下的城市建筑基本都是以高層存在,維護外墻越來越輕薄,窗戶越開越大,乃至全部變為玻璃幕墻,光線缺少必要的承影面,更多的是被反射和折射,這樣的建筑光影效果能與傳統一樣嗎?從十層樓窗戶照進客廳的光線與從一層地面院子照進的陽光絕對不是一回事。還有當下的城市車水馬龍,各種人工制造出來的噪音經久不息,這些噪音極大地瓦解了傳統建筑光影的純粹性甚至存在感,沒有天籟之音和靜謐的環境何談光影魅力?

傳統建筑因為所用材料、建造技術和施工周期導致空間是封閉內斂的,光影的效果因為洞窟般的窗戶而神秘迷人,可以說對應的是一種較為原始的慢生活。而當下晝夜長短的客觀時間似乎一如既往,但是人們做事情的節奏和手段發生了質變,速度與效率的提高壓縮了時間與空間,我們的生活越發變得時尚而輕薄,人被自己制造的工具和環境所俘虜,生理功能逐步退化,這似乎是令人傷心無奈的事情,我們除了與時俱進還有別的可能嗎?
在當下的國際建筑大師中,妹島和世的作品中的空間與光影令人驚嘆而著迷,她通過對磨砂玻璃、壓花玻璃、聚酯有機玻璃、柔軟幕布等材質的精心運用,使得建筑的光線既是自然的、生活的,也是詩意的,彌漫、模糊的光線,開放、均質、曖昧甚至趨于二維化的空間是她建筑作品呈現的特質,連空氣似乎都成了她運用的材料,她的建筑超然地存在著,卻沒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覺,恰恰人的存在點亮激活了那些純粹的空間,使得空靈中多了動感與活力。妹島似乎將桂離宮現代化和中性化了,她的建筑給我的感覺宛若晨霧中徐徐展開的太極拳,但是“從她的陰柔中可以看到魄力,從她的開放中可以看到隱秘,從她的曖昧中可以看到清晰”。妹島的老師伊東豐雄認為她的建筑脫離了建筑師對于建筑的夢幻和虛擬的幻想(指沉浸在自己已有的范式和想象之中),她的建筑是生活的體驗,是當今社會活生生人的體驗,所以具有真實感,是從生活中長出來的建筑。這種特質既來自天才般的靈感,也來自她從一而終的執著與堅持,這樣的特質也許讓常人難以企及,但卻足以給我們啟示與信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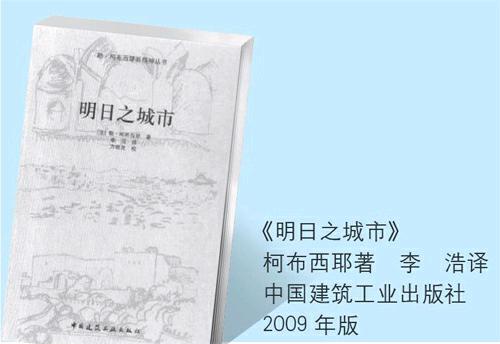
傳統建筑中的光影是有密度與溫度的,還具有自然的氣息,它的密度來自那厚實的維護墻體,而射進窗戶的陽光不僅僅提供著內心的溫暖,并且提供著真實的熱量,這樣說來曾經的光線意味著天氣與季節的變化,而在安裝了空調等各種現代設備的房間,人們對天氣與季節導致的溫度變化已不是那么敏感,可以說城市里基本是沒有季節的,也似乎可以不需要季節的存在,當然能四季如春最好。我曾參觀過柯布西耶的拉圖雷特修道院和圣皮埃爾教堂,感觸頗深,前者因為建造時間早,里面基本沒有什么現代設施,光影感覺是那么質樸與純粹,而且空間中可以嗅到那種來自原始的泥土氣息;而后者于二○○六年才完成建造(柯布西耶卒于1965年),盡管室內基本維持著素混凝土的原始狀態,但是設備管線多了不少,甚至還有粗大的空調風管,因為這些設施的存在讓人感覺到那些光線就沒有前者那么自然與純粹。
我們當下城市建設動力不夸張地說基本是靠出賣土地與建設大量住宅而維持的。我不知道全球的國家中有沒有像我們這么熱愛陽光的,幅員遼闊的祖國大地上,城市住宅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都嚴格地執行著“日照間距”這個硬性法規,常常會有新建建筑遮擋了后面住宅的日照,也有不良開發商在日照計算上弄虛作假,從而引發了大量的糾紛和矛盾。這個日照間距真的很公平嗎?能使得廣大老百姓陽光普照嗎?其實那些高樓底層的住戶日照永遠是少的,何況就是在京城,又有多少外來務工人員住在地下、半地下室呢?這個法規導致的結果是,我們的住宅基本都是南北向布置,高層住宅之間的樓間距動輒五六十米甚至更大,雖然這些高層住宅的容積率不低,可是密度卻基本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一個個小區將城市劃分成了一個個孤島。柯布西耶倡導的“明日城市”構想在我們當下的城市中基本實現了,只是還不夠完美,也許當中央拆除小區圍墻的政策實施后,就堪稱完美了。
我一直很驚訝范仲淹的想象力而非文采,他在寫《岳陽樓記》時根本就沒有去過這個地方,竟然妙筆生花,把岳陽樓寫得氣象萬千神采飛揚,千百年后仍讓人心曠神怡向往不已。古人講究的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因為印刷成本太高,加上那時也沒有報紙、廣播、電視、相機、手機和網絡,一些知識的獲取只能靠身體力行,這樣反而更節省時間和成本。那時的人們要看見并了解一個建筑似乎只能用腳步去丈量,靠眼看耳聞鼻嗅去體驗,靠心靈去感受,而當下大家對一個建筑的了解和認識就容易多了,即使職業建筑師又實地體驗了多少經典建筑呢?建筑師作品集的照片基本都是在房子建成后第一時間拍攝的,技藝高超的攝影師扛著專業的攝影裝備,如同狩獵一樣守候時機—為的就是捕獲那一縷神圣的光線,從而使得建筑因為這光影而神采飛揚熠熠生輝,不少建筑似乎就是為了作品集才應運而生的,因為相當一部分建筑師內心的“甲方”不是別的什么,正是作品集。奇怪的是特別講究“以人為本”“天人合一”的建筑師在拍作品集照片時并不喜歡人的出現,不少建筑師厚厚的作品集相片中人的數量加起來不會超過個位數,即使這樣拍出來的片子還需要精心挑選和后期處理,如果說看著美圖秀秀照片相親不靠譜的話,那用作品集照片來了解和體驗當下的建筑就更不靠譜。
當下建筑師做設計除了特別講究“以人為本”“天人合一”外,還很在乎建筑的場所感和地域性,其實多數建筑師都忽略了建筑所處環境的客觀時間性和季節性變化的影響,投在西墻上的朝陽和映在東墻上的夕陽,顏色與濃度是很不一樣的,當然春天和秋天的陽光也不一樣,杭州西湖和武漢東湖的差別不僅僅是面積不同。可以說在當下城市中生活長大的人(當然也包括建筑師)基本沒有分辨這些事物的意識,可是他們卻依靠掌握的知識和理論頑固而自信地講解著“小麥”和“韭菜”的習性、形狀乃至基因有多么的不同。
現代的城市是雄性的,它用滿城燈火照亮了自己,所以就不再需要月亮和星星,傳統的詩詞中可以沒有太陽,但是如果沒有了月亮與星空是不可想象的。兒時記憶中的三五之夜是那么明亮與美好,我曾經在月光下讀書寫字,還記得小學課文中張衡因為數星星從而成為偉大的天文學家的故事,可惜這些在現在的城市中已俱往矣,霧霾重重的日子能看見一輪暈乎乎的太陽都會激動不已。孫伏園曾經陪著魯迅去西安,魯迅失望地說連這里的天空都不是長安的了。今年春節去西安,霧霾中古城花燈綽約而朦朧,晚上因了這霧霾西安越發顯得厚重、深沉與古樸,竟然頗有詩賦中長安的氣象。還記起了蘇軾筆下的月夜,那是何等的空靈與畫意:“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未寢,相與步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松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
坐在四季開著空調與晝夜開燈的現代化寫字樓里,落地大玻璃窗外一切都模糊了,城市變得朦朦朧朧,一杯咖啡在手的建筑師優雅地畫著草圖,他腦海里憧憬著安藤忠雄的風之教堂、光之教堂、水之教堂……窗外的影子都到哪里去了?!也許只有擺脫了這心頭臆想的光影,我們才能得到涅槃的機會。
二○一六年六月十二日初稿,十五日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