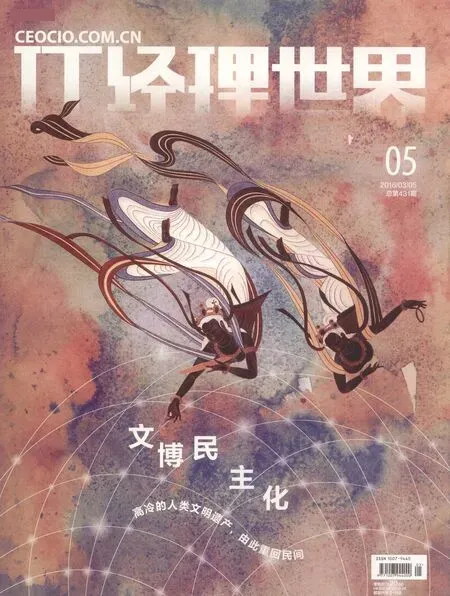我們處在巨變的前夜
胡泳
人們正迎來一個有機而個人化的未來。
想象力的分界線
2011年9月11日,在阿里巴巴的網商大會上,馬云請來《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演講,但他并沒有到現場,而是通過遠程視頻同阿里巴巴的網商分享他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弗里德曼寫過《世界是平的》,這本書認為全球化會取代冷戰,成為新的國際體系,因此它被當做全球化的基本讀物。有意思的是,弗里德曼沒有在視頻里談論《世界是平的》,而是講述了他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外交政策專家邁克爾·曼德爾巴姆合著的新書《那就是曾經的我們》。這本書講到美國發生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弗里德曼認為,中國將和美國面臨相似的境況。
弗里德曼說,世界互聯程度越高,變革就越快,對創新要求就越高。未來,全世界將不能再簡單地以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來劃分,而是可以分成兩類:高想象力國家(HIEs,high-imagination-enabling countries)和低想象力國家(LIEs,low-imagination-enabling countries)。
“如果我有一個創意火花,我可以在臺灣找設計,通過杭州阿里巴巴找廠商來貼牌生產,由一個網站來設計企業LOGO,真正的增值恰在最初的創意之上……”所以,在這個世界上,要么是高創新的國家,要么是低創新的國家。其實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也是如此,要么是高創新的人,要么是低創新的人。
三種思考方式
怎么區分高低想象力?弗里德曼列舉了三種思考方式。
第一,像工匠一樣思考。在中世紀,難以大規模實現批量生產之前,手工藝作坊的工匠們會手工去創造工藝品,無論是鞋、錢包、馬鞍、燭臺,工匠的想法都能灌注到作品中。因此,每個工匠都會把自己的名字簡寫刻在作品上。不要小看這個名字簡寫,它意味著,作為一個工匠,必須要給自己的產品賦予一個特色:這個東西是我全神貫注制作的,是獨一無二的。這樣一種工匠的產品,本身對于想要消費它或者使用它的人來講,具有非常巨大的個性化的號召力。
在網商大會談論像工匠一樣思考本身有一點諷刺,因為互聯網公司信奉的一個東西叫做速度。互聯網講究快,但我們可能要思考一下,是否存在某種慢的功夫,像中國的太極拳一樣,可以以慢打快。
發揮工匠精神的最好口號是“Take pride”,即引以為豪。你需要全神貫注地做你的工作,把一個好想法做深做透,就好像可以把你自己的名字簡寫刻在這個想法上一樣。
第二,像侍者一樣思考。弗里德曼舉了一個例子,他有一次和朋友在餐廳用餐,侍者和他們交流得非常好,決定額外送一份水果。就這么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弗里德曼很慷慨地給了侍者很多小費。因為他覺得這樣一位侍者把顧客所有已經想到和沒有想到的感覺都實現了。
由于侍者提供了額外的服務,弗里德曼就給她以額外的回報。這里所謂額外的服務就是,侍者給了弗里德曼和他的朋友額外的一份水果。
這個額外舉動取決于兩點:第一,這個姑娘所能控制的并不多,但她的確可以控制她的水果籃,那就是她的額外水果的來源。第二,現場的行為表明這個服務員具有企業家精神,因為她能夠在自己的領地里決定自己同用戶的關系。所以弗里德曼很感慨地說,一個服務員完全可以像一個企業家一樣來思考問題。
我們這里談論的侍者不是任何一種侍者。你需要具備進取性的企業家精神,改變你自己所能控制的那一塊領地,發現新的業務和新的機會。如果需要給這種思考方式提一個口號,那將是“Be entrepreneurial”,即勇于創業。
像侍者一樣思考,最終是為了獲得用戶和留住用戶。互聯網時代是一個消費者主權的時代,有沒有好的服務能力和服務意識,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企業是否能在這樣的經濟當中成功。
第三,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像新移民一樣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中,人們到處流動,而到了一個新地方要想生存下去,唯一的辦法是比當地人更勤奮,并且還有比他們更多的聰明才智。
《世界是平的》一書中,有一段極為煽情的話:“小時候我常聽爸媽說:‘兒子啊,乖乖把飯吃完,因為中國跟印度的小孩沒飯吃。現在我則說:‘女兒啊,乖乖把書念完,因為中國跟印度的小孩正等著搶你的飯碗。”為什么美國小孩的飯碗會被印度和中國小孩搶?因為印度和中國的孩子移民了。新移民不會坐等機會,也沒有先天優勢,只會調動所有的身體能量和聰明才智去爭搶機會。
人們為什么去美國?為什么見到埃利斯島上的自由女神雕像會激動?198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自由女神像列為世界遺產。該組織在“意義聲明”中稱,這座塑像是“人類精神的杰作”,“鼓勵思考、辯論和抗爭,成為自由、和平、人權、廢除奴隸制以及民主和機遇的強有力的象征”。也就是說,新移民到美國,首先因為那里為他們提供了實現夢想的機遇;其次,還因為那里與其行為處事的價值觀高度相符,符合他們自己的原則。
從另外一方面看,互聯網的使用有一個說濫了的比喻,即年輕人是互聯網的原住民,而年長者是互聯網的新移民。新移民要想在原住民的場地上生存,就得學習原住民的所有技能。
對于向互聯網轉型的企業來說,這個企業里的所有人,受制于該企業原有的范式,統統都是新移民。如何把自己由新移民變成原住民?需要“Stay hungry”,即保持渴求。
不了解從內容產出、產品運營再到社會化推廣的整個過程;不了解迭代與用戶體驗之間的關系;不了解如何開發殺手應用;不了解如何引流、建立社區等等,怎么辦?唯一的辦法是學習和實踐。承認自己的不足,懷抱一種小學生般的態度,勇于行動,也敢于失敗。如果努力學習了也不合格,那么唯有一個辦法:讓原住民來當家,自己扮演支持者的角色,讓出舞臺來。
一切都在從垂直變得水平
最后,弗里德曼為個人的發展總結說,我們的世界處在向高度互聯的轉型中,下一個工作不是你去找到的,而是你去創造的。所以,必須不斷創造,通過與人的合作,在創新中實現想法。普通人的時代已經結束,一般般的人只能獲得一般般的回報。
但弗里德曼沒有意識到,他的前后敘述存在深刻的矛盾。如果未來全球的競爭以創新和想象力為分界線,而個人的創造力也有高有低,那么這個世界何以變平?“世界是平的”在信息時代只是一種理想。
這一時代真正獨特的地方在于,它不僅僅是國家全球化,不僅僅是公司全球化,而且也是個人持續的全球化。個人必須越來越以全球化的角度思考,將自己置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在個人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將我們自己“水平化”。我們必須改變自身的工作習慣和學習習慣,必須有創意地修正這些習慣去適應嶄新的平臺。這是因為,我們正在離開一個以垂直控制與指揮來創造價值的世界,而走入一個與他人連結、與他人合作來創造價值的世界。人類社會目前處于這一巨變的前夜,一切都在從垂直變得水平。
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保羅·大衛寫了一篇關于電力的文章,給弗里德曼的說法提供了注腳。他問了一個問題:當電力首次出現的時候,為什么人類的生產力沒有突然增加?他研究的結果是,要獲得電力馬達取代蒸汽引擎的生產力提升,人們必須先重新設計建筑,把高大的可以容納蒸汽引擎和各種滑輪的多層建筑物,改成小型的低矮建筑,讓工廠可利用電力馬達運轉。此后,管理者還要改變他們的管理方法,工人必須要修正他們的生產方式,有難以數計的習慣和結構等待改變。一旦這些改變在某個轉折點產生匯集,轟地一聲,人類就會真正獲得電力所導致的生產力大幅提升。弗里德曼認為,今天我們身處如電力的改變所顯示的進程之中,在水平的平臺上,正學習改變自己的習慣,將自己水平化。
最終,個人必須學會面對一個巨大的范式轉變:無論工作、生活或休閑,我們曾經主要靠組織來聯絡——企業、專業協會、俱樂部社團和旅游公司。然而,我們現在的聯絡,正越來越多地依靠個人活動、網上聯系與自發的網下會晤,以及與熟人、朋友的朋友和陌生人之間的偶然碰面。個人積極地規劃自己的生活,獨立于現有機構或組建非正式的團體,社會變得更具流動性、更加不可預測、自由發展、無拘無束。我們正迎來一個有機而個人化的未來,它有著同樣重要的兩翼:網絡個體化,個體網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