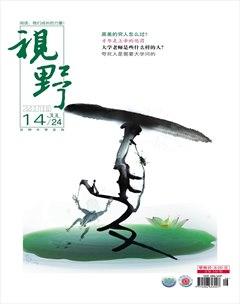粗鄙的明初皇帝
吳鉤
《明太祖實錄》收錄有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的一道諭旨:
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國之本,古者,司民歲終獻民數于王,王拜受而藏諸天府,是民數,有國之重事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數未核實,其命戶部籍天下戶口,每戶給以戶帖。”
于是戶部制戶籍、戶帖,各書其戶之鄉貫、丁口、名歲,合籍與帖以字號編為勘合,識以部印,籍藏于部,帖給之民。仍令有司,歲計其戶口之登耗,類為籍冊以進。著為令。
這道諭旨看起來并沒有什么特別,似乎不值得拎出來說道說道。不過這并不是朱元璋的原話,而是經詞臣、史官之手潤飾、改寫的文字。朱元璋的原文其實是這么說的:
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圣旨:
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戶口不明白俚,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們)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
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里下著速(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 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 來做軍。
欽此。
全文都是大白話,用詞俚俗粗陋,還有一些錯別字。顯然出自大老粗的手筆。有人說,這是頒發給愚氓看的政令嘛,當然要用大白話來寫啰,這樣老百姓才聽得懂啊。那好,國子監的太學生,總是有學問的吧,總該看得懂雅文吧。但朱元璋有一道教訓太學生的敕諭,還是那種大老粗的風格:
恁學生每聽著:
先前那宗訥做祭酒呵,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個個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懷著異心,不肯教誨,把宗訥的學規都改壞了,所以生徒全不務學,用著他呵,好生壞事。
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學事,他定的學規,恁每當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著恁呵,都不饒!全家發向煙瘴地面去,或充軍,或充吏,或做首領官。
今后學規嚴緊,若有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帖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個。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將來呵,也一般賞他大銀兩個。將那犯人凌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發往煙瘴地面。
欽此。
這道教訓太學生的敕諭,現在還刻在北京國子監遺址的石碑上——且慢,朱元璋在位時,明王朝尚未遷都北京,國子監還在南京呢,這敕諭怎么跑到北京來了?想來應該是朱棣遷都后,覺得他老爸的敕諭講得非常有道理,足以垂誡百世,所以便將訓詞全文刻于石碑,立在新都的國子監內。
說起來,朱棣跟他老子一樣,身上流氓習氣濃重,也熱衷于寫大白話圣旨。《皇明經世文編》卷一九一收錄有朱棣的一道圣旨,我原文抄錄下來:
那軍家每年街市開張鋪面,做買賣,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買辦?你部里行文書,著應天府知道:今后若有買辦,但是開鋪面之家,不分軍民人家一體著他買辦。敢有違了的,拿來不饒。
欽此。
圣旨的主要意思是說,在京城開鋪的商民聽著,官府向你們索要財物,你們就乖乖交上來,不聽話的,抓起來治罪。
且不說這些圣旨的內容,單看它們的文風,文詞都極粗俗,且字里行間透出惡狠狠的殺氣,不是警告商民“拿來不饒”,就是威脅太學生“梟令在監前”。這樣的粗野文字,居然可以作為國家法令頒行于世,足以說明一個問題:相對于漢唐宋,明初政治出現了嚴重的粗鄙化傾向。

或許有一些朋友會認為,政令文書的語言風格是虛的,形式而已,無關緊要,粗俗就粗俗,沒什么。但我要說,文明的政治,首先需要某種“形式主義”的文飾,包括禮樂、儀式、輿服、修辭,等等。在普通法法系中,法官與律師出庭時要戴假發,這就是輿服上的文飾。只有野蠻的統治才不加修飾。舉個例子,明末,殺人如麻的張獻忠在四川稱帝,要冊立皇后,“問左右以封皇后之禮”,張獻忠見禮數繁多,怒曰:“皇后何必儀注!只要咱老子球頭硬,養得她快活,便是一塊皇后矣。要許多儀注何用?”
這么一個對文明禮儀毫不在乎的土皇帝,也喜歡大白話圣旨。“獻忠一字不識,凡平日發敕書與群下,必口述過,不論鄙惡,悉照其口語書之,如差一字,便殺代書者。”部將劉進忠進攻漢中失敗,張獻忠給他發去一道圣旨問罪:“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漢中去,你強要往漢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許多兵馬。驢球子,入你媽媽的毴!欽哉!”文字之鄙惡,比朱元璋父子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此也可以想見,張氏在四川建立的所謂“大西政權”,離文明至少隔了十萬八千里遠。
事實上,文明的“文”字,本意就是文飾。文通紋,指紋理裝飾。當亞當與夏娃懂得用樹葉來掩飾他們的羞恥心,當人類懂得用衣冠來修飾自己的形貌,那一刻人類文明便誕生了。不妨說,正是“文飾”觸發了“文明”。
“王言”的粗鄙化,還說明了明初政治的另一個問題:國家政令文書的起草與頒發缺乏制度性的嚴密程序。后來內閣制逐漸成熟,明王朝才形成一套比較穩定的圣旨出臺程序:內閣學士“票擬”——皇帝(或代表皇權的秉筆太監)“批紅”——給事中審核——六部執行。內閣還獲得類似于宋代中書舍人“封還詞頭”的權力,如嘉靖年間,楊廷和“先后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換言之,皇權受到一定制約,雖然皇帝含恨在心。此時,明朝詔敕的文風也“漸至駢儷”,粗鄙的大白話圣旨開始退場。(曹耘山摘自“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