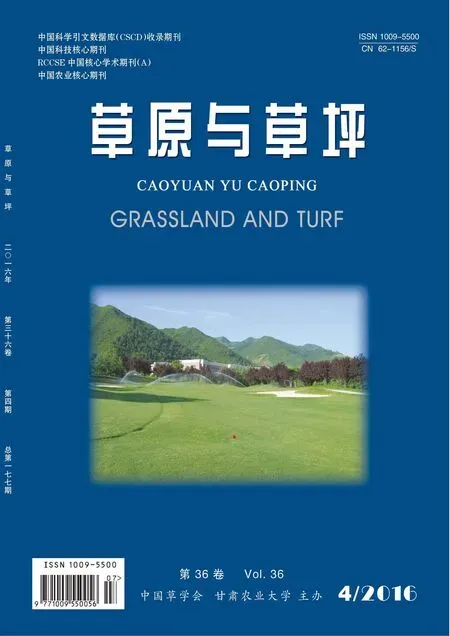9種牧草對青海同德牧區土壤特性的影響
陳懂懂,李 奇,劉 哲,劉力華,翟文婷,4,徐世曉,趙新全,5,趙 亮
(1.中國科學院高原生物適應與進化重點實驗室,青海 西寧 810008; 2.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 西寧810008; 3.青海省工程咨詢中心,青海 西寧 810000; 4.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 100049; 5.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41)
?
9種牧草對青海同德牧區土壤特性的影響
陳懂懂1,2,李奇1,2,劉哲1,2,劉力華3,翟文婷1,2,4,徐世曉1,2,趙新全1,2,5,趙亮1,2
(1.中國科學院高原生物適應與進化重點實驗室,青海 西寧810008; 2.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西寧810008; 3.青海省工程咨詢中心,青海 西寧810000; 4.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100049; 5.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四川 成都610041)
通過對青海省高寒牧區常見的9種多年生牧草單播2年后耕層0~15 cm土壤理化(pH、容重(BD)、有機碳(SOC)、全氮(TN)、無機碳(C)及微生物學性質(微生物生物量碳(Cmic)、氮(Nmic)和群落代謝功能)等指標的測定分析,結果表明,研究區域只有在種植披堿草2年后土壤有機碳含量有所增加,說明與其他草種相比,種植披堿草利于有機質的積累;試驗在每年施肥1次的情況下,土壤氮含量仍然偏低,說明此區氮素被過度利用,處于缺乏水平,因此每年增施氮肥數量、頻率以及時間上應加強管理。通過對不同牧草種植區土壤各因子的聚類分析,發現貧花鵝觀草、無芒雀麥、紫野麥草和扁穗冰草之間相似度較高,表明其對土壤養分及微生物群落功能的影響較為接近,故在大面積種植的時候可根據牧草地上生物量/質量的高低進行選擇性播種。從土壤質量方向考慮,種植雜花苜蓿、紅豆草和西北羊茅不利于土地的改良。
牧草單播;土壤養分;微生物生物量;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樣性
青海境內有草地36.45×106hm2,但長期受多種自然和人為因素影響,草地環境受到嚴重破壞,草原生產力大幅下降。為遏制草地生態環境惡化,實現草地生產可持續發展,2000年農業部開展了大規模的草地生態建設,并將人工種草及草地改良作為一項基本措施[1]。人工草地不僅能給家畜提供飼草料,還廣泛用于防風固沙、水土保持等生態建設[2]。青海省草地類型復雜,氣候惡劣,對其進行人工種草及改良并取得經濟和社會效益,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選擇適應性強的高產優質牧草品種[1]。青海草原工作者的工作多集中在基于適應性強[3-5]、高產優質[1,6-7]牧草品種的篩選、馴化等研究,而忽略了牧草種植對土壤質量的影響。
土壤作為一個基本的環境要素,與地上動植物和土壤生物三者共同構成了土壤生態系統,它們之間不斷地進行著物質和能量交換,土壤成為生物生長所需養分物質的源和匯,許多生物過程需要在土壤中完成[8]。植物的生長需要不斷地通過根系從土壤中吸取水分和養分,同時需要土壤作為基礎支撐,而地上部分植物生長及覆蓋也不斷地改變著土壤的理化性狀和微生態環境;此外,植物根系不斷地分泌有機物質,同時也在不斷地進行呼吸作用,釋放二氧化碳,改變著根際土壤環境及根際微生物群落結構,從而影響著土壤中的許多理化和生化過程[9]。不同植物種群對土壤化學元素特性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作用于地上和地下凋落物的數量和質量以及土壤微生境進行[10]。
通過對青海省高寒牧區9種不同多年生人工牧草種植區土壤養分及微生物群落代謝功能的比較,評價不同種多年生牧草單播對土壤質量的影響,為牧草品種的篩選以及土壤改良提供數據支撐;以期將牧草種植與草地土壤固碳功能相結合,在后期的牧草篩選中將其固碳功能作為因子之一加以考慮。
1 材料和方法
1.1研究區域概況
試驗地設在青海省海南州的同德縣,地理坐標N 34°38′~35°39′,E 100°08′~101°09′,位于青藏高原東部,平均海拔3 700 m。屬大陸高原性氣候,年日照時數2 550~2 760 h,年均溫-3.7~ -6.1℃,年降水427.2 mm,多集中于6~9月,雨熱同季,冷暖兩季分明。全縣草地面積47.16萬hm2,草地類型主要為高寒草甸、高寒草地、山地干草原[11]。試驗開展于同德牧場,位于青海省同德縣東北部巴灘地區(距離同德縣東約5 km處),土壤以暗栗鈣土為主。牧場試驗場多用于優質牧草選育等工作。
1.2研究方法
1.2.1試驗設計選取同德牧場3.5 m×6.5 m的小區9個,并將每個小區分成面積2 m×3 m的樣區,共27個小樣區,相鄰樣區之間間隔30 cm。于2011年5月播種,選取9個品種,行播,完全隨機排列,重復3次。在播種之前整個小區內土地是勻質的,種植期間施肥量均一致(在播種前于每個小區采集一個樣品共9個樣品混成一個混合樣,測定土壤背景值)。施有效N為46.897 kg/hm2;P2O5為72.804 kg/hm2;頻率為1年1次,時間為返青之前。播種之前的土壤背景值為土壤有機碳(SOC) 21.65 ± 0.33 g/kg,全氮(TN) 2.38±0.02 g/kg,土壤無機碳(SIC) 69.75 ±1.24 g/kg,C/N比9.11±0.19,pH 7.65±0.03,土壤容重(BD)1.16±0.14 g/cm3。
種植的牧草品種分別為:西北羊茅(Festucakryloviana),披堿草(Elymusdahuricus),貧花鵝觀草(Roegneriapauciflora),草原看麥娘(Alopecuruspratensis),紫野麥草(Hordeumviolaceum),扁穗冰草(Agropyroncristatum),無芒雀麥(Bromusinermis);雜花苜蓿(Medicagovaria),紅豆草(Onobrychisviciaefolia)。
1.2.2土壤樣品采集與測定于2013年,即牧草種植2年后的8月(8月底完成牧草收割)采集土壤0~15 cm耕層,隨機取樣,每個小區隨機選取3個點,取土后混合成一個樣品,每種牧草取3個土樣,混合,自封袋保存。立即帶回實驗室,過2 mm篩,去除根及其他雜物后,分成2部分。一部分風干,過0.15 mm篩,用于土壤養分等測定;一部分4℃保鮮保存,用于水分、微生物生物量及群落功能測定。
SOC用硫酸-重鉻酸鉀氧化法,TN采用凱氏定氮法;SIC用碳酸測定儀測定;BD采用環刀法、土壤含水量采用烘干法,pH用PHS-3C型pH計測定。土壤微生物量碳、氮(Cmic,Nmic)采用氯仿熏蒸浸提法[12]。
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樣性應用BIOLOG法,取土壤10 g,加90 mL滅菌生理鹽水(0.85%)在搖床上振蕩30 min,然后將土壤樣品稀釋至10-2倍,再從中取150 μL該懸浮液接種到BIOLOG微平板中的每一個孔中,最后將接種好的板置于25℃的恒溫培養箱中培養,每隔24 h在BIOLOG讀數儀上讀數[13]。
平均每孔顏色變化率(AWCD)計算:
式中:Ci為每個有培養基孔(590 nm~750 nm)的光密度值,R為對照孔(590 nm~750 nm)的光密度值,n為培養基數據,EcoPlate板n值為31。
多樣性指數采用Shannon-Wiener指數(H′)
式中:Pi為有培養基的孔與對照孔的光密度值差與整板總差的比值,即
試驗采用BIOLOG微平板培養第72 h的數據,來比較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樣性。
1.3統計分析
所有測定指標均采用單因素ANOVA分析;LSD檢驗分析在P<0.05比較平均值;用層序聚類分析中的平均距離法分析9種牧草之間的相似性。所有統計分析都在SPSS 18.0和Excel 2010中進行。
2 結果與分析
2.1不同牧草單播土壤理化性質比較
土壤SOC和TN呈現極好的相關性(R2=0.777,P<0.01)。播種2年后,披堿草單播土壤SOC和TN含量最高,但只有SOC比對照(種草前裸地)稍高,并遠遠高于其他牧草種植區(P<0.01);其他種植區的土壤SOC均低于對照區,而所有種植區的TN含量均低于種植前的水平(表1)。牧草種植區土壤SIC與SOC和TN呈負相關,尤其與SOC極顯著負相關(R2=-0.541,P<0.01),且含量遠高于SOC含量,在土壤總碳(TC=SOC+SIC)中含量可達76.3%~83.1%;種植2年后,整個種植區的無機碳均顯著增加,增加幅度從2.27%~32.17%。不同牧草種植區的土壤碳氮比(C/N)變化在9.02~10.03,除豆科2個種和無芒雀麥外,而種植其他牧草2年后土壤C/N比較對照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表1 不同牧草單播人工草地土壤養分含量比較
注:數值為均值±標準誤,同列不同小寫字母表示顯著差異(P<0.05),下表同
種植牧草后,整個種植區與對照相比,容重有所降低,尤其是種植豆科(2個種)和紫野麥草的土壤BD與其他種相比更低,整個種植區BD變化為1.00~1.14 g/cm3。pH結果表明,雖然不同牧草種植區之間存在差異,根據中國土壤的劃分標準[14],整個種植區土壤質地為中性偏堿,pH變化為7.54~7.67。
2.2土壤生物學性狀
2.2.1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扁穗冰草、貧花鵝觀草、紫野麥草和無芒雀麥之間土壤Cmic無顯著差異;西北羊茅,草原看麥娘和雜花苜蓿紅豆草的土壤Cmic含量遠遠低于其他牧草品種。種植披堿草、扁穗冰草與貧花鵝觀草之間的土壤Nmic無顯著差異,與草原看麥娘、西北羊茅和紅豆草之間差異顯著。土壤Nmic與Cmic之間相關顯著(R2=0.695,P<0.01)。
微生物熵[Cmic/SOC(%)]是微生物對碳累積潛力的一項指標,它充分反映了土壤中活性有機碳所占的比例,從微生物學角度揭示土壤肥力的差異[15]。種植區內Cmic/SOC(%)在不同牧草種植區內的變化與Cmic和Nmic的變化基本一致,Cmic/SOC(%)變化范圍為(0.58~1.50)%,其中,豆科2個種和禾本科的西北羊茅土壤中微生物對碳的固定較低(表1)。
2.2.2土壤微生物群落活性及功能多樣性BIOLOG試驗結果(AWCD)顯示出不同牧草單播的土壤微生物群落對不同碳源的代謝強度的差異性(圖1,表2)。隨著培養時間延長,土壤微生物對不同碳源利用程度增大,到192 h基本趨于平穩。9種單播牧草土壤中微生物活性有基本類似的變化趨勢。種植扁穗冰草的土壤中微生物對碳的利用變化最快;而紅豆草單播土壤微生物活性最弱。種植扁穗冰草的土壤微生物對碳源的利用強度與無芒雀麥之間無顯著差異;無芒雀麥,禾本科披堿草,貧花鵝觀草,草原看麥娘,紫野麥草,雜花苜蓿之間差異不顯著;它們均與西北羊茅和紅豆草之間差異顯著(P<0.01)。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謝功能多樣性指數(H′)與AWCD顯著正相關(R2=0.774,P<0.01),兩者耦合性較好。

圖1 不同牧草單播人工草地土壤微生物群落AWCD值的時間變化Fig.1 Kinetic changes in AWCD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within the incubation time (192 h) in 0~15 cm soil layer under different sowed grasslande
3 討論
土壤SOC和TN是土壤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播種披堿草2年后土壤SOC和TN含量最高,但只有SOC比對照(種草前裸地)稍高,其他種植區的土壤SOC均低于對照區,而所有種植區的TN含量均低于種植前的水平。說明播種2年后,在該研究區域,與其他草種相比,披堿草對土壤有機質有更大的貢獻;同時說明該區多數牧草對氮元素存在過度利用,在每年施加氮肥一次的情況下,氮素仍處于缺乏水平。

表2 不同牧草單播人工草地土壤微生物代謝活性及多樣性指數
土壤SIC主要是指土壤風化成土過程中形成的發生性碳酸鹽礦物態碳(主要以CaCO3的形式),其在全球碳循環中起重要作用[16]。在試驗區,牧草種植2年后,整個種植區的無機碳均顯著增加。可能是SOC分解后釋放的CO2經過沉淀,最終增加了土壤碳酸鹽含量;同時,在一定程度干旱、CO2分壓較小以及pH較高的土壤環境中,含鈣礦物質的風化以及外部環境提供的Ca2+都能促進CaCO3的形成[17],而根據測定結果顯示該研究區域土壤干旱(含水量在10%),且pH>7.5。
在研究區,不同牧草種植區的土壤碳氮比(C/N)變化在9.02~10.03,除豆科2個種和無芒雀麥外,種植其他牧草2年后土壤C/N比較對照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一般而言,當土壤C/N比在15~25,C/N比較高,有機質供肥狀況優越;而C/N比較低時,說明微生物分解活動能力增強,從而加快了土壤中有機質的分解,使有機碳含量下降,不利于有機質的積累。所以C/N比的下降也是反映土壤肥力退化的一個重要指標[18]。試驗結果表明,在研究區種植豆科和禾本科牧草促進了有機質的分解,這可以結合無機碳的結果加以驗證。
土壤BD是衡量土壤孔隙度的重要指標,同時還可以說明土壤對水分的滲透度和滲透速率的大小[19]。種植牧草后,整個種植區與對照相比,容重有所降低,尤其是種植豆科(2個種)和紫野麥草的土壤BD與其他種相比更低,可能跟這3種植物的根系對土壤的疏松有關[20],說明種植這3種牧草對改善土壤孔隙度和水分滲透等有一定的作用;但從整個種植區BD變化分析,整個區域土壤容重正常(1.05~1.20 g/cm3)[21]。
土壤微生物量是活的土壤有機質部分,又是土壤養分的儲存庫和植物生長養分的重要來源[22],是有機質動態的敏感指標。當環境發生變化時土壤微生物量比有機質變化更加敏感,因此,微生物量又是反映土壤干擾的靈敏的生物學指標[23-24],故土壤微生物量的測定對理解和預測土地利用變化的長期作用以及相關的土壤狀況是有積極意義。研究結果顯示扁穗冰草、貧花鵝觀草、紫野麥草和無芒雀麥之間土壤Cmic無顯著差異,其值遠高于西北羊茅,草原看麥娘和雜花苜蓿紅豆草(P<0.01)。土壤Nmic與Cmic有相似的變化。多數研究發現土壤微生物量與土壤有機質之間關系密切[25-27],而在研究中沒有發現它們之間的相關性,這與不同研究區域的生態系統差異有關[28]。
微生物熵(Cmic/SOC)比單一的生物量和/或有機質更能反映土壤生態系統受到人為干擾后的效果,能監測土地退化及恢復過程[29]。種植區內Cmic/SOC(%)變化為0.58%~1.50%。王長庭等[30]對三江源區高寒草甸退化草地土壤Cmic/SOC(%)的研究結果為0.26%~0.49%,任佐華等[31]對三江源區高寒草原土壤的研究結果為0.27~0.73%,李世卿等[27]得出的放牧影響下土壤Cmic/SOC(%)的值為0.35%~0.77%,諸多對比分析,說明牧草種植對天然/退化草地恢復有一定的效果。
土壤微生物在BIOLOG微平板上的AWCD是反映土壤微生物活性,即對碳源利用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13,32]。研究土壤微生物群落對不同碳源利用能力的差異,有助于全面了解微生物群落代謝功能特征。培養基多樣性指數表明的是土壤微生物群落利用碳源類型的多與少,即功能多樣性。研究表明,扁穗冰草AWCD和(H′)較高說明與其他牧草相比,其對碳源利用能力較強且利用碳源類型也較多。
通過對不同牧草種植區土壤各因子的聚類分析(包括土壤理化性質以及微生物學特性),發現貧花鵝觀草、無芒雀麥、紫野麥草和扁穗冰草之間相似度較高,表明它們對土壤養分及微生物群落功能的影響較為接近,故在牧草種植的時候可根據地上生物量及牧草品質的高低進行選擇性播種(圖2)。種植雜花苜蓿,紅豆草(均為引進種)和西北羊茅后土壤整體質量相對較差,不利于土地改良。

圖2 聚類分析Fig.2 Cluster analysis of soil factors under different sowed grassland注:圖中Case 1-西北羊茅;Case2-披堿草;Case 3-貧花鵝觀草;Case 4-草原看麥娘;Case 5-紫野麥草;Case 6-扁穗冰草;Case 7-無芒雀麥;Case 8-雜花苜蓿;Case 9-紅豆草
4 結論
在研究區域內,種植披堿草更利于有機質的積累。
研究區每年施肥一次時,土壤氮含量仍然偏低,說明此區氮素被過度利用,處于缺乏水平,故在每年增施氮肥數量、頻率以及時間上應加強管理。
貧花鵝觀草、無芒雀麥、紫野麥草和扁穗冰草之間相似度較高,表明它們對土壤養分及微生物群落功能的影響較為接近,故在牧草種植的時候可根據地上生物量及牧草品質的高低進行選擇性播種。
從土壤質量方向考慮,種植雜花苜蓿、紅豆草和西北羊茅不利于土地的改良。
[1]紀亞君.青海省牧草育種研究進展[J].草業科學,2009,26 (11):86-92.
[2]趙永富.幾種優良牧草的種植試驗[J].草原與草坪,2014,26(1):57-59.
[3]施建軍,王柳英,馬玉壽,等.“黑土型”退化草地人工植被披堿草屬三種牧草的適應性評價[J].青海畜牧獸醫雜志,2006,36(1):4-6.
[4]施建軍,王柳英,馬玉壽,等.“黑土型”退化草地人工植被早熟禾屬10種牧草的適應性評價[J].青海畜牧獸醫雜志,2006,36(4):14-16.
[5]秦愛瓊,朱勇,馬金英,等.藏北地區9種牧草栽培試驗初報[J].草業與畜牧,2012,33(04):27-29.
[6]施建軍,馬玉壽,董全民,等.“黑土型”退化草地優良牧草篩選試驗[J].草地學報,2007,15(6):543-555.
[7]陳鴻洋,傅華,黃德君,等.高寒地區垂穗披堿草優異種質資源篩選[J].中國農業科學,2013,46(4):841-848.
[8]郭艷玲.多年生禾草對土壤理化性質的影響[D].北京:中國農業大學,2005:10.
[9]趙鈺.四種牧草對土壤生化性質的影響[D].蘭州:蘭州大學,2013:8-9.
[10]吳建國,艾麗.祁連山3種典型生態系統土壤微生物活性和微生物量碳氮含量[J].植物生態學報,2008,32(2):465-476.
[11]周華坤,趙新全,王啟基,等.青海省同德縣草地現狀及畜牧業可持續發展策略[J].草原與草坪,2007,27(04):7-12.
[12]柴曉虹,姚拓,王理德,等.圍欄封育對高寒草地土壤微生物特性的影響[J].草原與草坪,2014,34(5):26-31.
[13]馬驛,陳杖榴,曾振靈.恩諾沙星對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樣性的影響[J].生態學報,2007,27(8):3400-3406.
[14]黃昌勇.土壤學[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0:171-179.
[15]Sparling G P.Ratio of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to soil organic carbon as a sensitive indicator of change in soil organic matter[J].Australia Journal of Soil Research,1992,30(2):195-207.
[16]楊黎芳,李貴桐.土壤無機碳研究進展[J].土壤通報,2011,42(4):986-990.
[17]王海榮,楊忠芳.土壤無機碳研究進展[J].安徽農業科學,2011,39(35):21735-21739.
[18]高寒,王宏燕,李傳寶,等.玉米秸稈不同腐解處理還田對黑土碳氮比的影響研究[J].土壤通報,2013,44(6):1392-1397.
[19]李篤仁,高緒科,汪德水.土壤緊實度對作物根系生長的影響[J].土壤通報,1982,14(3):20-22.
[20]李志洪,王淑華.土壤容重對土壤物理性狀和小麥生長的影響[J].土壤通報,2000,31(2):55-57.
[21]王金貴,王益權,徐海,等.農田土壤緊實度和容重空間變異性研究[J].土壤通報,2012,43(3):594-598.
[22]Singh J S,Raghubanshi A S,Singh R S,etal.Microbial biomass act as a source of Plant nutrients in dry tropical forest and savanna[J].Nature,1989,338:499-500.
[23]Ocio J A,Brookes P C.An evaluation of methods for measuring microbial biomass in soils following recent additions of wheat straw and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biomass that develops[J].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1990,22(5):685-694.
[24]單貴蓮,初曉輝,羅富成,等.圍封年限對典型草原土壤微生物及酶活性的影響[J].草原與草坪,2012,32(1):1-6.
[25]Sun G,Luo P,Wu N,etal.Stellera chamaejasme L.increases soil N availability,turnover rates and microbial biomass in an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on the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of China[J].Soil Biology Biochemistry,2009,41(1):86-91.
[26]徐麗君,王波,辛曉平.紫花苜蓿人工草地土壤養分及土壤微生物特性[J].草地學報,2011,19(3):406-411.
[27]李世卿,王先之,郭正剛,等.短期放牧對青藏高原東北邊緣高寒草甸土壤及微生物碳氮含量的影響[J].中國草地學報,2013,35(1):55-66.
[28]陳懂懂,孫大帥,張世虎,等.放牧對青藏高原東緣高寒草甸土壤微生物特征的影響[J].蘭州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47(1):73-77.
[29]唐玉姝,魏朝富,顏廷梅,等.土壤質量生物學指標研究進展[J].土壤,2007,39(2):157-163.
[30]王長庭,龍瑞軍,王啟蘭,等.三江源區高寒草甸不同退化演替階段土壤有機碳和微生物量碳的變化[J].應用與環境微生物學報,2008,14(2):225-230.
[31]任佐華,張于光,李迪強,等.三江源地區高寒草原土壤微生物活性和微生物量[J].生態學報,2011,31(11):3232-3238.
[32]鄭華,歐陽志云,方治國,等.BIOLOG在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樣性研究中的應用[J].土壤學報,2004,41(3):456-461.
Effects of 9 forage species on soil properties in the alpine pastoral region of Qinghai Province
CHEN Dong-dong1,2,LI Qi1,2,LIU Zhe1,2,LIU Li-hua3,ZHAI Wen-ting1,2,4,XU Shi-xiao1,2,ZHAO Xin-quan1,2,5,ZHAO Liang1,2
(1.KeyLaboratoryofAdaptationandEvolutionofPlateauBiota,NorthwestInstituteofPlateauBiolog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Xining,QinghaiProvince810008,China; 2.NorthwestPlateauInstituteofBiology,theChineseAcademyofSciences,Xining,QinghaiProvince810008,China; 3.QinghaiEngineeringConsultingCenter,Xining,QinghaiProvince810000,China; 4.Graduate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49,China; 5.ChengduInstituteofBiolog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Chengdu610041,China)
The soil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including soil pH,bulk density,organic carbon,total nitrogen and inorganic carbon),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and nitrogen,community functional diversity and their metabolic activity were all measured in the arable layer (0~15 cm soil) after planting 9 perennial grasses for 2 years in the alpine pastoral areas located in north-eastern Tibet Plateau.The results showed that,compared to other grasses,Elymusdahuricuswas conduciv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organic matter in the soil.The soil N was used excessively result in its insufficiency in this region,Therefor,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in term of nitrogen application amount,frequency,and application time.Based on the clustering analysis of soil factors,we found thatRoegneriapauciflora,Bromusinermis,HordeumviolaceumandAgropyroncristatumhad higher similarity,which implied that they had similar effects on soil nutrients and microbial community.Based on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or forage quality,these forages should be considered preferentially.Considering the soil quality,Medicagovaria,Onobrychisviciaefolia,Festucakrylovianawere not good forages for land improvement.
grass unicast;soil nutrients;microbial biomass;microbial community functional diversity
2015-11-06;
2016-04-12
青海省科技項目(2011-Z-734);青海省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2013-Z-941Q);中國科學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XDA05070200);國家科技支撐計劃(2012BAD13B0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 41030105)資助
陳懂懂(1982-),女,山東廣饒人,助理研究員,博士,研究方向為土壤生態學。
E-mail:chendd@nwipb.cas.cn
S151.9
A
1009-5500(2016)04-0041-07
趙亮為通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