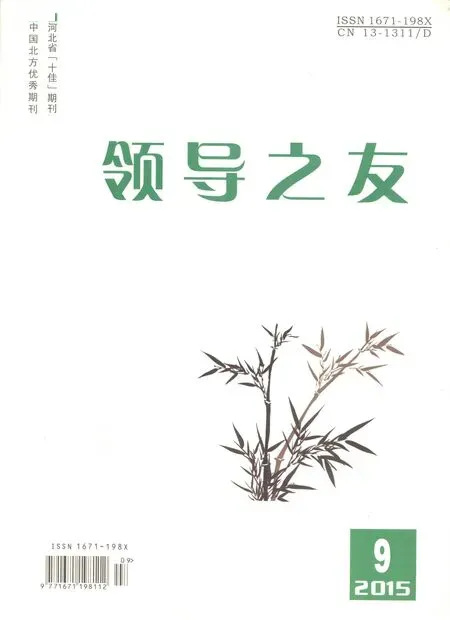藥酒
朱會(huì)鑫
縣長(zhǎng)張寶樂的老爸是村里的老支書。聽說老支書今天過七十大壽,村里人都來為老支書祝壽。這不,吃過早飯,也就是八點(diǎn)多鐘吧,便有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領(lǐng)導(dǎo)從四面八方趕來了。
由于來客太多,到了十點(diǎn)來鐘的時(shí)候,知客就吩咐擺下了兩張賬桌,靜候已久的賓客蜂擁而上,立馬里三層外三層地把賬桌圍了起來。正在這時(shí),張縣長(zhǎng)走了出來,態(tài)度堅(jiān)決地說:“今天一分禮錢都不收,到時(shí)候一起跟老爺子喝一杯就行了。”
十二點(diǎn)準(zhǔn)時(shí)開席。碗碗碟碟的各色菜肴上齊以后,開始上酒了,誰都沒有想到的是,每張桌子上上了一個(gè)酒壇子,再看那壇子上的標(biāo)簽,“老白干”三個(gè)大字赫然入目。
所有的賓客無不大跌眼鏡,如今鄉(xiāng)下人辦事,用酒再不上檔次,也得是二十來塊錢一瓶的,這倒好,讓我們喝四五塊錢一斤的老白干。這種念頭,各人也只是在心里一閃而過而已,是沒人說出口的。
待所有賓客都斟滿了杯中酒以后,老支書左手拿著小喇叭,右手端著酒杯站了起來,一旁的寶樂縣長(zhǎng)趕忙起身陪站在旁邊。老支書慢條斯理地說:“各位鄉(xiāng)親都知道,我老頭子這一輩子從不喜歡大操大辦,可這次,是我硬頭要辦的。也許有的人會(huì)說我老頭子是因?yàn)橛袀€(gè)做縣長(zhǎng)的兒子想顯擺顯擺,我要是說不是那么回事的話,你們相信不?說句掏心窩子的話,我今天啊,就是想請(qǐng)你們來喝喝這‘老白干,這可是上好的‘藥酒啊,它能救人呢!”老支書深情地回憶起十年前的往事。
十年前的今天,老支書六十大壽,沒有驚動(dòng)一個(gè)外人,一家人聚到一起吃了一頓團(tuán)圓飯。酒席上,當(dāng)上鄉(xiāng)長(zhǎng)的寶樂打開自己帶回來的高檔白酒。老支書望著包裝精美的酒瓶,探問道:“這酒一瓶要幾十塊吧?”
“爸,您好大口氣。八百多一瓶呢!”
“八百多?這酒是你自己買的?”
“爸,您老問這么多干嗎?有酒您就喝唄!”
老支書顫巍巍地端起酒杯,自言自語道:“我的乖乖,這一瓶也就六十多杯,這一小杯酒十幾塊錢啦……”
“爸,這酒可好喝了,喝再多都不上頭,您喝口試試,保準(zhǔn)您說好!”
老支書與眾兒女碰了一下酒杯后,將一杯酒一仰脖子喝了下去。寶樂笑問:“爸,怎么樣?是不是好酒?”
讓眾兒女意想不到的是,老支書搖了搖頭,眼眶里淚水直打轉(zhuǎn),半天才說:“這酒好苦!”
“爸,這酒怎么會(huì)苦呢?您怎么還掉眼淚了呢?”寶樂急問道。
“是啊,爸,您這是怎么了?”其他幾個(gè)兒女也齊刷刷地望著老支書。
老支書深嘆了一口氣說:“這確實(shí)是一杯苦酒啊,十年后的今天,恐怕寶樂是不是在大牢里,都說不定呢!”
“爸,您怎么說這話呢?”寶樂有點(diǎn)兒不高興。
“寶樂啊,你知道這‘貪字為什么是‘今字下面一個(gè)‘貝字嗎?它就是要警示后人不要貪呀。現(xiàn)時(shí)貪來的財(cái)物,只是過眼云煙,你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貪它干嗎呀?古人云‘因嫌紗帽小,卻把枷來扛,這道理你能不懂嗎?”
“爸,我錯(cuò)了,我知道以后該怎么做了。”寶樂雙膝跪倒在老支書的膝下。
老支書回身拿過自己喝了二三十年的老白干,為自己斟上,眾兒女也都給自己斟上了老白干。老支書說:“還是這酒好啊,雖然勁頭大了點(diǎn)兒,喝下去有點(diǎn)兒火辣辣的,可它能祛除體內(nèi)的污濁之氣……”
從那以后,寶樂的床頭始終擺放著一瓶二兩裝的老白干。
老支書望著寶樂動(dòng)情地說:“是這‘老白干救了你啊。”說到這兒,他掃視著所有來賓招呼道:“來,大伙兒一起來干上一杯這有特殊藥效的‘老白干!”
有必要交代一下的是,各大鄉(xiāng)鎮(zhèn)、部委辦局的領(lǐng)導(dǎo)在跟老支書告別的時(shí)候,都誠(chéng)心誠(chéng)意地從老支書那兒討了一瓶二兩裝的老白干,他們心里都喜滋滋的,說這回真的賺大了。
(責(zé)編 / 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