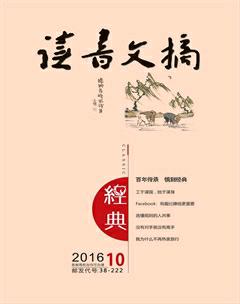工于謀國,拙于謀身
2016-10-11 23:53:26龔令民
讀書文摘·經典
2016年10期
龔令民
現在人說王安石是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但與王安石同時代的人卻說他是一只獾。
站在今人的角度,這些自然只是笑談,不過這笑談背后透露出的卻是時人“不是笑談”的心理。明人袁褧在《楓窗小牘》中說:王安石變法不久,有人在大相國寺墻壁發現了一首詩:“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拓條。阿儂去家京洛遙,警心寇盜來攻剽。”
蘇東坡說,這是一首含籖詩:首一句,終歲,即十二月,為“青”字。荒蕪即田上長草,為“苗”字。湖浦焦,為去水,為“法”字。三字合攏則為“青苗法”;第二句,貧女戴笠即“安”,落拓條即“石”,合二為一則為“安石”;第三句,阿儂為吳方言,意為“吾”,在此通“誤”,京洛是國都,于是借指為“國”,二者合則為“誤國”;第四句,“寇盜”皆民之賊也,換種說法即“賊民”,四句合起來正好是九個字:“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
但就是這個群眾眼里“誤國誤民”的王安石交給皇帝的卻是一份不錯的經濟答卷。立國日起,趙宋王朝的財政就不給力。而王安石上臺后,這一情況徹底扭轉。可即使如此,王安石依舊不受待見,到處都是嘲笑和譏諷的人。
北宋末以敢言著稱的名臣陳瑩中就說“尋常學者須知得王介甫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介甫十分不是,便是十分好人。”這樣的情況不獨宋代有,歷代都有。跟王安石一樣,之前的很多年,張居正幾乎就是奸臣的代名詞。
其實張居正生活的時代,大明王朝已岌岌可危。是他動用非常手段,大肆改革,使王朝出現了中興的跡象。……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