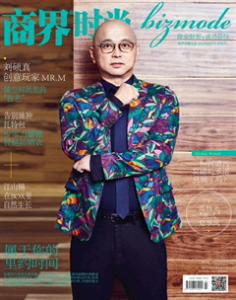韓硯朝 在不可知的世界中渡波前行
王筱
在剛剛過去的8年中,沒有什么比“水”更讓韓硯朝著迷的了。在他的心中,水有五德,至剛至柔,可高可低,不論是物理形態還是哲學深度都出神入化;在他的筆下,水有千百張面孔,深不可測的海面、看似平靜的湖水、冰川與洪水、沒有原因的水花……無邊無界地躍然紙上,似乎都在隱喻著往事的不可追、來日的不可知。韓硯朝是堅定的不可知論者,他深知全知的彼岸遙不可及,而水就是通往彼岸的路——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BM=BIZMODE
H=韓硯朝
BM:可以看到這次展覽的許多作品都是以黑與白為主色調,在色彩的運用上你有怎樣的考慮?
H:其實色彩也一直都在畫,但是主要傾向于黑白的居多。因為我覺得黑白能夠跟生活拉開一點距離,這樣的距離感給一些聯想以空間。水這個主題也是更抽象一些,所以用黑白居多。后來在創作過程中,我覺得有些色彩也能夠帶進某些情緒去,所以也并未完全拒絕色彩的運用。
BM:每一幅作品都有具體的場景來源嗎?有沒有完全源自于想象從而被構建出來的?
H:基本上都是來源于一些具體的場景。像《今夜無人入眠》,我深圳的家位于海邊,有的時候失眠或者睡眠不太好,我就會去海邊走走。有一天也是失眠夜,我就去到海邊,那附近我很熟悉,在那種特別安靜的情況下,夜半聽到海浪的聲音,就感覺到好像全世界只有我自己一個人醒著。我有時候會聽一些歌劇,那天半夜帶著那樣一種心境回到工作室的時候,剛好在播放著的歌劇唱段就是帕瓦羅蒂的《今夜無人入眠》,它的聲音感覺就排山倒海地過來,瞬間我就覺得這兩個東西之間產生了某種共通的感覺,后來就有了這個創作。
BM:似乎江、河、海都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湍急、奔流、洶涌等景象,而湖相對讓人感到平靜。《那片并不平靜的湖》系列是起源于怎樣的創作思考?
H:有次我去到一片湖,和同去的朋友聊起,當初老舍就是跳湖自盡的。就感慨,湖還會是那個湖,看起來也依然是那么平靜,但是在這個地方曾經發生過一些特別不平靜的事。在中國,往往有些事情發生了,但是只過了很短的時間就被人們忘記了,感覺就像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實際上就像我們的歷史,我們有幾千年的燦爛文明,但有時候感覺跟這個文明好像距離很遙遠,好像在我們這塊土地上什么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但實際上卻發生過很多很多特別不平靜的事。
BM:你的作品中是沒有出現人的,甚至許多作品中只有水一種元素,但卻能讓人感覺到一種張力,這是如何實現的呢?
H:我是這樣想的,我的作品中沒有出現人,人去哪兒了呢?其實人就是畫家自己和觀眾。我覺得畫家和觀眾是站在場景旁邊的,共同形成了人與世界之間一個旁觀者的關系。有的時候我感覺自己是這個世界的一個比較冷靜的旁觀者,然后去看,去觀察。像《噗通一聲》,其實就是一個東西掉水里了,濺起了水花,可以想象成是一塊石頭掉了進去,也可以想象成是一個人跳進了湖里。就像一位評論家給我寫的,“沒有原因的水花”或者說沒有原因的漣漪,不知道這朵水花與漣漪之前發生了什么,就去猜。這種猜就會讓作品更有意思。它不像有些作品那樣特別明確地指向什么事件,它不針對具體的事,但是很多事都可能包括在作品所強調的這種聯想當中去。我的作品雖然是具象的,但是我認為它們是具有抽象性的,就在于對它們的解讀的這種難度。我們面對抽象作品的時候往往就是面對這種解讀的難度,因為它所表達的意義是經過概括的。我雖然描繪的是一個意象,但是它實際上是從很多事里面抽象出來的一個場景或者說是一個共通的東西。
BM:為什么你對水如此著迷?江、河、湖、海,以及冰雪、冰川,這些水的不同形態中,有沒有你最偏愛的一種?
H:首先我覺得水具有非常好的品德,就是中國哲學要求人要有的仁、智、禮、義、信。“仁”,水的“仁”在于其滋養萬物,萬物有了水才能生機勃勃,這是一種仁愛的品質;水的“智”體現在其至柔和至剛的矛盾統一,比如它既能柔情似水,也能排山倒海,這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水是一種“禮”的載體,比如祭祀用酒、敬佛的水、朋友喝茶;一碗水端平,象征著不偏不倚,即使碗歪了,水也是平的,是為水的“義”,即正義與公平;“信”是說水的信用,我們二十四節氣里面的霜降、雨水等,這一天它都是要來的。其次,水的這五德代表了一種神奇的力量,它上天就是云,落地就是水,從來沒有固定形態,所以它就有一種抽象性,我一直在想在繪畫中怎么把具象的東西和抽象的東西連接起來,水其實就是這樣一種載體。最后,雪山、冰川往往代表著一種神性,一種崇高的東西,比如說梅里雪山的主峰叫卡瓦格博,這是神的名字;而水幻化成液體的時候,又代表著世俗的流動,我覺得水能高能低,有一種哲學和文化上的高度。我并不偏愛水的某種形態,江河湖海其實是一個整體,水這種東西沒有任何分別心。
BM:在畫面上呈現不同狀態的水,具體的繪畫過程差別大嗎?有沒有哪幅作品的創作過程非常特別?
H:基本沒有什么差別。就是在畫《大洪水》的時候耗時特別多,細節基本達到我繪畫的極限了。差不多連續2個月沒出門,每天要畫十五六個小時,周末也不休息,畫到后背有點受傷,挺崩潰的一件事情。因為我對自己的畫有一氣呵成的要求,它的顏色銜接要特別自然,所以要在顏料未干的時候推著畫。又因為它尺寸大,當寬度達到兩米以上的時候,比如每天只推進10厘米,那這個面積和細節都是比較吃力的,好在最后的呈現還可以。在畫的時候用到了一些方法,比如用特別軟的毛刷把一些細節糅到一起,比如說一塊白色和一塊黑色,糅的過程中就會形成一個特別豐富的過渡灰色層次,沒法兒直接用筆去畫出來,就是在用毛刷反復刷的過程中,自然形成。
BM:在你看來,水和岸之間是怎樣的一種聯系呢?
H:有一個詞叫彼岸,這個詞其實是一個哲學名詞,有許多種解釋。比如說我們現代所有的知識是此岸,那么也許我們還不能夠認知的那個未知世界就是彼岸。是什么將岸與岸隔開呢?就是水。水代表著一種無路可走,比如說人們一旦看到一條大河在這兒,基本上就過不去了,也就是無路了。但是水恰恰又無處不是路,只要有一條船,從哪兒走都過得去,基本上它就是這樣一個東西。全知的彼岸是無法到達的,但是水能夠助我們不斷地去接近那個彼岸。
BM:你曾經談到過自己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堅信世界是不可知的,那么一個人窮盡畢生精力所進行的非常有限的探索、經歷和記錄,在你看來有什么樣的意義呢?
H:我們認識的這個世界永遠只是一小部分。比如盲人摸象這個寓言故事,當摸到象腿腿時會覺得它像個柱子,當摸到象身時會覺得它是一面墻,當摸到象耳時可能會覺得大象是一把扇子。我們雖然不是盲人,但即便睜著眼睛,當這個“象”變得無限大的時候,我們仍然只能夠看到它的一個局部。這個無限大的“象”就是我們這個世界。但是這并不等于說我們就不能夠開始去接近真理,雖然總的來講我們無法認識這個世界的全貌,但是階段性的新認識還是會有,比如說我去思考水的五德,從而反過來對我們人的行為或者性格產生一種啟發作用,以水為師得到更多的智慧。這就是一種智慧層面上的進步吧?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我作品的一個寓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