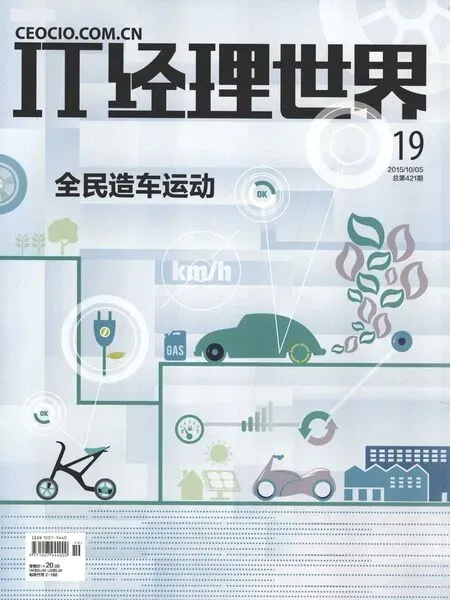他也許是個怪人,但絕不是個混蛋
布倫特·施蘭徳+里克·特策利/文布倫特·施蘭徳+里克·特策利
喬布斯的一生就如同莎士比亞的戲劇,你們都誤解他了。
史蒂夫去世后,關于他的報道鋪天蓋地,有文章、圖書、電影,還有電視節目,大部分只是在重復關于史蒂夫的那些傳說和成見。這些傳說和成見從80 年代起就開始流傳,那時媒體剛從位于庫比蒂諾(Cupertino)的蘋果公司總部挖掘出這位神童。當時,史蒂夫沉浸于媒體的追捧中,對于媒體并不設防,那段時間也是他生活最為散漫、放縱的一段日子,因此媒體在把他描繪成天才的同時,也免不了揭露他的卑劣以及對同事和朋友的漠不關心。后來他開始對媒體設防,只在需要宣傳產品時才與媒體合作,因此這些早期的報道就成了大眾獲知他個性和思維方式的唯一來源。這也許也解釋了為什么在他去世后,關于他的報道展現的幾乎都是一些成見:史蒂夫是一位天才,在設計方面天賦過人, 講故事的能力超凡脫俗,可以產生“扭曲現實”的魔力;他就是個自以為是的混蛋,一味地追求完美,完全不顧他人的感受;他覺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聰明,從來聽不進任何建議,而且從出生伊始,就是天才與混蛋的結合體。
以我對史蒂夫的了解來看,這些成見沒有一個是正確的。在我看來,史蒂夫比我在其他任何文章里讀到的形象都更復雜、更有人性、更多愁善感,甚至更聰明。他去世幾個月后,我開始整理我對史蒂夫的采訪筆記、磁帶和文檔,又回憶起很多已經淡忘的內容。這些舊物我整理了好幾周,整理完后我做了個決定:對于大眾頭腦里關于史蒂夫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見,光抱怨幾句是遠遠不夠的,我要憑借我對他的了解,向公眾展現一位更完整的史蒂夫,在他活著時是沒有辦法如此展現的。采訪史蒂夫的過程引人入勝而又充滿戲劇性,他的一生就如同莎士比亞的戲劇,充斥著傲慢、陰謀與豪情,充斥著十惡不赦的壞蛋與笨手笨腳的傻子,有幸運女神的垂青,有好心好意的忠告,也有出乎意料的結果。如此短的時間里有如此多的跌宕起伏,在他活著時,人們根本不可能完整地刻畫出他的成功軌跡。現在,我要將目光放長遠,重新審視這位自稱是我的朋友的人——史蒂夫。
對于喬布斯的誤解:
誤解一:童年“被拋棄”的段經歷是他暴躁易怒的行為的誘因
史蒂夫·保羅·喬布斯從小就覺得自己是受到優待的,這主要源于撫養他長大成人的養父母,養父母認為他是非常特別的孩子。史蒂夫1955 年2月24日生于舊金山,他的生母喬安妮·席貝爾(Joanna Schieble)決定放棄他的撫養權。當時席貝爾在麥德遜市的威斯康星大學讀研究生,1954 年與一位來自敘利亞的政治學博士在讀生阿卜杜勒法塔赫·錢德里(Abdulfattah Jandali)墜入愛河。席貝爾懷孕后搬到了舊金山,錢德里繼續留在威斯康星大學讀書。保羅和克拉拉·喬布斯(Paul and Clara Jobs)是一對工薪階層夫妻,沒有孩子,在史蒂夫出生幾天后收養了他。史蒂夫5歲時,全家搬到了山景城(Mountain View),很快又收養了一個女兒帕蒂。有些文章把史蒂夫這段被領養的經歷描繪為“被拋棄”,認為這段經歷是他暴躁易怒的行為的誘因,特別是在他職業生涯早期所表現出來的那些行為。但史蒂夫反復告訴我,保羅和克拉拉非常愛他, 也很寵他。史蒂夫的遺孀勞倫·鮑威爾·喬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說:“他覺得自己非常幸運能擁有這樣的父母。”
保羅和克拉拉都沒上過大學,但他們向席貝爾承諾,一定會讓史蒂夫上大學。對于中產階級下層家庭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鄭重的承諾,也開啟了他們對史蒂夫有求必應的模式,無論史蒂夫需要什么,他們都會盡力滿足他們唯一的兒子。史蒂夫很聰明,他從五年級直接跳到了七年級,老師甚至想讓他跳兩級。跳到七年級后,史蒂夫在學業上依然毫不費力,但常常受到同學的欺負與冷落。他求父母幫他轉到更好的學校去,盡管轉學意味著要花一大筆錢,但父母還是同意了。保羅和克拉拉收拾行李搬到了洛斯阿爾托斯的一處城郊居民區,這個地方位于舊金山灣的西面小坡,原本是一片李子園,后來改建成居民區。這片住宅區位于庫比蒂諾-森尼韋爾學區內,是加州最好的學區之一。在那里,史蒂夫如魚得水。
保羅和克拉拉不僅讓史蒂夫感覺到自己是受到優待的,也培養了他追求完美的性格,特別是在手工工藝方面。保羅·喬布斯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包括回收商、機械工、汽車修理工等,他很喜歡各種手工藝,也喜歡搗鼓各種器械,周末通常會做家具或是改裝汽車,他教會兒子要沉下心關注細節。保羅并不富有,因此也會收集一些值錢的零部件。后來,史蒂夫向我展示新款iPod 或是蘋果電腦時,始終記得父親的告誡:對于一個櫥柜來說,別人看不到的底面與表面的拋光一樣重要;對于一輛雪佛蘭汽車來說, 別人看不到的剎車片和汽車的油漆一樣重要。在他講述關于父親的故事時,我能感覺到史蒂夫的多愁善感,他把自己在數字電子領域卓越的審美能力都歸功于父親的培養,盡管保羅·喬布斯可能永遠都無法理解數字電子產品。
誤解二:喬布斯驕縱自大?
可能是因為史蒂夫經常與合作伙伴發生爭執,可能是因為他總是大言不慚地把自己的主觀看法當作事實,也可能是因為在媒體面前總喜歡把功勞往自己身上攬;史蒂夫極端自我主義、不愿向他人學習的形象深入人心。但事實上,這個看法是對他的誤解,即使在他最年少狂妄的歲月里,他也不是這樣的人。
史蒂夫不僅向蘋果公司的前輩討教經驗,還會從其他渠道尋求幫助。他還不具備管理公司的能力,因此很欽佩那些企業家,總會竭盡全力與他們會面、向他們學習。“沒有一個企業家是為了錢,”他告訴我,“戴維·帕卡德(Dave Packard,惠普聯合創始人)把所有的錢都捐給了基金會。他去世的時候,本可以是墓地里最有錢的人,但他不是為了錢。鮑勃·諾伊斯(Bob Noyce,英特爾聯合創始人)同樣如此。我的年齡已經足夠大了,應該主動去結識那些企業家。我21 歲的時候認識了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1987~1998 年擔任英特爾CEO),我給他打電話,對他運營公司的才能表達了仰慕之情,問他是否可以和我共進午餐。我又如法炮制,認識了杰瑞·桑德斯(Jerry Sanders,美國超微半導體公司創始人)、查理·史波克(Charlie Sporck,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創始人)和許多其他企業家。這些人都是企業的奠基人和建造者,他們身上具備了硅谷特有的敏銳的商業嗅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文節選自中信出版社《成為喬布斯》一書,2016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