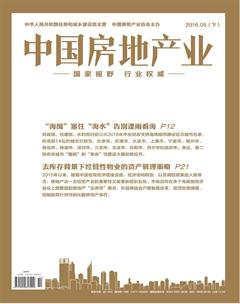胸懷丘壑 情連古今



1、1978年,您入文化部中國畫創作組,當時中國畫名家薈萃一堂,有黃胄、李苦禪、陸儼少、何海霞等先生,您對哪一位印象最為深刻,又受何啟發?
1978年撥亂反正,浩劫之余,剩下的一些老畫家就成了寶貝。當時,我們國家跟許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在駐各國的大使館中需要展示有中國特色的藝術品。文化部就召集一些老畫家,集合在北京友誼賓館進行創作。當時很多老畫家已經接近風燭殘年,身體都不太好了。組織這個事情的人是中央美院附中的老校長丁井文,他跟齊白石等一批老畫家都很熟悉。當時丁校長在擬定人員名單,聽人介紹并看到我的畫之后就把我找去,直接留在了中國畫創作組。那時候,我還在一個縣級市的文化館。進了這個組之后,就開始接觸了這些老畫家,看可染先生給外交部畫井岡山大畫。能看到可染先生畫那么大畫的恐怕也沒幾個人,因為先生畫畫不喜歡別人打攪。
當時像苦老(李苦禪)、何老(何海霞)等老藝術家對年輕畫家都是循循善誘。何老是長安畫派的中堅人物,那時我跟他住在一個套間里,可以說朝夕相對,所以聆聽他的教誨比較多。何老強調中國畫不論鑒賞還是創作,應該就講四個字“筆精墨妙”,即筆法精到,墨法奇妙。他最早是大風堂的傳人,在他很年輕的時候就拜到了張大千的門下。大千先生對他耳提面命,臨習宋元,傳統根基扎實。他跟我說年輕人要多下功夫,吃透宋元繪畫藝術。現在回頭看看,感覺確實大有深意。所謂文脈和技法的傳承,都是有源有流。某一個時候的源發展成下一個地方的流。下一個流鋪開太大了,往往被攤薄,稀釋,這個時候還得回到源頭上來,疏浚河道,才能出現新的流。
我覺得古人有兩句詩可以做山水畫的規則。一個是石濤說的“搜盡奇峰打草稿”,意識是行遍天下,縱覽山川,使之內營于心;還有一句是杜甫的“轉益多師是我師”,也就是說在技法上,要向古人多學習。請益的師傅越多,那你的本事也就越大。這兩個,還是師造化、師古人,畫家自己的境界決定山水的境界,一定要有一個丘壑內營的過程。
2、請劉老師談談您對中國文化與書畫的認識?
文化其實不是簡單的那點字句,而是字句里面貫穿流淌著的一種精神,這個精神滋養了一代又一代人。比如說,一談到民族氣節,我們就會想到文天祥,想起《正氣歌》;談到抵御外侮,就會想到岳飛,想起《滿江紅》。這些已經完全是超越表象的東西了,變成一種真正內在的有血有肉的可以充當民族脊梁的東西。它會有一個實指性,就是說它在傳承過程中不像水流那樣,勻速的,好像是無止的。它更像珠串那樣顆粒狀的珠圓玉潤,但是一脈相承,必須理解到這樣,才能增加文化傳承的自覺性。在文化的傳承當中,特別是像書畫這一類最具視覺因素。書畫藝術發祥既早,歷代也比較輝煌,即使是少數民族統治期間,統治者也在努力學習漢文化。
書畫在古代不只是作為一些藝術上的追求,它在文人的筆墨生涯里實際是抒情消遣,體現性靈。作品出來主要是博會心者一笑,不是為了市場價值,也沒有想著拿這個來傳世。對這些文人來說,詩書畫包括篆刻都是小道,但是小道也可以載道。“載道”這個詞是貫穿于中國文化一切活動核心的一個詞。文人尤其是用來載道的,藝術上的探索創作是載道的,自己的言行無不要求載道,最終還是要歸載到大道上的。中國文化的核心是非常理性的,關乎自然、與人性的。中華民族之所以有凝聚力,不是因為武力,也不是因為地緣,而是因為文化。
3、人們說書畫有好多境界,如景物之境、筆墨之境、人文之境。您也曾說,書畫最高境界在于精神意境。我覺得這跟人文之境也是不約而同的。您覺得要達到這種境界應做何努力呢?
關于這個三境界說,我覺得還是不夠準確。繪畫應該先有形似,無論你是畫花鳥、動物、山水、人,首先都要在這個形上找東西。第一個境界就是“形似”,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是境界是“神似”,在表面的東西里找內在的特質。第三就是“意韻”,神還是附著于某一個形上。從形神這兩個方面再把它抽離出來,造成一個畫家獨有的意境,在風格上突出獨有的韻致。我覺得這三個境界可能更恰當一些。
古人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都是說必要的歷練。但并不是說,這么做了,就能達到我們要求的那個高度,還是在內心要有一個真正的修煉。關于內在的修煉,儒家講日三省吾身,養浩然之氣。一個是反躬自省,一個是克制自己的貪念,這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
作為畫家要心懷古今,有很強的歷史感,然后在現實的當下,有比較強的博愛精神。有了這種精神,你去畫花鳥,你的感情就能深入到一枝一葉,一鵲一兔,就像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言:“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這樣放大的感情會更加飽滿和充沛,才更容易感染別人。
4、您覺得近百年來中國畫的發展軌跡是怎樣的?
1840年以后,中國畫面臨著社會形態的轉變,買家和欣賞習慣都有所不同,這在上海和廣州尤為突出。北京比較傳統,滿清官僚仍居統治地位,文人士夫以能和這些人交往為榮,文人墨客也都立志于加入這個圈子。
當時的上海已經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縣城,發展成為英日法等國的租借地。資本家在黃浦江邊開辟了大片的土地,建起了高樓大廈,稱為“十里洋場”。在那里有治外法權,有洋人的《字西林報》,華人的《申報》等等,人們享有一定的言論自由,商業氣息濃厚,整個滿清統治已經完全癱瘓,大家不再追求官本位,而是熱衷于學習西方語言和文化。就是在這樣一個氛圍下產生了海上畫派,像任伯年、虛谷及后來的吳昌碩都是海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海派是當時最活躍和成就最高的畫派,其繪畫行情很好。以任伯年為例,每年書畫收入不僅可以滿足其子科舉仕途之路,也能使自己生活寬裕。許多廣州商人到上海開店,店鋪里都想懸掛任伯年的畫。海派畫風受到西方繪畫的影響,像任伯年的畫,有點西洋水彩的味道,從花卉的寫生能看出西洋或東洋的那種神韻來。
不能不說起海上畫派最后的大家吳昌碩,他是劃時代的畫家,他見證了滿清末年到民國的初年的風風雨雨。他更是把書和畫結合起來,筆致從寫獵碣碑到把任伯年花卉畫法寫意化,然后發展成為獨具風格的紅花墨葉。當時這一風格非常受日本人推崇,凡是來中國的日本人必到上海求吳昌碩的作品。從這些年拍賣就可看出,日本回流的吳昌碩作品不在少數。
中國畫的發可以大致上可分上古,中古,近古以及近代。上古書畫同源,從甲骨文即可看出,繪畫近乎圖案,中古繪畫已脫離工藝和實用,線條(即筆)色彩并用,發展出工整謹嚴的工筆畫風,如顧愷之、閻立本、李昭道的作品。在中古的下半期,從唐王維開始,創作了一種不假丹青,純用水墨的畫法,可謂文人畫始祖,之后宋蘇軾、文仝、梁楷、石恪等繼承和發展了這一路畫風,文人畫始大興,自元四家更為彪炳一代。明以后的脈絡就寫意而言是青藤白陽,之后發展到八大石濤,入清后發展到八怪,進而是海上畫派。海上畫派之后是吳昌碩,他的紅花墨葉直接影響到齊白石。齊白石未定居北京之前,畫風比較冷逸,不受北京人喜歡。在陳師曾的建議下開始研究吳昌碩的畫,自創新風。所以,從花鳥來講這個脈絡就很清楚,也就是正脈。所謂“正脈“是指果實碩大,旁枝眾多,其影響范圍從長江過黃河到北京,遍布了半個中國。在那時京派很多畫家都受到齊白石的影響,甚至王雪濤的小寫意也是如此。
文人畫的發展以八大石濤作為一個高峰,其格調秀逸,冷峻,而繼之以起的吳昌碩畫風為之一變,雅健雄深,潑辣,酣暢。而恰恰這樣的對比和差異才使中國畫文人大寫意的傳承,落到了吳昌碩的肩上。他書畫合一的精髓、詩書畫三絕的特性傳承到齊白石。齊白石的草蟲、魚蝦、寫生的農具都是前人所沒有的。然后再到苦老,這都是吳昌碩,齊白石,一脈傳下來的,應該說從富麗堂皇到筆墨齊整,再到筆墨消散,到筆墨簡練概括,是這么一路過來的。當然這些東西可能有周期,但是我們還沒有看到下一個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