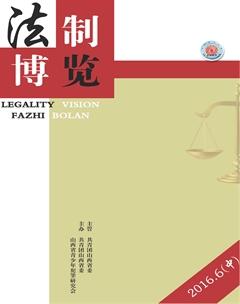論虐待型犯罪的主體范圍的擴大問題
張鑫
摘要:《刑法修正案(九)》將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的行為單獨立罪,將虐待型犯罪的主體范圍擴展至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是對于虐待型犯罪主體范圍的一次重大突破,但是對于實際生活中存在的雇主虐待保姆,大學生虐待舍友等具有嚴重法益侵害性的惡性虐待案件仍然不能得到恰當的刑法評價。本文擬通過案例分析、法理分析,深入探討虐待型犯罪主體的定位問題,并對虐待型犯罪的主體范圍的進一步完善提出建議。
關鍵詞:虐待型犯罪;主體范圍;立法建議
中圖分類號:D924.3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6)17-0031-03
近年來,虐待兒童、虐待老人等惡性的虐童事件頻頻曝光,虐待行為的主體由單一的家庭成員擴展至有看護關系的老師、護工等人群,關于這種行為的定性問題引發了社會各界激烈的討論。但是,《刑法》第260條規定的“虐待家庭成員”的單一處罰類型無疑不能很好地應對這一新情況,為此,《刑法修正案(九)》在虐待型犯罪的規定上做出了一定的補充,對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的行為單獨設立罪名,增設了“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這一新罪,但其是否能夠適當解決現實中的惡性虐待問題,還需要我們進一步的思考。一、虐待型犯罪的主體范圍的立法概況
虐待,從刑法學上講,虐待行為的內容必須表現為進行肉體上的摧殘與精神上的折磨[1]。從這一意義上看,虐待行為的實施主體并沒有限制,但基于刑法的謙抑性,我國刑法對虐待行為的處罰進行了一定的限制,最為突出的限制之一便是在虐待行為的主體上。
虐待型犯罪在刑法上主要是“虐待罪”和“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兩個罪名。虐待罪的最早規定見于我國79年刑法,在“妨礙婚姻家庭罪”一章中,將虐待罪的主體限定于“家庭成員”之間,該罪的價值取向也更多的側重于保護婚姻家庭關系的穩定。而后,在1997年對刑法進行修訂時,對于虐待罪的規定進行了變更,主要體現在,97刑法刪去了“妨礙婚姻家庭罪”一章,將虐待罪移至“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一章中。但是,總體來看,97刑法對于虐待罪的整體規定并未進行大幅度修改,基本保留了79刑法中的規定,仍將虐待罪的主體定位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其主體范圍并無任何實質性突破。歷經近二十年的變化,特別是近幾年頻頻曝光幼師虐待兒童、護工虐待老人等惡性事件,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熱議,對《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的適用也提出了新的挑戰。在新修訂的《刑法修正案(九)》中,虐待型犯罪的罪名規定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刑法修正案(九)》增設了兩條關于虐待型犯罪的規定,新增的第二百六十條之一即規定了“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通過這一新罪,對虐待型犯罪的主體范圍做出了重大的突破。一方面,將虐待型犯罪的主體擴展至負有監護、看護義務的職責的個人,另一方面,將虐待型犯罪的主體由個人擴展至單位,使虐待型犯罪成為單位犯罪的一種。這一規定,無疑對于解決當下存在的各類虐待兒童、虐待老人、虐待未成年人案件有著重大的積極作用。但是,目前刑法關于虐待型犯罪的主體范圍規定仍存在著不足之處,對于現實中存在的部分惡性虐待事件仍然顯得力不從心。二、從案例看虐待型犯罪的主體范圍的缺陷(一)共同居住的非家庭成員的虐待行為不能入罪
1.雇主虐待保姆案——特定身份關系下的虐待問題
現實生活中,除現行刑法規定的虐待情形以外,還存在其他類型的惡性虐待問題,雇主虐待保姆便是一種典型的惡性虐待形態。例如新聞上曾經報道過的“43歲保姆被雇主虐待9個月,精神恍惚傷痕累累”的事件。43歲的陳姐被其雇主招募后,雇主便沒收了陳姐的手機、身份證,威脅恐嚇陳姐,而且一直不付工資。陳姐每天工作近20小時,完全喪失了與外界聯系的機會。[2]因為本案中雇主的行為涉嫌非法拘禁等其他犯罪行為,已依其他罪名被追究刑事責任。但是依照非法拘禁等其他罪名追責存在著很大的缺陷,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等罪名只能評價某一次犯罪行為,而無法全面地對雇主長期、經常的虐待行為完整作出評價,另一方面,如果雇主對其雇傭的保姆并未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等其他犯罪行為,僅是對其經常性、長期性的進行肉體上與精神上的摧殘、折磨,其傷害程度并未構成故意傷害罪的程度,則雇主實施的虐待行為則不能得到刑法的評價。
縱觀實際生活中,類似雇主與共同生活的保姆的,還有師傅與共同生活的學徒等,他們均屬于特定人身關系下形成的一種狀態,都具有共同生活的特點,同樣會存在一方對另一方,肉體與精神上的摧殘與折磨的行為,在這些特殊密切關系人之間發生的虐待行為侵害了刑法所保護的法益,嚴重損害了受害人的身心健康,是對受害人健康法益的侵害,如果放任不管將使刑法的保障作用無法體現,挑戰著刑法的威嚴。[3]但是,由于虐待型犯罪的主體范圍規定的限制性,這些行為并不能夠得到有效的刑法規制,對于特定人身關系下弱勢群體權益的保護明顯存在不足,暴露出虐待型犯罪的主體范圍的缺陷所在。
2.大學生虐待舍友案——普通個體之間的虐待問題
經媒體曝光的“陜西16歲男生遭舍友襪子塞嘴脫褲虐打,煙頭燙掌心”一事是大學生虐待舍友事件中的一起典型事件。小軍(化名)因為報到當天下午被舍友懷疑拿了舍友的手機和50元錢,從報到當晚開始,其舍友就開始經常性地對其進行毆打、用煙頭燙等虐待行為,并威脅其不許告訴老師和家長。后來,由于班主任老師發現小軍的異常,經醫院檢查發現小軍的左腳腕粉碎性骨折,系由于其舍友共6人對其進行抽打等行為所導致,警方已經在立案調查。[4]本案中,因小軍的傷害程度已經達到故意傷害罪的入罪程度,其舍友的行為目前可以故意傷害罪來進行追究其刑事責任,但故意傷害罪僅針對其造成目前重傷結果的這一次傷害行為進行刑法評價,而無法對其舍友在小軍入學至案發時間段內遭受的經常性傷害進行刑法評價,但實際上,舍友們對小軍從入學至案發時間段內進行的經常性虐待行為,已經對小軍肉體和精神造成了嚴重損害,對小軍的合法權益造成了嚴重的侵害。
從這起案例中,可以看出,除去具有雇傭等特定人身關系而共同生活的主體之間的虐待行為,在共同生活的普通個體之間同樣可能存在虐待行為,并且該行為同樣具有嚴重的法益侵害性,但并不能得到刑法的恰當評價。在現實生活中,非家庭成員之間的虐待現象時有發生,但由于刑法關于虐待罪犯罪主體僅限于家庭成員,故意傷害罪須以造成他人輕傷以上后果方可立案,對上述虐待行為如何規制成為了實務難題。[5](二)反向虐待問題不能入罪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虐待被監管、看護人的犯罪形態,但這一規定具有明顯的方向性,該罪的表現為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虐待被監護、看護的人,但是不得不考慮,現實中是否存在反向虐待的可能性呢?比如某慢性病人甲雇傭乙作長期康復理療,期間對乙實施虐待,情節惡劣的,也不能適用《草案》第18條之規定((現已為正式的《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九條)。[6]反向虐待行為與普通的常見虐待行為的法益侵害性并無相差,但是反向虐待行為并不能得到現行刑法的評價,它的存在會使虐待被監管、看護人罪的適用遇到瓶頸,同時也凸顯了目前刑法對于虐待型犯罪主體范圍規定的缺陷。三、虐待型犯罪的主體范圍擴大的法理分析(一)法益侵害性分析
自1997年刑法修訂以來,虐待罪已經被歸入“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一章,《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作為刑法第二百六十條之一,同樣也被歸入“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一章,因此根據刑法類罪名與具體罪名的關系,虐待罪所侵犯的法益應當是他人的人身權,而人身權的保護并不應該因為行為實施主體的不同而差別對待,不應該仍然限于婚姻家庭等特定的身份。同時,刑法具有法益保護的機能,指刑法具有保護法益不受犯罪侵害與威脅的機能。[7]對于嚴重侵犯法益的行為,刑法就需要發揮它的行為規制機能,從而達到保護法益的效果。從這一意義上講,虐待家庭成員、虐待被監護、看護人與虐待共同生活的雇員或共同生活的其他主體之間的法益侵害時相當的,行為人的虐待行為對受虐人的身體和精神都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同時也危害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這種共同生活的普通主體之間的虐待行為已經符合刑法規制的條件,需要我們完善虐待型犯罪的主體,從而達到保護受虐人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穩定的效果。(二)與其他罪名的銜接角度
體系解釋是刑法解釋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方法。刑法的體系解釋要求我們在看待單個罪名的同時,必須要考慮到該罪名與其他罪名的關系,考慮到整個刑法體系的完整性。以國外的立法經驗為例,虐待行為主要通過“虐待罪”來規制。縱觀國際上關于虐待罪主體的立法,除越南等少數國家的刑法典將虐待罪的主體范圍限定為“家庭成員”外,大部分國家規定的虐待罪主體范圍都比我國規定得寬泛,并主要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沒有在刑法典中對虐待罪的主體范圍作出任何限定,如《俄羅斯聯邦刑事法典》和《菲律賓刑法典》。第二種情況是雖將虐待罪的主體限定在一定范圍內,但其范圍比較廣泛,并不限于“家庭成員”。[8]而且,對于普通人之間的虐待行為,一般由刑法的其他罪名進行規定,從而與虐待罪一起,共同構成了規制虐待行為的完整的犯罪圈。如《德國刑法典》第225條規定:“對下列不滿18周歲之人或者因殘疾、疾病而無防衛能力之人實施虐待行為以致損害被害人健康的構成虐待被保護人罪:1.受其照料或保護之人;2.其家庭成員;3.受其照料之權利人;4.職務或工作關系范圍內的下屬。”[9]這一規定是德國刑法中的“虐待被保護人罪”,其范圍并不限于家庭成員,但是限于有照顧或職務等特定關系的主體。但是,《德國刑法典》第223條規定:“從身體上虐待他人或損害其健康的”,是故意傷害罪。[10]由此可以看出,德國刑法上的虐待被保護人罪的主體范圍與故意傷害罪的主體范圍構成了無縫銜接,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犯罪圈。
而我國關于虐待型犯罪的現行規定,主體限于家庭成員和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對于共同生活一般主體之間的虐待行為不能依照現有的虐待型犯罪的罪名來進行刑法評價。同時,刑法中的其他罪名也無法對共同生活的一般主體之間虐待行為進行適當評價。例如,故意傷害罪一方面只能針對傷害達到輕傷以上的虐待行為,并且只能針對個別行為進行分別評價。尋釁滋事罪,作為妨礙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的一種,其侵犯的法益為公共秩序與社會秩序,且其同樣不能涵蓋施虐者對受虐者實施的精神折磨的行為。除此之外,侮辱罪同樣不能全面恰當地施虐人長期的虐待行為,而且因為其也是告訴才處理的罪名,仍然不能很好地保護受虐人的合法權益。因此,我國的現行刑法在虐待型犯罪的罪名與其他罪名的銜接上明顯存在缺陷,不能恰當地對共同生活的一般主體之間虐待行為這一嚴重侵犯法益的行為進行刑法評價,需要進一步的完善。四、虐待型犯罪的主體范圍擴大的立法建議(一)將“家庭成員”確定為量刑身份
根據犯罪主體的身份對刑事責任影響性質和方式的不同,刑法上的身份可以分為定罪身份和量刑身份。本文認為,家庭成員應當作為虐待型犯罪的量刑身份,而非定罪身份。79刑法和97刑法都將虐待罪限定于家庭成員之間,刑法界的通說也認為虐待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即他人的人身權益和正常的婚姻家庭秩序,不可否認,虐待行為這種發生一般發生封閉生活環境下的犯罪行為最普遍和常見的便是家庭生活中,其對婚姻家庭關系的影響必然不容小覷。國家在刑事立法上必須重視家庭的角色與功能,涉及到家庭成員之間的侵犯時,刑法要更加注意恢復已遭破壞的家庭秩序。[11]因此,將家庭成員作為量刑身份,在量刑上予以考慮婚姻家庭秩序,在法定刑的確定上,較普通人之間的法定刑確定的較低,從而使虐待型犯罪的規定更為人性化,更具合理性,達到保護他人合法權益和維護婚姻家庭秩序的雙贏效果。(二)將虐待罪的主體擴大為共同生活的個人
貝卡利亞說過,家庭精神是一種拘泥小事的瑣碎精神,而共和國的調整精神,作為基本原則的控制者;則看到這些小事,并把它們聚合在關系著大部分人幸福的基本類別之中。[12]根據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虐待行為并不僅存在于家庭成員、監護、看護人與被監護、看護人中,它同樣存在于共同生活的其他主體之間,并且發生在共同生活的其他主體之間的虐待行為對他人的人身權法益的侵害性同樣達到了嚴重的程度,需要刑法的規制。因此,要想更好地解決現有的虐待型犯罪的罪名在現實適用中的困境,就必然要對其進行進一步的修改,不應將處罰的對象僅限于家庭成員之間、監護、看護人與被監護、看護人之間,而應當將虐待型犯罪的主體定位于共同生活的一般主體。
故本文主張,通過修改刑法第二百六十條關于“虐待罪”的規定,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條基礎上增加一款關于“虐待共同生活的非家庭成員”的情形,將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的犯罪形態也納入其中,同時,將其法定刑設定高于“虐待家庭成員”,從而通過“虐待罪”一罪來規制虐待行為,將虐待行為進行全面恰當的刑法評價。[參考文獻]
[1]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第4版),2011:818.
[2]王雅.43歲保姆被雇主虐待9個月精神恍惚傷痕累累.[EB/OL].搜狐新聞.http://news.sohu.com/20150507/n412584575.shtml.
[3]謝敬蘭.論虐待罪的立法完善[D].昆明理工大學,2014:33.
[4]譚文婷.16歲男生遭舍友虐打 被用煙頭燙掌心.[EB/OL].西部網.http://news.cnwest.com/content/2013-09/29/content_10110512.htm.
[5]唐英.虐待罪的犯罪主體應適當擴大[N].江蘇法制報,2013-11-20(3).
[6]師曉東.身份犯視角下虐待罪的局限及其破除——兼評<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十八條之規定[J].山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5.7.(3):41.
[7]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第4版),2011:25.
[8]徐文文,趙秉志.關于虐待罪立法完善問題的研討——兼論虐童行為的犯罪化[J].法治研究,2013(3):104.
[9]徐久生,莊敬華譯.德國刑法典[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166.
[10]師曉東.身份犯視角下虐待罪的局限及其破除——兼評<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十八條之規定[J].山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5,7(3):41.
[11]沈瑋瑋,趙曉耕.家國視野下的唐律親親原則與當代刑法——從虐待罪切入[J].當代法學,2011(3):37.
[12][意]貝卡利亞.黃風譯.論犯罪與刑罰[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120.立項課題法制博覽LEGALITY VISION2016·06(中)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