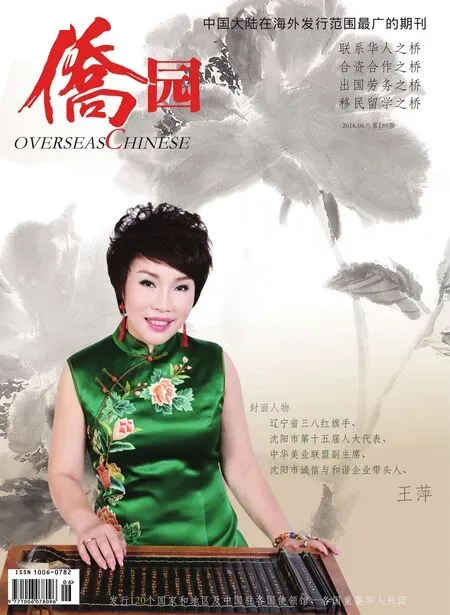圣地神居:解讀積石冢
文 穆重懷 (遼寧大學中俄文化比較研究中心)
圣地神居:解讀積石冢
文穆重懷(遼寧大學中俄文化比較研究中心)

積石冢與祭壇
無論是東山嘴 還是牛河梁 遼寧和內蒙古境內的紅山文化遺址都鮮明地表現出了與眾不同的史前文化特征 那就是充分印證了神權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中 人對自我和世界的認知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經歷了漫長的思維過程。出于原始思維 先民們對自然界充滿了奇幻瑰麗的想象 并從自身出發去考量自己身邊的一切。萬物有靈成為原始思維中最重要的思想組成 最終導致了原始宗教的產生。由于傳承有序 遼海地域的紅山文化遺址忠實地記錄了初民們的原始宗教形態的發展歷程 它的外在表現就是在各個遺址發現的積石冢 以及與積石冢相融合的祭壇和神廟。三者的結合為我們揭示了原始初民們的思維特點和心理表征 具有世界性的意義。
正如林惠祥先生指出的那樣 人類文化的根源在于人類的心靈。而原始初民的心靈體現在他們的宗教信仰上。眾所周知 人類原始宗教的發展經歷了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三個階段。從東山嘴和牛河梁的紅山文化遺址我們可以看到 紅山文化積石冢建筑群恰恰驗證了這一演進歷程 每一個發展階段都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記。以積石冢為核心的祭祀區和陵墓區體現了紅山文化先民對自然、對自身認知的思維歷程 具有獨特的人類學標本價值 這是我們今天亟待開發和考證的。從環境看 牛河梁遺址所在的地域與以往發現的紅山文化居址存在著極大的不同 并不符合史前人類選擇居住地的條件。牛河梁山梁縱橫 長達10余千米。梁的兩側多是高山 諸多山梁的高差不大 但在梁脊處多有山崗 山崗之間距離不遠 高度也相近 往往可以對望 這就為建筑完整的陵墓-祭祀區域提供了便利的自然條件。并且牛河梁地區自古以來就是華北平原經燕山到達東北的交通要道。這樣的自然環境為紅山先民開展自己的宗教活動創造了天然的條件。由此可見 先民們在最初的選址過程中就已經決定了牛河梁遺址群的性質和功能 陵墓-祭祀區的出現是先民們經過考察而有意為之的結果。
在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中數量最多的就是積石冢。在目前已知的16個地點中 積石冢就占了11處。這些積石冢之間既有共性 也有個性 但共性大于個性 存在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建筑時代先后的表現。縱觀這11處積石冢和它們的附屬建筑就可以發現它們的共同特征都是建筑在牛河梁各山梁梁脊的山崗上 并且這些山崗的海拔高度彼此相差不多 相互距離也相差不大 特別是視野都相對開闊。與主梁梁頂的女神廟的相對距離也是組組相分由內而外 基本相等。從現在掌握的材料看 牛河梁地區曾為紅山文化先人居住的生活區 但自開始作為陵墓區以后就鮮有人類生活的跡象了。也就是說 牛河梁地區已經變為集神權與王權于一身的大巫或是部落首領專用的墓地和祭祀場所 被賦予了神圣的地位。

陶制筒形器
此外 積石冢和冢壇組合的位置關系也應該置放于我們考察的視野之內。牛河梁的梁脊走向是南北方向 梁脊從南到北由高到低。由此沿著牛河梁梁脊走向形成了一條南偏西20°的斜向軸線。眾多的積石冢和冢壇組合都位于這一軸線上 或是距離軸線兩側不遠。而且每個積石冢的朝向也都是符合一定的方位要求的 基本都為正東西或正南北方向。雖然有時上下層積石冢的墓葬方向有所不同 但也都是朝向正方位 非東即南 都是朝陽的方向。這本身就說明了在冢廟壇的建筑過程中就已經進行了整體規劃 而且在方位的選擇上遵循著一定的規律。
積石冢的修建一般是先筑墓 然后再在墓上建筑冢臺 封土置于墓和冢臺之上 在封土上再進行積石。在四周用石塊砌出冢界 最后堆積出冢體。積石冢冢體的形狀多樣 有長方形、正方形、圓形以及圓形和方形的多方結合。盡管形狀不同 但是建筑過程中還是遵循十分嚴格的建筑標準的。圓形冢幾乎都是正圓形或是十分接近正圓形 方形冢幾乎都是標準的長方形和正方形 這不僅表明了紅山文化的初民們已經掌握了相當精確的方圓概念 而且也體現了先民們對宇宙構成模型的基本認識。
積石冢往往是一冢多墓 但無論墓的大小均為砌石墓。它包括土壙墓穴和地上筑墓。墓穴多鑿入風化基巖層 使用石砌的墓室 在一些文章中將其稱為石棺 。墓室四壁用板狀石塊或是石板平鋪 一般為7—8層 最多達12層 疊摞緊密 直到今天還依然整齊。地上筑墓也同樣采取石板立置和石塊平砌的方法砌出墓室。兩者的差別在于陪葬玉器種類和質量的不同 以及數量的多寡 但都用石料做墓室是它們的共同特征。所用石料為灰白色板狀灰巖。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提醒我們 在紅山文化的葬俗中用石所具有的獨特含義。
從紅山文化積石冢的所在位置和具體形制看 我們認為牛河梁與東山嘴遺址都是紅山文化先人祭天的所在。積石冢建造在高崗之上本身就符合古人祭天的禮制。在《禮記·祭法》中有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上古時代先人們為了縮短與天的距離 往往試圖到與天最近的地方去祭天 因此在原始初民的思維中山就成為溝通天人的重要媒介。這也是后世君主要到泰山去舉行封禪大禮的原因之一。這里說的泰壇也就是所謂的圜丘 其本意是取法天圓地方。這與牛河梁與東山嘴的紅山文化遺址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把去世的兼有神權和王權的部落首領安葬在高山之上本身就是為他 她 們建立了一條通往天國的神秘捷徑。
考察東山嘴與牛河梁的紅山文化遺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紅山文化先民對石的崇拜 熟悉紅山文化器物的人常說 紅山文化是惟玉為葬。需要指出的是 玉本身也是石的一種 。從積石冢到祭坑的設計無一不突出石在宗教文化中的作用。我們認為 這種石崇拜是與對天的崇拜 也就是太陽神的崇拜聯系在一起的。
如果說在山崗上建冢壇廟是與祭天有關 那么冢壇廟的方位也與太陽運行的方位相關。古人祭天的時候一般是東向或南向 牛河梁遺址的整體規劃是與太陽的周視運動相一致的 也就是說它的選址和建設是與祭日儀式有著緊密聯系的。在其周圍的東北-西南走向的山梁上的積石冢同樣也具有這樣的文化內涵。而且建設冢壇的石料的顏色 白色和紅色 也代表著太陽的顏色。但是應該指出的是 在紅山文化的東山嘴和牛河梁時期太陽神已經不是自然神 而是具有人格神的特征。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 諸多積石冢中都有中心墓。中心墓的規格和陪葬品都要高于在同一冢群中的其他墓葬 而且陪葬的玉器也都具有典型性。我們推測 這些中心墓的墓主在當時都是掌握一定權力的氏族首領 還極有可能兼有祭司的職能。他她 們是太陽神在人間的代表 在他她 們去世以后還是要回到太陽神那里去。這也就是在后世的商代甲骨中所說的“賓于帝”的先聲。但是紅山文化的宗教形態遠沒有商代的成熟 而是處于一種過渡的狀態 從女神廟的發現來看就證明了這一點 這是一個由多神崇拜向一元神過渡的時期 但人格神已經走上了神壇 并將取得最后的勝利。
把紅山文化的石崇拜和太陽崇拜聯系在一起 主要的依據是在中華文化中石與天的關系。《淮南子》中女媧補天的神話就清楚地指出了女媧是煉石補天 “于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 天是用石建造的。這恐怕與天降隕石留給初民的印象有關 而且女媧時代的大洪水說不定就是小行星撞地球所引發的。因此我們認為 積石冢與祭壇大量使用石料可能與對太陽的崇拜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樣積石冢和祭壇選用石料的顏色也可以對此進行佐證。
積石冢冢體的石塊堆積似乎沒有固定的規律 只是簡單的堆砌。冢的四周筑有冢墻 利用加工過的平整石料 采用三七錯縫法砌筑 一般為三層 由內向外層層疊加 至上口取平 所使用的石料為灰白色燧石條帶狀白云質灰巖。白色是太陽的象征 這是為人們所公認的。
在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中與積石冢組合出現的是祭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位于第二地點的圜丘形祭壇。這個祭壇是石砌的三重圓臺 由外到內直徑分別為22米、15.6米和11米。三重圓臺層層高起由外向內以0.3至0.5米的高差形成三層臺面 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圓形壇體 開創了中國古代建筑采用三臺的先河。馮時先生認為 這個祭壇是中國古老的蓋天理論的現實實踐 不僅描述了一整套的宇宙理論 同時也準確地表現了分至日的晝夜關系。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祭壇同祭日儀式之間的關系。我們還需要加以注意的是用來修建祭壇的石料。它沒有采用通常建筑積石冢所用的白色硅質石灰巖 而是采用了淡紅色的安山巖石塊。石塊為不規則的五棱狀柱體 石柱截斷而成樁 并排立置 規格從外到內逐漸變小 外圍石樁最大 內圈石樁最小 排列規則、整齊。祭壇內圈分布有夾脈石英的花崗巖自然石塊 厚度0.2至0.6米。在東北一側還可以辨認出弧形擺放的石塊 這可能是壇體第三層臺面的構成部分。由此可以推測 壇頂堆石原來可能是一個圓形臺面。此外在臺面與內圈石樁之間還應有一圈紅色的陶筒形器。這種陶筒形器同積石冢上的一樣 同樣是上下貫通 沒有底部。在祭壇上還發現了陶制塔形器的碎片。根據這些發現 我們可以推定 這個祭壇的功能就是用來祭祀太陽神和它在人間的代表的。因為紅色的內外圈和白色的臺頂都與太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而且上下通透的陶制筒形器本身也有通天達地的功能 這些都為太陽神祭祀的認定提供了現實依據。特別是陶制塔形器的發現進一步明確了紅山文化中太陽神所具有的豐產之神和生殖之神的神格特征。
在積石冢的石砌臺階內側還有成排的筒形陶器 數量巨大。這種筒形陶器為泥質紅陶 壁厚 多在口下飾玄狀紋 外表繪黑彩 花紋多樣。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底部 而且底緣一般都經過加工。這種筒形陶器是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獨見的陶器。它所在的位置和形狀都難以為它的功能和性質找到合理的解釋。但無疑應當與積石冢的整體功能相關 應該是整個祭祀儀式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牛河梁遺址中還有為數眾多的祭祀坑。這些祭祀坑的坑內都經過火燒 形成硬面。坑內填充白色細沙土 坑口平面呈圓形。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第五地點2號祭祀坑。這個祭祀坑坑口為圓形 直徑1米。坑壁略微向內傾斜 坑深0.6米 坑壁和坑底經過火燒呈現紅色。坑底是一層白色灰燼 厚度約為2厘米。其上為厚約13厘米的黑褐色填土層。填土層上是厚約2—5厘米的一層紅燒土。紅燒土上是厚約7厘米的白色沙土層。沙土色澤純凈 沒有雜質。在它的上面是一層厚約5—7厘米的小石粒層 石粒直徑多在1.5厘米左右 大小十分均勻 似為人工所制。石粒層上是一層棕紅色燒土層 厚度不均勻最厚處達10厘米。燒土層上又是一層厚度達20厘米的白色沙土層。沙質松軟、純凈 其間混有少量陶片。白色沙土層上面是坑的表層 也為厚度不均的燒土層。從祭祀坑的排列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中包括紅燒土、白沙土和小石粒 把這些東西作為祭祀的用品 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祭祀對象與太陽神的關系。祭祀坑被火燒烤過這本身就使人產生與太陽崇拜的聯想 因為火是與太陽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而石粒又與火有著密切的關系。史前時代鉆燧取火 火是從石塊的撞擊中產生的 原始初民自然就會以為火是生長在石頭里。由此就出現了石與火 與太陽關系的豐富想象。從這個視角看 在祭祀坑中出現有意制作的小石粒并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 而是將它們作為與太陽神溝通的媒介。
值得注意的是 在第三、第十六地點的積石冢都發現了陶塑人像殘件或殘片。在第三地點發現的是一件人面殘塊 質地為泥質紅陶 夾有少量的石英巖顆粒。正面經過抹光 并施以比較厚的而且均勻的紅陶衣。形狀為片狀 只殘留鼻、嘴和面部的右側。這個殘缺人像具有寫實的特征 從整體到細部比例勻稱 符合人體解剖學的原理。考古人員認為 “根據其面形近似方圓 顴骨不高 嘴部大小適中唇不厚 唇線圓潤 鼻部扁而寬 鼻尖不凸出等特征判斷 似屬于東亞蒙古人種為女性。”在第十六地點發現的是人上肩胳膊和陶塑人手部殘件 其中陶塑人手部殘件材質為泥質紅陶 施有紅陶衣。整體為片狀 塑出食指、中指和無名指 三指并聯 殘存部分為手指端部 指甲形狀相當寫實 大小與真人相類。同樣在東山嘴遺址也發現了陶塑人體殘件 大小約為真人的1/3左右 根據分析得出的結論也偏向于是女性塑像。由此可見 在積石冢所在地多有女性人像存在 這些女性陶像應為紅山文化先民們祭祀的偶像。從這些人像的性別和帶有紅色陶衣來看 它們應該具有史前太陽神的神格 具有保佑豐產與生殖的雙重功能。在這種情況下 積石冢也就成為具有神廟功能的祭典組合之一。可以想見 在高高的山崗上 白色的積石冢 紅色的祭壇 還有那環繞一周的紅色陶制筒形器與盤坐于其上的紅色女神像再加上獨特的紅色陶制塔形器 在五千年前的藍天驕陽之下是何等的莊嚴肅穆。
作為紅山文化重要特征的積石冢已經超出了簡單墓制的范圍 在紅山文化的宗教活動中被賦予了更為神圣的功能。它不僅是巫覡們的靈魂棲息地 而且還是溝通天地的通神之所。這些積石冢是新石器時代人類精神生活和物質生產的真實寫照。它們具有的文化價值的復雜性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和解讀 以求為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注入新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