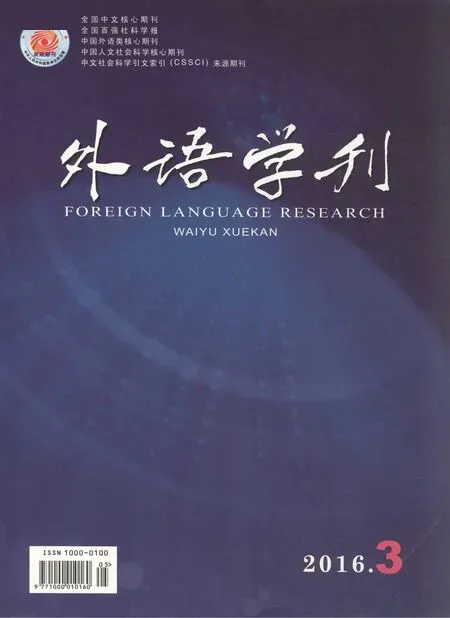社會(huì)翻譯學(xué)視閾中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傳譯的歷時(shí)詮釋*
王洪濤
(天津外國語大學(xué),天津 300204)
●文學(xué)研究
社會(huì)翻譯學(xué)視閾中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傳譯的歷時(shí)詮釋*
王洪濤
(天津外國語大學(xué),天津 300204)
本文在社會(huì)翻譯學(xué)視閾中借鑒布爾迪厄反思性社會(huì)學(xué)的“場(chǎng)域”、“慣習(xí)”和“資本”等概念與理論,將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傳譯的萌芽、肇始、興盛、沉寂、復(fù)蘇及發(fā)展6個(gè)階段還原至當(dāng)時(shí)的國際社會(huì)文化背景下,通過高度語境化和深度歷史化的方式對(duì)其進(jìn)行“關(guān)系主義”解析,以詮釋出不同階段傳譯活動(dòng)與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文化之間的共變關(guān)系,進(jìn)而揭示出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近四百年傳譯活動(dòng)的整體運(yùn)作軌跡與規(guī)律。
社會(huì)翻譯學(xué);中國文學(xué)英譯;場(chǎng)域;慣習(xí);資本
1 引言
“社會(huì)翻譯學(xué)”最初由當(dāng)代西方翻譯研究學(xué)派創(chuàng)始人霍姆斯(J. Holmes)在《翻譯學(xué)的名與實(shí)》(1972/1988)一書中提出。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隨著斯密奧尼(D. Simeoni)和赫曼斯(T. Hermans)等西方學(xué)者紛紛借鑒布爾迪厄(P. Bourdieu)的反思性社會(huì)學(xué)理論和盧曼(N. Luhmann)的社會(huì)系統(tǒng)理論等開展翻譯研究,社會(huì)翻譯學(xué)研究在翻譯學(xué)經(jīng)歷的這一“社會(huì)學(xué)轉(zhuǎn)向”中發(fā)展成為一種成熟的譯學(xué)研究范式,并初步成長為翻譯學(xué)的一個(gè)分支學(xué)科(Merkle 2008:175)。作為翻譯學(xué)一個(gè)嶄新的分支學(xué)科,社會(huì)翻譯學(xué)旨在探索社會(huì)因素及社會(huì)變量與翻譯活動(dòng)及翻譯產(chǎn)品之間雙向、互動(dòng)的共變(covariance)關(guān)系(王洪濤 2011:16)。社會(huì)翻譯學(xué)在形成過程中,吸納布爾迪厄用于消解主客二元對(duì)立的場(chǎng)域(field)①、慣習(xí)(habitus)②和資本(capital)③等反思性社會(huì)學(xué)概念與理論,借鑒其關(guān)系主義(relationalism)④方法論,因而較之以往囿于語際轉(zhuǎn)換規(guī)律的語言學(xué)研究范式和陷入“文化決定論”的文化研究范式,社會(huì)翻譯學(xué)的研究范式“從一個(gè)更接近翻譯本質(zhì)屬性的角度觀察和闡釋翻譯活動(dòng)和譯者與社會(huì)、文化、全球化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王悅晨 2011:12),進(jìn)而能夠更加客觀、深入地揭示出翻譯活動(dòng)在國際社會(huì)文化背景下從發(fā)生到發(fā)展、從傳播到接受的整體運(yùn)作軌跡、規(guī)律與邏輯。
作為東學(xué)西漸的一部分,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的傳譯活動(dòng)迄今已近四百年歷史,依據(jù)傳譯的規(guī)模、水平與整體影響,先后經(jīng)歷萌芽期、肇始期、興盛期、沉寂期、復(fù)蘇期和發(fā)展期6個(gè)階段。對(duì)于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的傳譯,國內(nèi)學(xué)者分別主要從海外漢學(xué)研究、漢籍外譯研究和比較文學(xué)中的影響研究等角度進(jìn)行考察,并探索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傳譯的基本史實(shí)、主要特征以及英國文學(xué)對(duì)于中國文學(xué)的接受等問題。然而,雖然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的傳譯主要發(fā)生在向來關(guān)注中國文化典籍的漢學(xué)場(chǎng)域中,且不少傳譯活動(dòng)的確有著很多文學(xué)性考量,但無論是從單一的海外漢學(xué)研究角度,還是純粹的漢籍外譯研究角度,亦或是傳統(tǒng)比較文學(xué)中的影響研究角度,都難以將其中的多重動(dòng)因、多種變量和多維影響考察清楚,因?yàn)橹袊膶W(xué)在英國的傳譯活動(dòng)不僅受英國以及國際漢學(xué)、文學(xué)、文化、教育乃至政治、經(jīng)濟(jì)、宗教和軍事等各個(gè)場(chǎng)域的影響并同時(shí)反作用于這些場(chǎng)域,而且受制并以某種形式反制于其中的經(jīng)濟(jì)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huì)資本,另外還與不同場(chǎng)域中具體的譯者慣習(xí)彼此關(guān)聯(lián)。
鑒于此,本文擬在社會(huì)翻譯學(xué)視閾中借鑒布爾迪厄反思性社會(huì)學(xué)的“場(chǎng)域”、“慣習(xí)”和“資本”等理論,依據(jù)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傳譯的歷史進(jìn)程,將其6個(gè)階段的傳譯活動(dòng)分別還原到當(dāng)時(shí)整個(gè)國際社會(huì)文化背景下,通過高度語境化和深度歷史化的方式解析“關(guān)系主義”,以詮釋出不同階段傳譯活動(dòng)與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文化之間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共變關(guān)系,進(jìn)而揭示出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近四百年傳譯活動(dòng)的整體運(yùn)作軌跡與規(guī)律。
2 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的傳譯:社會(huì)翻譯學(xué)視閾下的歷時(shí)詮釋
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的傳譯活動(dòng)在不同歷史階段分別呈現(xiàn)出“間接傳譯”、“直接英譯”、“系統(tǒng)英譯”、“少量英譯”、“專業(yè)英譯”和“新型傳譯”等各種形態(tài),而這些具體形態(tài)與當(dāng)時(shí)英國乃至國際社會(huì)文化語境中的“漢學(xué)場(chǎng)域”、“宗教場(chǎng)域”、“商業(yè)場(chǎng)域”和“權(quán)利場(chǎng)域”,與充斥于各種場(chǎng)域之中的“經(jīng)濟(jì)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huì)資本”,與在不同場(chǎng)域中凝塑而成的“譯者慣習(xí)”等社會(huì)文化因素構(gòu)成多維多向、彼此制約的“共變”關(guān)系。
2.1 萌芽期(17世紀(jì)初至18世紀(jì)中期):漢學(xué)場(chǎng)域空缺中的間接傳譯
縱觀東學(xué)西漸史,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的傳譯活動(dòng)既沒有規(guī)模化的譯者隊(duì)伍,也沒有專門性的組織或機(jī)構(gòu),因此難以形成獨(dú)立的場(chǎng)域。事實(shí)上,除早期來華傳教士、外交官以及一些來自其他領(lǐng)域兼職譯者的部分譯介活動(dòng)外,以大學(xué)漢學(xué)系、漢學(xué)研究院或其他相關(guān)機(jī)構(gòu)為依托的英國漢學(xué)界在其專職工作之余承擔(dān)大部分的中國文學(xué)英譯工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構(gòu)成決定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傳譯或盛或衰的“漢學(xué)場(chǎng)域”。然而,早期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的傳譯活動(dòng)卻恰恰缺少這樣一個(gè)當(dāng)時(shí)已在歐洲大陸發(fā)軔的漢學(xué)場(chǎng)域,而其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相關(guān)的宗教場(chǎng)域。
16世紀(jì)早期亨利八世發(fā)起的宗教改革,使得英國脫離羅馬天主教建立自己的國教。英國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羅馬天主教會(huì)的傳教事業(yè)之外,從而遲于意大利和法國等國家來華傳教,對(duì)于中國的了解也相對(duì)較少、較晚,所以到16世紀(jì)末17世紀(jì)初歐洲大陸漢學(xué)已經(jīng)發(fā)軔之時(shí),英國的漢學(xué)研究還處于洪荒階段。因此,對(duì)東方抱有濃厚興趣的英國只好借助歐洲其他國家來華傳教士、漢學(xué)家的有關(guān)中國的譯作、著述和記載來了解中國,而英國在17世紀(jì)初至18世紀(jì)中期對(duì)于中國文學(xué)的間接傳譯活動(dòng)也由此而來。
作為西方漢學(xué)奠基人之一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生前曾留下一部關(guān)于中國概況及其在華傳教經(jīng)歷的意大利語手稿,人稱《利瑪竇札記》。1615年,法國傳教士、漢學(xué)家金尼閣(N. Trigault)在德意志出版他用拉丁文翻譯并擴(kuò)展和潤飾的利瑪竇手稿,被稱為《基督教遠(yuǎn)征中國史》。書中涉及中國詩歌、四書五經(jīng)等中國文學(xué)概況的描述,據(jù)稱“它對(duì)歐洲文學(xué)和科學(xué)、哲學(xué)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響,可能超過任何17世紀(jì)的歷史著述”(利瑪竇 金尼閣 1983:31-32)。由于該書用歐洲知識(shí)界廣泛流行的拉丁語刊行,因此出版后廣受歡迎。1625年,在英國出現(xiàn)一個(gè)英文摘譯本,被收入《普察斯朝圣者叢書》之中(同上: 29-30)。這雖是一個(gè)簡(jiǎn)單的摘譯本,卻標(biāo)志著英國對(duì)于中國文學(xué)的譯介由此開始萌生。1735年,法國神甫杜赫德(J. Du Halde)根據(jù)來華傳教士們提供的資料編撰了一部《中華帝國全志》,其中收錄有《詩經(jīng)》數(shù)首、《古今奇觀》數(shù)篇以及法國來華傳教士、漢學(xué)家馬若瑟(J. de Premare)于1731年法譯的中國元曲《趙氏孤兒》,而英國很快就出現(xiàn)該書的兩部轉(zhuǎn)譯本:布魯克斯(R. Brookes)節(jié)譯本(1736,書名改稱《中國通史》)和凱夫(E. Cave)全譯本(1738-1744);1762年,英國又出現(xiàn)柏西(T. Percy)選輯出版的《中國雜文選編》,其中載有對(duì)凱夫譯本潤飾而成的《趙氏孤兒》新譯本(馬祖毅 任榮珍 1997:222-23)。至此,英國便擁有轉(zhuǎn)譯自法語的3個(gè)《趙氏孤兒》譯本。就這樣,由于缺少漢學(xué)場(chǎng)域及對(duì)中國文學(xué)有研究的漢學(xué)家,英國早期對(duì)于中國文學(xué)的傳譯便處于這樣一種從歐洲其他國家漢學(xué)家譯作那里間接轉(zhuǎn)譯的萌芽狀態(tài)。
2.2 肇始期(18世紀(jì)中期至19世紀(jì)初):經(jīng)濟(jì)資本刺激下的直接英譯
18世紀(jì)中期以后,英國進(jìn)入資本主義的上升時(shí)期,商品經(jīng)濟(jì)高度發(fā)展,對(duì)于經(jīng)濟(jì)資本的追逐使其迫切需要打開中國市場(chǎng)。19世紀(jì)初,英國東印度公司將鴉片銷售到中國,同時(shí)從中國進(jìn)口茶葉和絲綢,兩國之間的商業(yè)往來日益頻繁。由于中英兩國語言截然不同,英國所有對(duì)華貿(mào)易都須依靠翻譯來完成,因此“正是商業(yè)發(fā)展的需要促使英國開始關(guān)注起中國的語言和文化”(Chen, Hsiao 1967:1)。1825年,英國商人邀請(qǐng)當(dāng)時(shí)著名的漢學(xué)家馬禮遜(R. Morrison)在商業(yè)中心倫敦開設(shè)具有漢學(xué)教育前身意味的倫敦東方學(xué)院(London Oriental Institution),進(jìn)行漢語教學(xué)(同上:2)。雖然3年后這一具有英國漢學(xué)教育前身意味的機(jī)構(gòu)隨著馬禮遜動(dòng)身趕往廣東而關(guān)閉,它卻成為英國商業(yè)場(chǎng)域促進(jìn)其漢學(xué)場(chǎng)域形成的一個(gè)有趣例證。在此背景下,英國拉開中國文學(xué)直接英譯的大幕。
1761年,柏西發(fā)表英譯本《好逑傳》(HauKiouChoaan),該譯本譯自中國明末清初的長篇俠義愛情小說《俠義風(fēng)月傳》。1774年,該書再版時(shí),柏西在前言中指出譯稿出自英國商人魏金森(J. Wilkinson)之手。魏金森供職于東印度公司,曾在廣州居住多年,譯稿是他學(xué)習(xí)漢語時(shí)的翻譯練習(xí),共4冊(cè),前3冊(cè)為英文,末一冊(cè)為葡萄牙文,其漢語教師可能為葡萄牙的來華傳教士(馬祖毅 任榮珍 1997:224-225)。柏西將英譯稿進(jìn)行潤飾,同時(shí)將葡文譯稿譯成英文,于是形成英國第一部直接從漢語翻譯成英文的中國古典小說。因此,如果說利瑪竇和馬若瑟最初對(duì)于中國文學(xué)的翻譯主要出于傳教目的,那么魏金森翻譯中國古典小說的直接目的則是“將其作為學(xué)習(xí)漢語的一種練習(xí)”(St. André 2003:42),而其最終目的顯然并不僅限于此。鑒于魏金森當(dāng)時(shí)供職于東印度公司的駐華機(jī)構(gòu),沈安德(J. St.André)指出其翻譯動(dòng)機(jī)不是“單純的”,認(rèn)為其翻譯是一種帶有“東方主義”、“殖民主義”和“商業(yè)主義”性質(zhì)的行為(同上:46)。不難理解,他此處所謂“商業(yè)主義”指魏金森進(jìn)行翻譯的一個(gè)重要?jiǎng)訖C(jī)是為在商業(yè)場(chǎng)域中更好地獲取經(jīng)濟(jì)資本。
然而,這一時(shí)期英國東方學(xué)家瓊斯爵士(Sir W. Jones)對(duì)于《詩經(jīng)》片段的直接翻譯則是個(gè)例外。1770年,瓊斯爵士讀到拉丁文譯著《中國哲學(xué)家孔子》,通過《大學(xué)》部分接觸到《詩經(jīng)》片段,深受感動(dòng),于是找來巴黎皇家圖書館所藏的《詩經(jīng)》漢語原本仔細(xì)研究,然后對(duì)照著柏應(yīng)理等人的譯作將《衛(wèi)風(fēng)·淇奧》第一節(jié)重譯成拉丁文,十多年后又將其譯成英文。另外他還將《周南·桃夭》和《小雅·節(jié)南山》各一節(jié)譯成英文(張弘 1992:58-59)。馬祖毅和任榮珍指出,與耶穌會(huì)士的翻譯不同,瓊斯并沒有將《詩經(jīng)》視為“經(jīng)”,而是把它當(dāng)成文學(xué)作品意義上的“詩”來進(jìn)行翻譯(馬祖毅 任榮珍 1997:226)。誠然如此,瓊斯對(duì)于《詩經(jīng)》的英譯別具深義。
2.3 興盛期(19世紀(jì)初至20世紀(jì)初):漢學(xué)場(chǎng)域確立后的系統(tǒng)英譯
19世紀(jì)初以后,中英之間的商業(yè)往來更為頻繁,而此后爆發(fā)的兩次鴉片戰(zhàn)爭(zhēng)更是使得中國國門被迫向英國敞開,大批的英國商人和傳教士涌入中國。1854年中英正式建立外交關(guān)系以后(Chen, Hsiao 1967:3),許多英國外交官也來到中國,其中兼具學(xué)者身份的就有四十余人。由此一來,在經(jīng)濟(jì)資本和傳教事業(yè)的推動(dòng)下,尤其是在具有支配地位的國家“權(quán)利場(chǎng)域”的影響下,英國的漢學(xué)場(chǎng)域開始逐漸形成。
1837年,倫敦大學(xué)授予基德(S. Kidd)漢學(xué)教授一職,其繼任者分別為齊玉堂和霍爾特(H.F. Holt)、比爾(S. Beal)等;8年后,史丹頓又在國王學(xué)院設(shè)立漢學(xué)教席,費(fèi)爾森(J. Fearson)、薩默爾斯(J. Sammers)和道格拉斯(R. Douglas)等先后擔(dān)任該教席(同上:2-4)。1876年,牛津大學(xué)設(shè)立漢學(xué)教席,首任教授為理雅各(J. Legge)。1888年,劍橋大學(xué)也設(shè)立漢學(xué)教席,首位教授為威妥瑪(T. Wade)。1906年,英國財(cái)政部任命雷伊勛爵(L. Reay)為主席,成立一專門委員會(huì)開展調(diào)查,以提高漢學(xué)研究;經(jīng)過調(diào)查,該委員會(huì)于1909年在報(bào)告中提議倫敦大學(xué)成立東方學(xué)院(只是該學(xué)院遲至1916年成立,后改稱亞非學(xué)院)(同上:6)。至此,英國的漢學(xué)場(chǎng)域便由小到大、由點(diǎn)到面地正式確立起來。
隨著漢學(xué)場(chǎng)域的逐漸確立,英國對(duì)于中國文學(xué)的英譯也走向興盛,而尤其以漢學(xué)3大星座——理雅各、德庇時(shí)(J. Davis)和翟理斯(H. Giles)——對(duì)于中國文學(xué)的系統(tǒng)英譯為突出代表。理雅各早年曾任香港英華書院校長,并在港居住達(dá)三十余年,自1841年起開始系統(tǒng)地研究和翻譯中國古典文學(xué)作品。1861年至1872年,理雅各將其在王瑫和洪仁玕等協(xié)助下英譯而成的5卷本《中國經(jīng)典》(TheChineseClassics)先后出版,其中包括《論語》、《大學(xué)》、《中庸》、《孟子》、《書經(jīng)》、《詩經(jīng)》和《春秋左傳》。返回英國出任牛津大學(xué)漢學(xué)教授后,他在《東方圣書集》(SacredBooksoftheEast)中以6卷的篇幅出版其英譯的《詩經(jīng)》(與宗教有關(guān)的部分)、《孝經(jīng)》、《易經(jīng)》、《禮記》、《道德經(jīng)》和《莊子》等中國典籍。德庇時(shí)曾在中國擔(dān)任英國駐華商務(wù)總監(jiān)、駐華公使、香港總督,對(duì)中國文學(xué)的英譯涉及詩歌、戲劇和小說等多個(gè)方面。他是中國唐詩英譯的先行者,1829年他在倫敦出版的《漢文詩解》一書中包含杜甫的《春夜喜雨》和王涯的《送春詞》等詩歌的英譯,而其戲劇方面的翻譯有1817年在倫敦約翰·默里公司出版的《老生兒:中國戲劇》和1829年通過倫敦東方翻譯基金會(huì)出版的《漢宮秋:中國悲劇》(馬祖毅 任榮珍 1997:240,271)。另外,他的《中國小說選》(1822)收錄《三與樓》、《合影樓》和《奪錦樓》等小說的英譯,同時(shí)還在1829年以更加尊重原作的態(tài)度重譯《好逑傳》。翟理斯早年曾在中國擔(dān)任英國駐華外交官,回國后任劍橋大學(xué)漢學(xué)教授。他對(duì)中國文學(xué)的英譯十分廣泛,從詩歌到散文、從神話故事到佛教傳記均有涉及。他翻譯的《聊齋志異》(1880)被多次再版,深受西方讀者歡迎。翟理斯在中國文學(xué)英譯方面做出的最大貢獻(xiàn)當(dāng)屬他編譯的兩卷本《中國文學(xué)瑰寶》(1883/1922,1898/1922),其中收錄中國歷史上各個(gè)時(shí)期著名詩作和散文的英譯。此外,他撰寫的《中國文學(xué)史》(1901)也收錄多種體裁中國文學(xué)作品的英譯片段。
較之先前,英國這一階段的中國文學(xué)英譯呈現(xiàn)出系統(tǒng)、全面而深入的特色,而其中的根本原因則要?dú)w功于其漢學(xué)場(chǎng)域的確立。在英國漢學(xué)研究進(jìn)入高等學(xué)府、漢學(xué)場(chǎng)域逐漸形成的背景下,漢學(xué)研究從原先依附的傳教、經(jīng)商和外交等活動(dòng)中獨(dú)立出來,成為一門走向?qū)I(yè)化、專門化和世俗化的學(xué)問(Girardot 2002:123)。漢學(xué)家們的研究在時(shí)間、經(jīng)費(fèi)和出版渠道等方面有充分的保障,從而極大促進(jìn)其對(duì)于中國文學(xué)的全面研究和系統(tǒng)英譯。以理雅各為例,其在牛津漢學(xué)教席的設(shè)立在經(jīng)濟(jì)資本意義上得到倫敦涉華商界的巨額經(jīng)費(fèi)支持(同上:163),另外其后期對(duì)于《易經(jīng)》和《莊子》等幾部中國典籍的英譯和出版則直接得益于繆勒(M. Müller)與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合作的“東方圣書集”項(xiàng)目,而正是由于繆勒將理雅各英譯的中國典籍引入西方主流文化場(chǎng)域的生產(chǎn)和流通環(huán)節(jié),漢學(xué)意義上的東方學(xué)“在西方學(xué)術(shù)話語圈中取得學(xué)科性的認(rèn)可”(同上:142)。
2.4 沉寂期(20世紀(jì)初至20世紀(jì)中期):譯者慣習(xí)影響下的少量英譯
20世紀(jì)初至中期,由于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影響,英國的漢學(xué)研究受到很大沖擊,加之第一代漢學(xué)家已逐漸淡出歷史,自身嚴(yán)重削弱的漢學(xué)場(chǎng)域難以再對(duì)中國文學(xué)的譯介活動(dòng)提供有效支撐,因此英國對(duì)于中國文學(xué)的翻譯在整體數(shù)量和規(guī)模上都出現(xiàn)明顯下降,而與先前的興盛期相比,更是陷入某種沉寂。在此背景下,漢學(xué)家韋利(A. Waley)卻在中國文學(xué)英譯方面取得驕人成就,究其原因,則是與韋利本身在漢學(xué)場(chǎng)域中形成而又反作用于漢學(xué)場(chǎng)域的個(gè)人“慣習(xí)”息息相關(guān)。
韋利1907年進(jìn)入劍橋大學(xué)國王學(xué)院學(xué)習(xí),專業(yè)為古典文學(xué)。作為著名教授迪肯森(G. Dickinson)和摩爾(G. Moore)的學(xué)生,韋利深受兩位學(xué)者仰慕東方古代文明的影響,萌生致力于東方文化研究的愿望,因此于1913年應(yīng)聘進(jìn)入大英博物館東方部任館員(馬祖毅 任榮珍 1997:229)。出于工作需要,開始自學(xué)漢語,研讀漢學(xué)書籍,并到倫敦大學(xué)亞非學(xué)院深造,而后來更是到該院授課,對(duì)中國古典詩歌和古典文學(xué)產(chǎn)生濃厚興趣,決意將其譯介給英國讀者,從而走上英譯中國古典詩歌和古典文學(xué)的道路。其對(duì)中國文學(xué)的英譯作品主要包括《漢詩一百七十首》(1918)、《詩經(jīng)》(1937)、《論語》(1938)、《猴王》(《西游記》,1942)、《中國詩歌》(1946)和《敦煌歌謠與故事選集》(1960)等以及散見于各種期刊雜志的大量中國詩歌英譯作品。可貴的是,韋利的譯作質(zhì)量上乘,深受英國讀者喜愛,并且在英語文學(xué)界產(chǎn)生良好的影響。《牛津英語翻譯文學(xué)導(dǎo)讀》一書對(duì)韋利評(píng)價(jià)很高:“事實(shí)上,韋利是唯一將其中國文學(xué)英譯作品在眾多普通讀者中間流傳開來的譯者,這足以證明其文學(xué)才華橫溢、翻譯方法得當(dāng)”(France 2000:225)。而《不列顛百科全書》在介紹韋利的詞條中也說,“他優(yōu)秀的東方古典著作英譯作品對(duì)葉芝和E.龐德等現(xiàn)代詩人有深刻影響”(不列顛百科全書 1999:65)。韋利能在英國對(duì)于中國文學(xué)譯介處于相對(duì)沉寂的這一歷史時(shí)期脫穎而出,究其根本,除去其文學(xué)天賦突出的因素,大概與其在漢學(xué)場(chǎng)域中形成的樂于并善于研究、翻譯中國文學(xué)的個(gè)人“慣習(xí)”有關(guān),因?yàn)椤皯T習(xí)”不僅是環(huán)境和社會(huì)的產(chǎn)物,而且“具有改造自然,變革社會(huì)的潛在功能”(趙一凡 2009:751)。
當(dāng)然,除韋利外,這一歷史時(shí)期還有翟理斯之子翟林奈(L. Giles)對(duì)于《論語》和《孟子》等作品的少量英譯以及其他譯者對(duì)于中國文學(xué)作品的零星英譯。
2.5 復(fù)蘇期(20世紀(jì)中期至20世紀(jì)末):漢學(xué)場(chǎng)域恢復(fù)中的專業(yè)英譯
二戰(zhàn)以后,英國政府逐漸意識(shí)到其在中國問題及中國歷史文化方面存在的認(rèn)知缺失曾在其戰(zhàn)時(shí)帶來很多困難,因此戰(zhàn)后英國政府對(duì)于漢學(xué)研究的態(tài)度發(fā)生轉(zhuǎn)變:“從先前的輕視變成積極地開展調(diào)研,而從總體上來說,學(xué)生對(duì)于中國研究的興趣更濃,主修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學(xué)生人數(shù)也逐漸增多”(Chen, Hsiao 1967:10-11)。在這種背景下,英國的漢學(xué)教育很快復(fù)蘇和發(fā)展:牛津和劍橋開設(shè)可以授予榮譽(yù)(優(yōu)秀)學(xué)士學(xué)位的漢學(xué)課程,倫敦大學(xué)亞非學(xué)院增設(shè)關(guān)于中國哲學(xué)、歷史和藝術(shù)等領(lǐng)域的講師職位;除此之外,1952年杜倫大學(xué)設(shè)立漢學(xué)講師職位,1963年利茲大學(xué)開設(shè)中文系,1965年愛丁堡大學(xué)成立中文系。這樣一來,受兩次世界大戰(zhàn)影響的英國漢學(xué)場(chǎng)域逐漸恢復(fù)起來,而一直棲身于其中的中國文學(xué)英譯活動(dòng)也慢慢活躍起來,雖然就翻譯規(guī)模和譯者人數(shù)而言,這一時(shí)期難以與先前的興盛期相比,但在具體的翻譯水準(zhǔn)和研究層次上卻愈發(fā)專業(yè)。在當(dāng)時(shí)規(guī)模并不甚大的譯者隊(duì)伍中,霍克斯(D. Hawkes)堪稱翹楚。
霍克斯1945年至1947年在牛津大學(xué)研讀中文,1948年至1951年作為研究生在北京大學(xué)深造。返回牛津后,他以《楚辭》為題完成其博士論文,并于1959年發(fā)表包含《楚辭》英譯的專著《楚辭:南方之歌——中國古代詩歌選》,同年起擔(dān)任牛津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1971年,霍克斯辭去牛津大學(xué)中文系主任的教職,全心投入《紅樓夢(mèng)》的英譯。經(jīng)過10年的深入研究和精心翻譯,霍克斯將《紅樓夢(mèng)》前80回譯成英文,先后分3卷列入著名的“企鵝經(jīng)典叢書”出版。作為少數(shù)在中國高等學(xué)府深造過的英國漢學(xué)家之一,霍克斯對(duì)于紅學(xué)有很深的造詣,因此其《紅樓夢(mèng)》英譯水平堪稱專業(yè)而精湛。由于《紅樓夢(mèng)》原書存在著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程甲本和程乙本等多個(gè)版本,霍克斯沒有簡(jiǎn)單地選擇其中任何一個(gè)版本,而是在不同版本之間斟酌,選擇自己認(rèn)為足以構(gòu)成最佳故事的東西,自行組織一個(gè)特殊的本子作為源語文本,而這樣一來,“差不多每一個(gè)不同版本之間的選擇都要求譯者解決一連串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小說的作者情況及其發(fā)展演變,評(píng)注者身份的確定,早期編訂者的可信程度和他們的版本性質(zhì)等”(張弘 1992:267-68)。由此,霍克斯《紅樓夢(mèng)》英譯的專業(yè)水準(zhǔn)可見一斑。在他的指導(dǎo)下,《紅樓夢(mèng)》后40回由漢學(xué)家閔福德(J. Minfold)英譯完成,并于1982年和1986年作為后兩卷在“企鵝經(jīng)典叢書”出版。至此,西方世界第一部《紅樓夢(mèng)》英文全譯本誕生。值得一提的是,這部《紅樓夢(mèng)》英譯本借助企鵝出版社的平臺(tái),真正進(jìn)入西方主流文化場(chǎng)域的生產(chǎn)、流通和消費(fèi)環(huán)節(jié),成為中國文學(xué)作品英譯的成功典范。
另外,該時(shí)期著名漢學(xué)家葛瑞漢(A. Graham)英譯的《列子》(1960)、《晚唐詩選》(1965)、《莊子》(1981/1986)和白之(C. Birch)在話本小說研究基礎(chǔ)上英譯的《明代短篇小說選》(1958)等都顯示出很高專業(yè)水準(zhǔn)。
2.6 發(fā)展期(20世紀(jì)末至今):漢學(xué)場(chǎng)域變革中的新型傳譯
20世紀(jì)末以來,隨著中國經(jīng)濟(jì)實(shí)力和國際影響的持續(xù)上升,作為新型漢學(xué)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正在海外蓬勃興起。與向來致力于中國古典研究的傳統(tǒng)漢學(xué)(sinology)不同,“中國研究”關(guān)注當(dāng)代中國問題,側(cè)重當(dāng)代中國的經(jīng)濟(jì)、政治、社會(huì)和國際關(guān)系,其中也包括當(dāng)代中國的文化和文學(xué)。在此背景下,英國的漢學(xué)場(chǎng)域也在經(jīng)歷著同樣的變革:除從事“中國研究”的新型漢學(xué)外,傳統(tǒng)漢學(xué)在繼續(xù)研究古漢語以及中國古典文學(xué)、歷史與文化典籍的同時(shí)也開始關(guān)注起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而在這種變革中成長起來的英國新一代漢學(xué)家洛菲爾(J. Lovell)也由此成為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英譯的杰出代表。
洛菲爾,中文名為藍(lán)詩玲,畢業(yè)于劍橋大學(xué)中文系,后又獲現(xiàn)當(dāng)代中國文學(xué)博士學(xué)位,其博士論文探討中國作家的諾貝爾獎(jiǎng)情結(jié)。博士畢業(yè)后,洛菲爾曾在劍橋講授中國歷史和文學(xué),現(xiàn)在倫敦大學(xué)任教。2003年,她將韓少功的《馬橋詞典》譯成英文出版,2007年又將朱文的《我愛美元》譯成英文出版。2008年,洛菲爾將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wù)》翻譯成英文出版,2013年她又將朱文的8篇小說譯成英文,取名《媒人、學(xué)徒及足球迷》。最值得稱道的是,洛菲爾翻譯的《色戒》和《阿Q正傳和其他中國故事》被納入“企鵝經(jīng)典叢書”出版,在英國乃至整個(gè)英語文學(xué)界產(chǎn)生廣泛影響。
事實(shí)上,作為西方主流出版商的英國企鵝出版社,一直是中國文學(xué)與文化在英國乃至英語國家翻譯和傳播的重要平臺(tái)。近年來,列入“企鵝經(jīng)典叢書”出版的中國典籍英譯作品還包括《山海經(jīng)》(1999)、《大學(xué)與中庸》(2004)、《孟子》(2005)和《聊齋志異》(2006)等。2008年,企鵝出版社同時(shí)在倫敦和紐約推出由美國翻譯家葛浩文(H. Goldblatt)英譯的《狼圖騰》,獲得巨大成功。2011年,企鵝出版集團(tuán)在中國的子公司購買《北妹》、《公務(wù)員筆記》和《血罪》3部小說的版權(quán),開啟每年出版5至8本中國題材小說(英文版)的計(jì)劃。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英國與美國及其他英語國家之間在語言、文化和學(xué)術(shù)研究等領(lǐng)域的相互貫通,加之當(dāng)前文化場(chǎng)域日益加速的全球化進(jìn)程,中國文學(xué)作品在美國及其他英語國家的英譯本也同樣在英國傳播開來。比如,美國翻譯家葛浩文英譯的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作家巴金、莫言、蕭紅、蘇童、賈平凹、阿來、張潔和王朔等人的作品在英國廣泛傳播并產(chǎn)生一定影響。
3 結(jié)束語
社會(huì)翻譯學(xué)旨在探索翻譯與社會(huì)之間雙向互動(dòng)、復(fù)雜多樣的“共變”關(guān)系,以克服語言學(xué)研究范式囿于語際轉(zhuǎn)換規(guī)律的客觀主義不足,同時(shí)規(guī)避文化研究范式“文化決定論”的主觀主義的缺陷,而致力于消解主客二元對(duì)立的布爾迪厄反思性社會(huì)學(xué)理論于是便成為社會(huì)翻譯學(xué)的重要理論來源。鑒于此,本文在社會(huì)翻譯學(xué)的視閾中,揭示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傳譯活動(dòng)從萌芽期的“間接傳譯”推進(jìn)到肇始期的“直接英譯”,進(jìn)而躍升至興盛期的“系統(tǒng)英譯”,然后消退為沉寂期的“少量英譯”,繼而演進(jìn)至復(fù)蘇期的“專業(yè)英譯”,直至衍化為發(fā)展期的“新型傳譯”的整體運(yùn)作軌跡與規(guī)律。
盡管就整體而言,中國文學(xué)的主要方面在英國都得到翻譯和介紹。然而,就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傳播與接受的效果而言,我們卻不得不保持清醒的認(rèn)識(shí)。不久前,筆者曾以“中國文學(xué)英譯作品的傳播與接受”為題,在牛津大學(xué)人文社科專業(yè)的師生中開展過問卷調(diào)查,初步的統(tǒng)計(jì)結(jié)果難以令人樂觀。僅以《紅樓夢(mèng)》的霍克斯譯本、《紅樓夢(mèng)》楊憲益和戴乃迭譯本、《水滸傳》的賽珍珠譯本和《紅高粱》的葛浩文譯本4部英譯作品的接受效果為例,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真正讀過上述譯作的讀者分別僅占調(diào)查讀者總數(shù)的8%、4%、0%和6%,而這為數(shù)不多的讀者基本上又都來自原本就熟悉中國文學(xué)的漢學(xué)專業(yè)師生。由此不難推斷出中國文學(xué)英譯作品在英國普通讀者中間傳播和接受的整體現(xiàn)況。從社會(huì)翻譯學(xué)的角度來看,這其中的原因不僅與譯者采取的英譯策略相關(guān),更與英國讀者在其自身所處的各種場(chǎng)域中形成的個(gè)人慣習(xí)相關(guān),與各種資本支配下中國文學(xué)英譯作品在英國乃至整個(gè)英語國家文化場(chǎng)域的生產(chǎn)、流通及消費(fèi)狀況相關(guān)。
注釋
①“場(chǎng)域”(field)是布爾迪厄反思性社會(huì)學(xué)理論的核心概念:“從分析的角度來看,場(chǎng)域可以界定為由不同位置間各種客觀關(guān)系形成的網(wǎng)絡(luò)或構(gòu)型(configuration)”(Bourdieu, Wacquant 1992:133-134),可進(jìn)一步解釋為一種具有自我運(yùn)行規(guī)則且其規(guī)則獨(dú)立于政治及經(jīng)濟(jì)規(guī)則之外的“獨(dú)立社會(huì)空間”(social universe)(Boudieu 1993:162)。
②“慣習(xí)”(habitus)指那些“可持續(xù)、可轉(zhuǎn)換的傾向系統(tǒng),傾向于把被結(jié)構(gòu)的結(jié)構(gòu)(structured structures)變成具有結(jié)構(gòu)功能的結(jié)構(gòu)(structuring structures)”(Boudieu 1992:53),簡(jiǎn)單說來就是個(gè)人所擁有的性格傾向、思維方式和行為習(xí)慣等,它在社會(huì)的制約中生成,而一旦生成后又順應(yīng)并反作用于社會(huì)。
③布爾迪厄根據(jù)“資本”(capital)所處的具體場(chǎng)域和轉(zhuǎn)化的成本高低,將其區(qū)分為3種類型:可直接轉(zhuǎn)化為貨幣、經(jīng)常表現(xiàn)為產(chǎn)權(quán)的“經(jīng)濟(jì)資本”(economic capital);以教育文憑等為表現(xiàn)形式且在某些條件下可以轉(zhuǎn)化為經(jīng)濟(jì)資本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由個(gè)人社會(huì)職責(zé)和社會(huì)關(guān)系構(gòu)成、經(jīng)常表現(xiàn)為各種頭銜爵位且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轉(zhuǎn)化為經(jīng)濟(jì)資本的“社會(huì)資本”(social capital)(Boudieu 1986:243)。
④布爾迪厄認(rèn)為“存在的就是關(guān)系的”(the real is the relational)(Bourdieu, Wacquant 1992:97),因而在方法論上提出“關(guān)系主義”(relationalism)的原則,目的在于超越傳統(tǒng)社會(huì)學(xué)研究中個(gè)體主義與整體主義、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之間的二元對(duì)立,而該“關(guān)系主義”方法論主要貫穿于其提出的“場(chǎng)域”、“慣習(xí)”和“資本”這3個(gè)彼此關(guān)聯(lián)、互鑒互證的基本概念與理論方法中(同上:15-19)。
不列顛百科全書[Z].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9.
利瑪竇 金尼閣. 利瑪竇中國札記[Z]. 北京:中華書局, 1983.
馬祖毅 任榮珍. 中國翻譯簡(jiǎn)史[M]. 北京:中國對(duì)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7.
王洪濤. 建構(gòu)“社會(huì)翻譯學(xué)”:名與實(shí)的辨析[J].中國翻譯, 2011(1).
王悅晨. 從社會(huì)學(xué)角度看翻譯現(xiàn)象:布爾迪厄社會(huì)學(xué)理論關(guān)鍵詞解讀[J].中國翻譯, 2011(1).
張 弘. 中國文學(xué)在英國[M]. 廣州:花城出版社, 1992.
趙一凡. 從盧卡奇到薩義德:西方文論講稿續(xù)編[M]. 北京:三聯(lián)書店, 2009.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A]. In: Richardson, J.(Ed.),HandbookofTheoryandResearchfortheSocio-logyofEducation[C]. New York: Greenwood, 1986.
Bourdieu, P.TheLogicofPractice[M]. Chicag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Bourdieu, P.TheFieldofCulturalProduction:EssaysonArtandLiteratur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Bourdieu, P., Wacquant, L.AnInvitationtoReflexiveSocio-log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Chen, Y.-S., Hsiao, P.SinologyintheUnitedKingdomandGermany[Z].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1967.
France, P.TheOxfordGuidetoLiteratureinEnglishTranslation[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Girardot, N.TheVictorianTranslationofChina:JamesLegge’sOrientalPilgrimage[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Merkle, D. Translation Constraints and 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A]. In: Pym, A., Shlesinger, M., Simeoni, D.(Eds.),Beyond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St. André, J. Moder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ast Translation Practice: European Translations of theHaoqiuZhuan[A]. In: Chan, T.-H.(Ed.),OneintoMany:TranslationandtheDisseminationofClassicalChineseLiterature[C]. Amsterdam: Rodopi, 2003.
ADiachronicAccountoftheEnglishTranslationofChineseLiteratureintheUKfromthePerspectiveofSocio-translationStudies
Wang Hong-tao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 incorporated in such concepts as field, habitus and capital put forward by Pierre Bourdieu in his reflexive sociology to contextualiz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UK, by situating the six phases of the translation activity diachronically against the specific cultu-ral-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UK and the world, so as to reveal the covariance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the social-cultural dimensions involved and track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UK during the past four centuries.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field; habitus; capital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xiàng)目“中國文學(xué)作品在海外的傳播及影響”(09BWW003)的階段性成果。
H059
A
1000-0100(2016)03-0146-6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3.030
定稿日期:2016-04-01
【責(zé)任編輯謝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