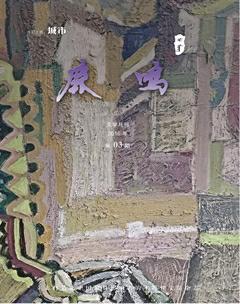地球上的一座城
春樹
在冬日,朦朧的清晨
清晨在蒙蘇利公園
公園在巴黎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
地球上天上一顆星
——Jacques Préver
夢一般美的巴黎女人
突然又開始迷戀巴黎,或者說是迷戀法國。那種慵懶又迷人的氣質,漫不經心的藝術氛圍,熱愛生活、熱愛色彩、熱愛細節、熱愛享受的法國式生活……
法國女孩向來與眾不同,在打扮上,她們最討厭的可能就是從眾和庸俗。《碟中諜4》里性感的女殺手太讓人驚艷,我目不轉睛地看著她,這個女孩一看就是個法國女孩。也許是因為她的化妝?沒有濃妝艷抹,甚至沒有刻意修去稍顯浮腫的眼袋,僅僅是畫了條眼線,涂了些睫毛膏。也許是因為她的眼神?靈敏、機巧、有一絲傲慢,絕不試圖討好或媚俗。法國女孩就是這樣,如同一朵懶洋洋的睡蓮,美麗又淡然,就像藏了一個謎語。不要研究法國式的美,要研究你自己的特點和個性,這才是法國式的秘密。
法國人討厭極端,法國女人討厭功利和社會階層。法國人保護個人生活,又對八卦艷情報有寬容態度,法國女人不像別的國家女人那樣在乎年齡,在乎大牌時裝,歸根結底,她們的生活態度就很藝術:順其自然,關注美,珍視美。美是多么重要啊,美就是一切!
曾經討厭巴黎,寫過一首詩叫《巴黎春天》,里面惡狠狠地奚落巴黎。更年輕的時候當然喜歡紐約這只大蘋果,巴黎落伍了,不再是世界藝術的首都,像蒙了一層塵的美人,自顧自地美和落寞。曾在巴黎呆過短暫的幾天,穿白色緊身小吊帶和牛仔褲,逛盧浮宮,去公園,在路邊喝咖啡,夜晚去了埃菲爾鐵塔,當整點鐵塔開始亮燈時,覺得它一陣抽搐,簡直像個行為藝術。現在想來,這是一種形式感,一種很有趣的形式感。有個細節我至今難忘,在去現代藝術博物館時,除了牛仔褲,上身只穿了一件藍色的kenzo肚兜,后背只系著一條絲帶,除此之外全部裸露。并沒有任何人指指點點,沒有人用語言或眼神打擾我,在這里,穿任何時裝都可以。
慢慢地,我開始喜歡上法國情調和巴黎。15歲時看過的法國哲學類和文學類的書又重新撿起,還有那些法國新浪潮電影、法國香頌,甚至法國女孩的家居類裝扮,都讓我入迷。紐約更先鋒,倫敦更前衛,但只有巴黎,更注重平衡,更不急不徐,姿態從容,流露出一種:愛誰誰,我就是我,你愛喜歡不喜歡的精髓,換句話說,這叫“自由”。18歲的時候迷戀英國朋克式的緊身打扮,只求引人注目,20歲的時候喜歡紐約式的混搭和意大利式的裸露性感,現在開始喜歡法國時尚中的天然魅力:舒適與簡單。
時尚是一種意識的反映,你的思想是什么樣,你就穿成什么樣。我心中的時尚之王是伊夫·圣·洛朗,他曾說過:我討厭資產階級的女子,討厭她們倔強和精神。她們總在某個地方別著首飾并且頭發梳得油亮。他的夏娃是“那些不會受任何事情困擾的女性”。換句話說,她們不再是獵物,而是獵人。
如果沒有巴黎女人,巴黎也就不再是巴黎。她們為什么看起來那么優雅自在迷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即使你一件件分析她們身上的衣服,你都無法得出準確的答案。我的法語老師Léa就是個典型的巴黎女子,穿著顏色穩重的墨綠色T恤和一件長短合度的黑色長褲,下面是一雙高度和褲子配合得非常好的黑色高跟鞋,一頭長卷發,挑染了一些亮棕色,身材苗條又有曲線,自然而舒服,總而言之,簡單又好看,比例剛好,毫無破綻。
要知道在一堆不擅長打扮或者打扮過度的德國人里面,看到她這樣的女子,真的是讓人眼前一亮啊。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容易過度打扮的英國女人、精心裝飾的美國女人、自然樸實的德國女人都不是我的菜,只有俏皮可愛又帶一絲隨意的法國女人才讓我真正折服。審美是從小培養的,不去巴黎怎么能知道她們的秘密?我只知道,她們并不會貿然穿一身名牌,更不會為了LOGO而穿,也不會打扮得過分精致(上了年紀的女人除外),而到底是這個國家對藝術的尊重,對不同年齡段女人的熱愛和美食文化才能建構出這樣迷人的女子。她們也并非空有虛名,她們畢竟是波伏娃的后人。
巴黎女孩的秘密是什么?這真是個迷題,吸引著我一再去巴黎。只為了呼吸巴黎的空氣,看看巴黎天空的云朵,吃一下小館子,放縱一下自己,買些美妝和衣服。它每次都讓我流連忘返,我不會厭倦巴黎,因為它就是美夢。
巴黎,一場流動的盛宴
搬到柏林三個月后,我們急需度個假,我的第一選擇就是:巴黎。
每每因柏林的粗糙、狂野而感慨的時候,我都會用巴黎來安慰自己。這是座給了太多人安慰的城市,它離柏林大概一千多公里,坐飛機一個多小時就能到達,然而這兩座城市的區別又是那么明顯,一座是陽性十足的生猛嚴謹,一座是女性化且精致無比的浪漫抒情。它們猶如猛男和淑女一樣對比強烈。
抵達巴黎的時候是夜里十一點多,當時我還在想,會不會街上沒什么人。哦,這真是太小看巴黎了,街上依然車水馬龍,路過的咖啡館外都坐滿了人,這座享樂的城市是不會那么早就打烊的,夜色溫柔,巴黎越夜越美麗。
依然住在十三區的一家小旅館,它只有二十幾間房,小巧得猶如巴黎本身,有一個狹長的院子,草長得很整齊,草坪周圍種植著幾棵不知名的花樹,有一株是金黃色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在臺灣見到過的俗稱“黃金雨”的花。還有一株灌木,粉紅色的花還是合攏狀態,待到白天,它便綻放了。這次我們沒有訂到一層的房間,二層的房間需要走一段窄窄的樓梯,房間布置和一層類似,只是樓道非常窄,只能單人通過。拉上白色印花的窗簾,躺到桃紅色的枕頭上,頓時感覺到一股巴黎特有的感受——像飄在云朵里。那枕套的顏色就像成熟的蜜桃,又甜又軟,配上蜜橘色的毯子和極淺的鴨蛋青色的被套和白色的床單,視覺感覺恰到好處。
正餓著,樓下服務員送來了一杯甜白葡萄酒,一杯熱巧克力和二塊酥皮點心,統統來自旅館旁邊的餐館,一家法國西南部特色的餐館。
起床后第一件事當然是去吃早餐。錯過了旅館自帶的早餐,不怕,還有許多選擇。我們去的是一家名為Le Loir dans la théière的咖啡館,這里熱鬧極了,差點沒進去……服務員熱情周到,但放心,如果你是單獨出現或者只是兩個人,他是不會給你四個人的桌子的。像巴黎所有的咖啡館一樣,這里密度很高。我們坐的桌子,旁邊的人離我們只有一臺電腦的距離。但是沒有人抱怨,因為下午之前這里真的很搶手。點壺有水果香氣的綠茶,再叫一個沙拉或者夾著辣椒和西紅柿的蛋卷,總之味道實在棒極了,周圍的人也都在滔滔不絕地聊天,包括坐在我左手邊上的兩個老太太,她們真的很巴黎,打扮得體,具備巴黎女人可愛的八卦本能,雖然我聽不懂她們的對話,但她們真的一直在不停地說,直到我們離開,她們還在聊,像兩個青春期的少女,可愛極了。
依舊,像每次來巴黎,總是上街隨意逛。總是在散步的過程中能發現許多有意思的店,除了耳熟能詳的連鎖店以外,還有些是更有特色的小店。除去逛街購物以外,我最開心的一天是周日,那天所有商店關門,只有博物館還開著。LV Fondation位于十六區郊外,排隊的人已經排成了一條長龍,從穿著看,他們大部分都是本市人,偶有少量熱愛藝術的游客。
在排了大概四十分鐘的隊后,我們進入了這座博物館。在這里我居然看到了蒙克的《嚎叫》和莫奈的《睡蓮》。樓上是先鋒藝術家的展,質量很高。憑著這張票,我們又免費游覽了近在咫尺的有150年歷史的大公園Jardin Dacclimatation。這里有許多兒童游樂設施,還有農場、動物園、馬場、蔬菜園,大人們在這里也可以玩得心滿意足,包括在草地上野餐、參觀首爾園、日本長野小木屋,渴了還可以去中國茶樓喝茶……
令人開心的是,這座公園內的餐飲水平很高,居然有現場制作的廣東式蒸餃和燒賣,價格不便宜,然而剛吃了第一口后,我就發現物有所值。小小的幾只點心,每一只的餡都不一樣,獨具匠心。冰淇淋呢,也有更為健康的酸奶冰淇淋,用的是來自于諾曼底地區的不含脂肪的酸奶,隨意加些水果進去,比如草莓或菠蘿片,口感剛剛好。這時候就不能抱怨價格的高昂了。
巴黎于我而言,完全變成了一座吃喝玩樂的圣殿,滿足口腹之欲,或者是逛街購物,所有人都會在這里如愿以償。
千萬不要過于迷戀巴黎喲,因為它實在是太貴了!
是的,如果有一個地方能讓女人如此崇拜如此欣賞,那就是巴黎。這座偉大而恢宏的城市獨一無二,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能與巴黎的美相提并論。這也是座昂貴的城市,我沒有看過全球最貴城市排行榜,而在我的經驗里,它和紐約倫敦的物價不相上下,統統是那種既能讓你享受到無上的美好,又能讓你的荷包大出血的城市。每天僅僅是在不同的咖啡館喝咖啡,再吃點小東西,加起來的錢都讓人心疼了。
巴黎擁有美妙的購物氣氛,因為它處處是小店,處處是風景。公園旁邊的小路口就有商鋪,博物館對面也可能就是家迷人的小店。就連路邊,周末也有市集。中國人最喜歡去的老佛爺、巴黎春天,我已經嗤之以鼻,只心儀左岸最有情調的一座商場,平時這里沒什么中國人,游客更不會樂意來這里。但是那天,我到商場樓上去辦理退稅時,發現有對衣著光鮮的中國母女正坐在柜臺前面,旁邊急匆匆走來一個男服務員,左右兩手里拎著她們剛買的Chanel。一瞬間,我都仇富了。
第一次去巴黎
當清晨,我們坐了一夜長途巴士抵達巴黎的時候,我的錢包里只剩下三百歐元了。但是,那句話怎么說的,盡管我們窮困潦倒,但是我們到了巴黎!
巴黎的清晨是淡灰色和淡粉色相間的。空氣清冷而濕潤,我們睜大雙眼,拼命捕捉巴黎初秋的風韻。
在把隨身的行李存到了火車站的臨時行李箱后,我們決定到路邊的咖啡店吃早餐。點了咖啡和羊角面包,我們坐在路邊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把羊角面包在咖啡里蘸一下,開始吃。剛剛出爐的金黃色的面包松軟可口,香甜的巧克力醬配上淳厚的咖啡,不禁感嘆:在巴黎吃飯果然是種享受!
巴黎,喬治桑的巴黎!薩特和波伏瓦的巴黎!蘭波和波德萊爾的巴黎!迷人的薩崗的巴黎!茶花女的巴黎!
花神咖啡館。早在我去過巴黎之前,我曾經寫過一首詩,就叫《花神咖啡館》:
花神咖啡館
我坐在花神咖啡館
這里是巴黎么
我要看看那張桌子
還要偷走一個煙灰缸
像報紙上說的少年一樣
我扔掉了許多衣服和無用的首飾
也沒什么意思
也決定不了我身邊
是不是還坐著一個
親密的人
實際上在更早以前,我還寫過一首《巴黎春天》:
不知道古往今來有多少中國人都向往巴黎
那個漂浮著香水咖啡美酒的艷情之都
巴黎的女人很嬌小 喜歡戴著便帽
項鏈和精致的手套
法語是上層人的語言
巴黎 巴黎 巴黎 巴黎 巴黎 巴黎
已經被說俗了的巴黎 我討厭巴黎
巴黎呆在陰溝里我喜歡紐約
哪怕是世貿大廈再倒塌幾座
我還是喜歡美國的感覺
除了美國,全世界都沒有青春
我喜歡粗俗的美國人我喜歡可口可樂
我喜歡美國的街道和冷漠的都市感覺
這一切是如此融洽
巴黎有的只是成熟后的婦人
巴黎只有春天 曖昧的春天
聞之欲吐的春天 骯臟齷齪的春天
看來那時候對巴黎的感覺實在太唐突了些。
去了盧浮宮。
金字塔。下午,我們坐在咖啡館里,開始思考晚上該去誰家里借宿。我突然想起,有個朋友在巴黎。我給她發短信,她剛好有時間。她住在十二區的一座居民樓內。樓梯都是老式的,年代有些年頭了,踩上去還會吱吱作響。
房間兩室一廳,不太大。她平時與另一個女生合租。
她的房間明亮,整齊。據她說,所有東西都是一點點買來搬進來的,“這里不像國內,搬家很麻煩。”
晚上我們就在她的屋里打地鋪。
我們去了公墓。向薩特和波伏瓦的墓地送了束花。
微風吹在我的臉上,
我躺在那里
遠處有人在吹口哨
我睜開眼皮,天下著雨
那是柔和而平靜的雨
——薩特《惡心》
這個矮個子、斜視、其貌不揚的男人出生在1905年6月21日的巴黎。從此,去巴黎的觀光客除了參觀這個香水、服裝、咖啡和美酒的艷情之都,還多了一個去處,看看薩特和波伏娃日常討論和寫作的地方“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各國的文學愛好者也可以去花神咖啡館和它隔壁的雙偶咖啡館(lesdeuxmagors)偷個煙灰缸,再順便抬頭看看紫色的天——薩特說過一句如夢如幻的話“巴黎的天空是紫色的”。
薩特,從17歲就開始影響過我,說來慚愧,雖然家里堆著《薩特全集》和他零零散散的一些其它著作,但他的劇本實在看不懂,但他真是一個牛逼的演說家:
“倘若某人想出名,他要的不是出名:他想要一切。”
“我們應當不懷著希望行動。”
“自由地承擔所有的責任。”
“是懦夫讓自己變成懦夫,英雄讓自己變成英雄。”
“人是自由的。人本身就是自由。”
“離開愛的行動是沒有愛的;離開了愛的那些表現,是沒有愛的潛力的;天才,除掉藝術作品中所表現的之外,是沒有的。”
不排除許多知道薩特名字的讀者通過流行的格言來揣度他們自己的薩特。而他的代表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真正看下來的只有極少的一部分人。就像魯迅一樣,知道他名字的人遠遠多于真正看過他所有著作的人,而在這些全部看過他著作的人中,真正懂他的人又有多少?
他的書中,我最喜歡的是《惡心》、《墻》、《臟手》和《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其中《惡心》是本很好看的小說,講的是一個叫安東納·洛根丁的比較孤獨的學者在一個小城遇到的人和事,他常常感到一種奇怪的感覺,后來他發現,那種感覺叫“惡心”。這惡心呼嘯而來,呼嘯而去,每次都讓人有種眩暈的感覺,而且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在此時此地存在。總之,就是“忘了我是誰”。這種景象倒很符合《存在與虛無》中的一句悖論“它是它不是的東西,它不是它是的東西。”薩特說,人之所以感到惡心,是看到了生活中并不美好的真實所在。至于《臟手》,也別怪這戲讓許多人誤會,并且遭禁,熱愛共產黨的作者“搗騰”出這么一部寫共產黨人殺共產黨人的戲是容易被政治利用,《墻》講得是一個比較荒誕的故事,帕勃洛經過五天的單獨禁閉,又在地窖關了二十四小時,他等了三個小時才輪到受審。回到牢房接著等……他告訴了審問他的敵人朋友的假地址,卻弄假成真,傍晚他獲悉朋友被捕。而《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是薩特對存在主義所受到的一些指責,提出答辯。他指出:除了出生是不自由的以外,別的都可以自由選擇,因此你要為你的選擇負責。存在主義的根本論點是存在先于本質,倡導個人主觀意識的復蘇。關于虛無:既然所有的結果都走向虛無(即死),所以更要珍惜選擇的自由。
他每日筆耕不綴。他遵守他的諾言“我的心臟的最后一次跳動,剛好落在我的著作最后一卷的最后一頁”“明天寫得更好,后天寫得好上加好,最后以一部杰作告終”堅持寫到雙目完全失明方始擱筆。
1980年4月15日,薩特逝世于巴黎魯塞醫院,終年75歲。5萬人自發地走上街頭,用這個薩特常用的表達自己的方式為這個哲學家送行。正如薩特所說,“存在主義必須在生活中印證為真誠的,生活為一個存在主義者,意即準備為這個觀點付出代價,不僅是把它寫在書上而已。”他的那些擁簇,也都接受了他的觀點,所以他們走上街頭用存在主義者的方式紀念他,一個哲學家和作家得到這樣的待遇還真不多見。波伏瓦死后,和薩特一起合葬在蒙巴納斯公墓。這是這對親密朋友、戀人、最理想的對話者必然的歸宿。
再次來到墓地,是為了尋找俄羅斯導演塔可夫斯基的墓。我們來到拉雪茲神父公墓,卻意外地找到了“大門”的主唱Jim Morrison的墓地。他是很多愛搖滾的人的偶像,1971年,旅居巴黎的Morrison被發現死在了他公寓的浴缸里。他的墓地也就留在了巴黎而非美國。他的墓前被攔起了欄桿,不少樂迷都會來此朝圣。我把一束準備送給塔可夫斯基的玫瑰扔了進去。后來我們才發現,塔可夫斯基的墓地在郊外一個俄羅斯墓園。我們用了兩個小時才尋到那里。這就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