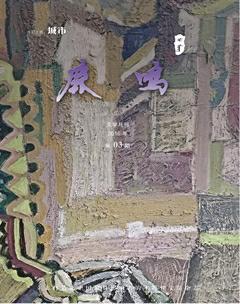城市的門坎
誓戎
十幾年前我寫過一首小詩,叫《城市的門坎》,詩中道:“父親和父親的父輩們/捐高的城市的門坎/真陡/收錄機的幾個鍵盤/竟讓我跋涉了多年,我還在母親的叮嚀中,蓄起了長發,無數次狂風吹過,才形成了今天的風景線”。從藝術的角度看,這首詩意境一般,草草收場,但它表達的情感卻很真實客觀。三十多年前,城市的門戶不像現在這樣洞開,一個農村青年能從有限的縫隙鉆入城市,并在城市里立穩腳跟,其中的艱難困苦難于言表并刻骨銘心。盡管現在我是一名有著三十幾年教齡的高職院校老教師,到如今還常常夢到不知什么緣故被學校下放到家鄉烏盟察右前旗當鄉村教師去了,夢中的我不要說重返城市,就是想調回有火車站的旗里工作也萬不可能。每逢做這類夢時我總是大汗淋漓痛苦不堪。這可能是城市門坎的陡峭程度對我的內心觸動太深太久的緣故。
我小的時候正是國家三大差別最嚴重時期,城市農村森嚴壁壘,村里人想成為一個吃商品糧的市民,難度無異于登天。當時農村青年上大學和當工人主要靠村里和鄉里推薦,而全公社那幾個微乎其微的指標,社隊兩級的干部們都為各自的子女們爭得頭破血流,豈能推薦到普通村民身上。我上面有兩個哥,大哥材地不錯,可惜上完小學就趕上了“文革”大串聯,老師領著他們去了一趟北京,回來便不再上學了。二哥從小不愛學習,只上了小學二年級。兩個哥沒念成書,加上我家的家庭成分較高,是富裕中農,參軍或做社辦教員根本無望,就只有修理地球的份了。母親看著兩個虎騰騰的兒子整天挖土翻糞的勞作,再看看個別因出身好或有門路而成為煤礦工人、鐵路工人的人回村后威風八面的樣子,時常嗟嘆道:“哎,麻煩,工人(公)呀母人的”。的確當時跳出農門到城鎮當了工人或干別的,社會地位比在農村當社員不知高出多少倍,他們回農村找對象盡揀好的找,還不花一分彩禮錢。村里的姑娘為了找個在城鎮工作的對象,托親戚朋友介紹來介紹去,好的沒有,嫁給腿瘸眼斜的也干。有件事對我影響很深,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國家的糧食政策是統購統銷。集寧市是離我們村最近的城市,市里有的工廠所需的土豆得去我們村拉。有一年,集寧肉聯加工廠去我們村拉運土豆,隨車來的有幾名小伙子,個個穿著藍棉大衣翻毛皮鞋,很精神。集寧肉聯場在全國也有名氣,職工一千多名,這幾個小伙子是正兒八經的工人。他們在村里待了三天,村里騷動了三天,村里十幾個妙齡姑娘,想著法子和他們接近,有的摘出家里的葵花餅給青工們吃,有的加班加點地幫肉聯廠揀土豆裝土豆,有的則穿著新絲襪臉上搽滿雪花膏圍著青工們說笑。當然這些舉措里一部分姑娘是指望抓住短暫的時間同城里青工速成對象,一部分則是把同青工們接近或說幾句話作為一種榮耀。三天后,這三位青年工人同拉土豆的車一道走了。但這幾個青工個個是負心郎,受了那么多優待,走的時候和姑娘們連聲再見也沒說。前面提到過集寧市是離我們村最近的城市,因此村里的大人們動不動就說集寧長集寧短的,當時在我稚嫩的心里總認為集寧是個大城市,村里的小伙伴們也都這樣認為,要是誰去了趟集寧,能把其他小伙伴羨慕死。我上小學二年級那年夏天,生產隊派父親趕馬車去集寧拉貨,父親說要帶我去,走之前那幾天,我心里忐忑不安,生怕父親變了卦。其實父親不會那樣做,父親之所以費心費力地帶我去集寧,一是了卻我吵嚷幾年的心愿,二是讓我這個好奇心特重的男孩見見世面。集寧離我們村一百二十多里,路上走了兩天,臨進城時,父親對坐在車中莜麥秸捆上的我說:“到了街里見到稀奇的東西不要亂叫亂說,看街上的小孩笑話你罵你地老大”。我就依從了父親的話,啥也不敢說,瞪大眼看高高的大煙囪和屋上摞屋的樓房。那次進城父親還領我進了飯館,我們一人吃了碗素面條,我至今記得那面條是一角二一碗。對了,隱隱約約還記得那次父親還給我五分錢買了塊酸奶豆腐,和五角錢買了個鐵皮鉛筆盒。
現在我已是個有著三十幾年“城齡”的老包頭人了。住著電梯高樓,用著智能手機,并且還自費出版過詩集,按理說我該算城里人了。其實不然,我私下合計了一番,我只能算半個城里人,因為我有著城里人那種懂知識講衛生,但沒有許多城里人的矯情偽飾和精于算計。此外,到如今我還保留了許多農村人慣有的習性,如吃飯喜歡圪蹴在地上并愛用大海碗等,如為人老實辦事實在等。這也就是說,我到如今還沒有徹底跨越城市的門坎,仍留下半個身子在外面。城市的門坎真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