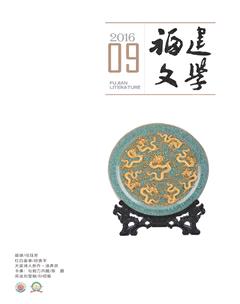撲入眼簾的兩只貓(創作談)
任玨方
中篇小說《眼球》講了一則近乎虐心的故事。電臺音樂節目女主播丘彌臨危受命,為提升收視率,被調去參與一檔電視節目的網絡宣傳。把這份工作掰開來看,非丘彌愿意、喜歡做的事。丘彌的愿望是在圖書館里,安安靜靜地生活。但她深陷在現實中,被驅趕被鞭策,朝目標前行。她看到了危險,某種東西像小說中隱藏在水底的蛙人,隨時準備將她拖進水底,成為利益祭品。她體會到了不可抗拒,她的人格與生活,在旋渦里無法自主,繼而飛速沉淪。為此,她有過掙扎,有過逃離。但她能做到的掙扎,只是在寂靜的山里,聽男友從嘴里吐出一句一句關于寧靜的詞語。在寧靜中生活,看似平常,卻需要勇氣。口吐寧靜屬于畫餅充饑。即便如此,男友還是鼓勵她“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兩個人都知道,無法不回歸現實。現實具有強大的魔性,讓他們逃不掉、放不下,只能想象、渴望去過“泛五湖”的生活。丘彌看到了毀滅。當節目組安排她玩命之際,她無法將這極度荒謬、瘋狂、駭人要求與現實等同,她的瘋、倦、怕剎那間達到巔峰,終于迷失在夢幻般的現實里。
有兩只貓——一黑一白,蹲在人們面前。
印度人克里希那穆提說,人們的意識是不停地掙扎去適應、修正、改變、吸收、拒絕、評估、責備、判斷,但是任何這樣的意識運動仍然處在痛苦的模式當中。這意識中的任何運動,如夢想、意愿,都是自我的運動。任何自我的運動,不管是朝向最高的,還是朝向最平凡的運動,都滋生著痛苦。這種意識掙扎的說法,用在丘彌身上很適合。意識掙扎本身有多層意味。激發意識掙扎的前提有三,一是知道行為對錯的尺度標準,二是知道具體行為已落到尺度標準之下,三是有自我救贖意愿。意識掙扎的結果也有三:一是沉淪到底,二是自救成功,三是始終在尺度標準上沉浮。意識掙扎始終是主觀世界里發生的事。一般來講,主觀指人的意識、精神,客觀指人的意識以外的物質世界,或指認識的一切對象。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主觀和客觀是對立的統一。客觀是不依賴于主觀而獨立存在的,主觀能動地反映客觀,并對客觀事物的發展起促進或阻礙作用。主觀、客觀,像是兩只貓,在現實與意識之間跳躍,有時讓人愉悅,有時讓人痛苦——因自我性、自主性的意識掙扎。
在現實與想象之間跳躍著兩只貓,在經濟生活領域同樣也跳躍著兩只貓。這兩只貓也足夠讓人們目眩。
《眼球》的背景是一則眼球經濟故事——兩臺電視節目爭奪收視率,展開針鋒相對的對抗。眼球經濟是注意力經濟的別稱。經濟學家的解釋是,之所以把注意力經濟形象地稱作“眼球經濟”,是指實現注意力這種有限的主觀資源與信息這種相對無限的客觀資源的最佳配置的過程。在網絡時代,注意力之所以重要,是由于注意力可以優化社會資源配置,可以使經濟團體獲得巨大利益,注意力已成為一種可以交易的商品,這就是注意力的商品化。注意力作為一個個體資源雖然是有限的,但如果從全社會總體角度看,它又是非常豐富的資源,而且其再生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從而引發的經濟效益具有倍增的乘數作用。在《眼球》這篇小說中,兩家電視臺的節目爭奪收視率,是因為節目收視率、受眾規模比利潤更受到投資者重視。
寄托于一則眼球經濟的故事,小說《眼球》有它的自身訴求。它竭力想要去描繪眼球端出現的問題。眼球端的問題,直截了當地說便是現代各種社會關系中人的問題。這個問題龐大,一個中篇無法承擔。小說《眼球》圍繞人際關系與社會活動的標準、準則,設置了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就是什么是標準、準則。比如節目好不好憑什么去判斷?一種做法對不對憑什么去衡量?小說里有兩檔電視節目,一檔節目從制作到播出質量都很好,但它總是立在失敗者位置上,面臨夭折。另一檔節目善于炒作,喜歡走捷徑。小說中的人物,他們的答案顯而易見,誰成功,他就是好的、就是對的。可以看出,成功者不僅掩蓋了一切問題,而且可以掌握規則,這是非常可怕的。現實允許這樣的判斷標準嗎?對應到現實中看,笑貧不笑娼這樣的社會俗語出現,可見成功所標榜的張揚的某些東西,足夠混亂。在追求利益中各種手段層出不窮,不惜突破公共道德的底線,違反公序良俗,乃至違反法律,類似的事件早已屢見不鮮。幾十年前,當白貓黑貓在經濟領域大顯身手時,我們無法判斷這兩只摸著石頭過河的貓。現在,多少可以看出些端倪。經濟活躍要感謝兩只貓,但產品造假、環境污染、惡意競爭等等現象層出不窮,我們是時候給白貓、黑貓定規矩,將白貓、黑貓裝進法律的籠子里了。
有一段論述非常好。“利益既可以指經濟利益,也可以指社會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是一個比較廣泛的范疇,而我們卻常常將其狹義地理解為單方面利益,從而導致了許多錯誤的觀點。”
責任編輯 楊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