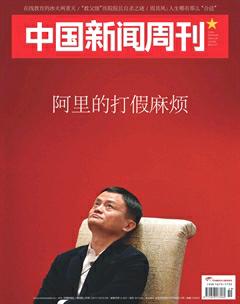推進土地資本化,讓農者有其股
楊英杰
習近平最近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上強調指出,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
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是有歷史記載以來執政者所極為關注的問題,亦為眾多居廟堂之高或處江湖之遠人士所關心。
縱觀數千年的中國史,朝代的更迭、政權的沉浮,可以說都能夠從是否穩妥解決農民與土地關系這一問題中尋找到答案。無怪乎毛澤東同志即指出,“誰贏得農民,誰就會贏得中國;誰解決了土地問題,誰就能贏得農民。”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一直把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作為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由此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調。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1951年,梁漱溟先生參加了幾個月的土改工作,受到極大震撼。他寫道:“此次到西南參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遠角落的農民身上牢牢建筑起來;每一個農民便是一塊基石。”“每一個農民便是一塊基石”,非常形象地描繪了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治國之要。
肇始于上世紀80年代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得億萬農民成為改革開放的急先鋒,隨著農村社會生產力的極大解放,鄉鎮企業的大發展推動了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速,中國農村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充分說明,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處理好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巨大歷史性成就,制度創新居功至偉。尤為值得肯定的是農村土地的制度性創新,不僅解決了中國的糧食問題,更為中國工業化、現代化提供了龐大的勞動力儲備。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人還是同樣的人,地還是同樣的地,只是改變了土地使用權性質,就使得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土地使用效率和農副產品數量質量的提高,農村勞動力逐漸流向鄉鎮企業,較低的勞動力成本成就了大量的鄉鎮企業,而隨著經濟發展,第一批較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也隨之產生,為中國工業化進程提供了人力資本的支持。
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任何制度變遷之邊際效益都會遞減,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亦需不斷演進深化,才能逐漸適應農村、農民、農業為跟進全球化、現代化、工業化之需求,這也是近年來一系列涉農制度出臺的根本原因。其中最要緊的目的則在于提高農村土地資本的高效流轉,以實現土地資本化的內在需求。土地資本化是當前農村土地(包括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最終指向,因為任何物品的資本化都是以發揮其最大效用為目的,也是實現物品價值最為高效最為快捷的途徑。
近日,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透露,目前全國1/3的土地已經流轉,如何完善農地產權機制變得日益迫切。
比如,有的地方已將農村土地集中以實現規模化經營,農民既可以土地入股取得分紅,也可以作為勞動者領取工資報酬。可以預期的是,土地資本化特別是股權化將成為農村土地制度進一步改革的一個方向性舉措。對于已處于迥異于農耕時代的工業化中后期階段的中國,經濟對就業的容納能力顯然已經擺脫農業生產力低下對勞動力的束縛,因而股權作為土地的抽象代表,流轉的便利性、甚至在適當時候的易變現性,將會極大地釋放農村生產力,不啻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的第二次革命。
當然,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須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堅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當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最為關鍵的前提,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是要抓緊落實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制度,真正讓農民吃上“定心丸”。也只有真正實現農地的“確權”,農地的“確股”才有基礎,農地資本化更具可操作性。
推進土地資本化,讓農者有其股,是農業現代化的需要,也是農民城鎮化的前提。當然,無論是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還是農民進城,政府可以引導示范,但不能搞強迫命令,不能一陣風、一刀切,要將選擇權留給農民自己。
(作者系中央黨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