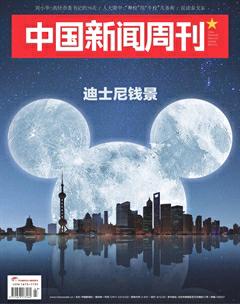殺掉一個人,拯救一百人,你如何抉擇
楊時旸
一邊是無辜的小女孩,另一邊是房間內正在試穿自殺式爆炸背心的恐怖分子,到底如何抉擇
從題材上講,這部《天空之眼》不可避免地會讓人們聯想到《獵殺本·拉登》,而這二者之間其實并不相似。《天空之眼》在于提出了一場嚴肅又殘忍的道德拷問,一堂沒人能給出答案的人性公開課。
凱瑟琳上校追蹤一名女性恐怖分子頭目已經六年,終于確認了她的出現地點,準備實施無人機定點轟炸。但此時,在那所目標房屋的門外,出現了一名販售食物的無辜小女孩。圍繞著這個“附帶傷害”的致死可能性,從軍方、政客到具體實施轟炸的士兵,都陷入了各自的考量和糾結。

《天空之眼》劇照。
這部電影的視角設定極具象征意味。這次襲擊,根本沒有正面沖突和廝殺,一切一直處于“上帝視角”之下。英國的情報機構利用各種高科技的偵察手段以及衛星和無人機系統,在天空中監控著一切,正是這種高高在上、可以洞察一切的視角,讓原本代表著正義一方的人們真的像上帝一樣注視到了世間百態——不只是作為敵人的恐怖分子,還有作為犧牲者的平民和兒童。上帝視角讓死傷不再是一個符號和概念,而變成了具體的、鮮活的人。
那些士兵可以看清女孩堅毅的、苦中作樂的生活細節,這對于他們內心的波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除了視角,空間的設定也布滿心機。所有做決定的人們,無論軍方還是政客,都坐在遠離戰爭現場的房間里遙控指揮,這是現代化戰爭的常態,也恰巧形成了一種有趣又殘忍的隱喻。一群主持著外交內政的中年男女,坐在鑲嵌著桃木護墻板、懸掛著枝形吊燈的房間里,喝著咖啡,吃著曲奇,看著大屏幕上對恐怖分子的實時監控,一切都顯得無比詭異,他們正在“觀看”一個生死攸關的場景。他們是抽離的,但同時又是他們在決定著那一群人的生死。這一切荒誕又令人唏噓。
《天空之眼》從始至終,都只運用了幾塊屏幕和幾個房間去講述一切,沒有大開大合的動作,只通過凝重的表情和緊繃的身體語言塑造情緒。而正是這最簡潔的場景卻延展出了最深刻的道德問題。
一邊是無辜的小女孩,另一邊是房間內正在試穿自殺式爆炸背心的恐怖分子,到底如何抉擇。這不可避免地讓人們想起著名的哈佛公開課中有關道德的爭辯。一列火車開來,在撞死一個人和三個人之間,到底選擇不選擇扳下道岔?
恐怖分子造成的威脅可能是殺死數百上千人,但那個場景是當下看不到的,而那個孩子無辜的犧牲卻清晰地呈現在眼前,在這種情形之下,人類的理性有時無法跨越道德和情感的關口。而更殘忍和冰冷的一幕發生在高官云集的指揮部中,他們一邊盯著大屏幕,一邊說,“如果讓恐怖分子出去實施了自殺式爆炸,我們就贏得了人心,但如果我們因為附帶傷害而炸死了那個小女孩,那他們就能獲得了談資。”也就是說,在某一個瞬間,他們曾經想過,放任恐怖分子實施行動,以換取對自己有利的輿論環境。而這樣,自己還能賺取道德加分。
不可否認,在這場戰爭中,致力于打擊恐怖分子的這群人是正義的一方。但當他們把別人的生命當做籌碼進行計算的時候,是否也讓人們感覺到了另外一種意義上的恐懼呢?
《天空之眼》設置的幾個層面非常耐人尋味,操控導彈的士兵、軍方高層、文官政客,以及遠在他國訪問的國家元首和作為盟友的美國高層。這是一個由低到高的遞進關系,也是以戰場為圓心,由近及遠的距離。你會發現,越是切近真實戰場的人,道德感就越強,人性濃度越高,而越到外圍,道德與人性就逐漸稀薄。指揮部中的人們,算計的是政治上的得失,而當電話打到遠在他國訪問的最高層,他們根本不把這一切當做需要審慎考慮的事。電影故意顯示出了戲謔又殘忍的場景,權力最高層中的人在馬桶上、在球案邊,隨意決定了他人的生死。
恐怖分子被消滅了,用了兩顆導彈,小女孩作為“附帶傷害”也沒能逃過這一劫。從理性上講,誰都知道這筆賬要算到恐怖分子頭上,但這一切會永遠壓在那兩個按下導彈發射按鈕的年輕士兵身上。那些掌握權勢的高層最終會把這次襲擊濃縮為一次勝利的演講,然后將之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