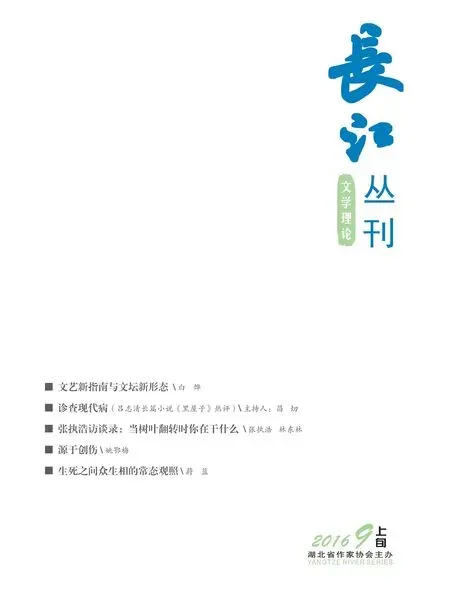參悟生死化蝶成蛹——略論非虛構文學《重癥監護室》
王均江
參悟生死化蝶成蛹——略論非虛構文學《重癥監護室》
王均江
作家就像一個狙擊手,他選定的題材是他的狙擊位,他用的體裁則是他手中的狙擊槍。他的成績就在于,他的狙擊位選擇是否有利,他是否完全發揮了槍械的性能,以及他最終斬獲的敵人數目。
但這個比喻用于周芳和她的《重癥監護室》,似有一種嚴重的違和感。她那里歌頌生命,我卻在這里大談殺戮。然任何比擬總是有其局限,取其相通之處可也。
我們先檢視一下狙擊手周芳:她選定重癥監護室這個生死場作為狙擊位,狙擊槍為非虛構文學,她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是:“我渴望著成為生死邊緣里,和病人、和家屬,和醫護人員站在一起的那個人”,因為,“活著,如此司空見慣,我麻木了”,她渴望在盡可能近的距離之內,經歷生死。這個殺手不太冷。
為了配合非虛構文體,她使用的是日記加補記的方式。日記側重現場描述病房內的所見所聞,補記側重她內心的感受及與之相關的在病房外發生的事情。這就同時在讀者面前展開了兩個世界,一個生死懸于一線的異常世界,一個常態的日常世界。沒有活人經歷過死亡,也很少人親身體驗過死神惡狠狠的敲詐勒索與威脅。作者決定充當翻越這兩個世界的使者,替包括她自己在內的活在日常世界里的人去嘗試那種痛苦與撕裂。
首先要說到是作者極強的描述能力。詳細記錄汪東坤開顱手術的文字幾乎超出了一般人的承受能力。從醫生用紅色記號筆畫手術線,到切頭皮,翻皮瓣,直到在負壓吸引器的作用下露出白生生的顱骨,“電鋸哧哧地響,一個小拇指粗的洞鉆出。二個洞,三個洞,四個洞。血濺到手術單上……”,這樣的文字直接引發生理反應,簡直讓人窒息或嘔吐,讓我們切身地感受到什么叫血肉之軀,什么叫人的脆弱!
作者非常善于提煉日常生活中的詩意。在重癥監護室這樣一個背景之下,當眨眨眼晴動動手指暢快地呼吸一口氣都成為一種奢侈的時候,處于日常世界里的人就算是身在天堂了。
這里是對生命進行現象學反原的最好場所,把生命還原到這個境地,日常生活就顯現出盎然蓬勃的生機與詩情。作者用她敏感的心,很好地抓住了這些詩意的瞬間。比如刻畫那個從工地八樓摔下來,肝脾肺膀胱都摔破了、身上需要同時插著十根引流管的小伙子,二十多天過后,他終于醒過來,一根根管子拆掉,終于可以自己主動吃一點食物了。“一床劉浩云一邊大口地吞咽著面條,一邊含糊不清地在叫著快一點,快一點。他用手焦急地指向嘴巴,示意我喂快一點……這碗清水面條出現在劉浩云的口腔里,就像愛情出現在他的青春里,再合適不過、再美滿不過了。它總共只有一個意味:吃吧,活下來。”這碗面條簡直就像海德格爾在他的名篇《藝術作品的本源》中描繪的構筑神廟的石頭,在神廟建筑中,石頭的承重、不朽、光澤等等特性才能充分顯露出來,而在這里,一碗少鹽無油無任何佐料的面條的價值才能得以充分顯現,食物與水才有了它們原本的品性,甚至足以讓人敬畏:“從此,我不敢再小看一粒糧食,甚至粘在棉簽上的一滴水,它們就是這世界最本初的樣子。”
再如,作者對聲音的還原:“這房間里從早到晚都不缺少聲音。營養泵的聲音,輸液泵的聲音,微量元素泵的聲音,氣墊床的充氣聲,呼吸機聲,氧氣瓶聲,空調聲,對流層聲音。在這些聲音里,我傾聽著心跳聲,呼吸聲,叫罵聲。這一切,都來源于活著的人。劉小萌,如果這一刻你朗讀課文,一定是世間最美的聲音。”劉小萌是一個患重癥心肌炎加惡性心律失常的高二女生,學習成績很好的乖乖女,她妹妹小時候患與她類似的病已經夭折了……作者作為母親,同時作為醫院里暫時的醫護人員,對這個孩子極度不舍,她自愿加班來病房守夜,在極度擔憂與焦灼中傾聽著病房里的各種嘈雜,耳中幻聽一樣想到了這個病危女孩的讀書聲,真的,在那一刻,世界上怎么可能還有什么聲音比它更美?書中經常溢出的這種充滿愛與真的質樸詩情,照亮了我們蒼白而脆弱的生命。
作者寫重癥監護室,卻不局限于重癥監護室,而是以重癥監護室為 望孔,把筆觸伸到了生活世界的各個角落,寫出許多動人的故事,記載了很多令人難忘的人物。在病人中,那個一輩子強勢的鐵人張爹爹與到老依舊沉醉于與老伴你儂我儂的張玉芬婆婆,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者到老了才發現生命中還有個比他更強的對手叫病魔,它讓他丟盡了臉,然而張爹爹卻毅然決然用兩次自殺來維護自己的尊嚴。鑒于第一次喝藥被搶救過來的教訓,第二次他采用了先喝藥后投河雙保險的措施,投河前又用繩子把自己拴在樹上以免兒子找不到尸體而在鄉鄰面前貽羞,這份自尊、這份體貼令人心痛到內傷!
但總體來說,多數病人在重癥監護室基本上就是手拿黑色鐮刀的死神待收割的莊稼,自我表現能力有限,而監護室外的病人家屬才占據著更大的表演舞臺。說到這里,我不得不提到全書的一個華彩樂章,即對劉菊秀家屬們的描繪。得知劉菊秀去世的消息,一家人哭成一團。從劉菊秀的大姐、二妹到她的挺著大肚子的女兒,再到她伉儷情深、悲痛欲絕的老公,強自隱忍終于泣不成聲的年邁高堂,都有極精微動情的細節描寫,作者可謂賺足了眼淚。但相對來說,作家想賺眼淚總還是容易的,讓人吃驚的是篇末的補記:
“3天后,10月25日早上,我在外科大樓見到了劉菊秀的愛人,他提著兩個開水瓶,匆匆忙忙從外面走進來。他一邊走一邊打電話,生了,生了。大人小孩都好。七斤八兩。他聲音響亮,滿臉帶笑。這個既當外公又當外婆的男人臉上,幾乎看不到三天前的陰影。”
這段不長的補記簡直字字珠璣。它讓我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說《縣城醫生》。小說里,醫生給獵人治完病,莫名其妙地講起了他一生最難忘的一段生死戀情,極其沉痛,極其動情。講完了,卻又若無其事地纏著獵人打牌,最后贏了幾個小錢,開開心心地回家了。
是的,愛又如何,愛得死去活來又能怎樣?其后,還不是得柴米油鹽平平淡淡地,該怎樣就怎樣過日子。正如作者所說:“這世上,從來沒有停止過壘上新生的墳墓,也從來沒有停止過生產出新的人。生的生,死的死,各行其是。一代過去,一代又來。”這可謂是醇厚而深刻的生命感悟,不到一定年歲是永遠也無法理解的。因而,這一篇日記加補記雖只有短短四面,僅就表達的意蘊而言,甚至可以說抵得上屠格涅夫的那個短篇小說了。
人生體悟之外,作者還寫到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令人感慨,發人深思。王佳璐生病前是當紅美女,人長得漂亮職業也不錯,傲嬌得給老公戴上一頂又一頂綠帽子,后與老公離婚。可惜好景不長,得了重癥肌無力,連喘氣都成問題了。情人們一時作鳥獸散。前老公卻既不能原諒她,又不能眼睜睜看她生病不管,就以前老公的身份瞞著家里人打工掙錢給她治病,一堅持就是十幾年,只是不肯復婚。人間竟也有這樣的情義!
王四紅也是,老公成了植物人之后,她給自己改名王美麗,給老公改名高興,以病房為家,要美麗著高高興興地過這種日子。當然她也有她的淚水。淚水流過了,還是要過日子,因為日子終比淚水長。

《縣城醫生》
有有情就有無情。趙老太出車禍后被子女們遺棄在病房里。鐵人張的二兒子比起愛老父親,更愛惜他自己的子女和錢財。
這些道德與情義是亙古的論題,是古典文學的意義核心。但好的作家尤其是當代作家,不會僅僅糾纏于這個維度。當代作家必須看到社會問題的歷史性層面,乃至人性的哲學層面上的問題。
王桂香老人一家赤貧,病有治好的希望,但拿不出重癥監護室對他們來說的天價費用(每天3000元),猶豫再三,最后也只好眼睜崢地拔掉呼吸機上的管子去死。“姆媽,姆媽,我們沒錢了,沒錢。女兒趴在床沿上嚎啕大哭。”“過年了,我給你墳頭上燒蠻多錢。老伴低聲說道。”作者不動聲色地描繪了一場人生慘劇。
與此相對應,離休干部晏楚林已不需要住重癥監護室了,但他的子女們因不愿意花自己的錢請護工照顧老父親,硬是死賴著不肯搬離重癥監護室,反正花多少錢都是國家買單。更有甚者,有子女為了多拿一個月的老父的高工資,竟賄賂醫生無論如何都要讓老父活到下個月的第一天。
還有,住福利院的傻子被火嚴重燒傷,是否值得花100萬把他救活?這可能是個無解的哲學問題。但現實的版本是,家屬與福利院達成協議,剝奪了傻子的被救治權。
作者也記錄了宗教在我們這個國家重新興起的跡象。植物人汪東坤的老母親在基督教中得到了她需要的安息。除了神,誰能安慰她呢?
相對于病人與家屬,對醫護人員的描繪就遜色多了。醫生“一臉佛相,一股祥和之氣”,每個人都被要求散發出“祥和寧靜的光”。還有墻上的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說實話,如果作者不寫那些醫生被患者監控,患者要求醫護人員出示用過了的裝昂貴藥物的小藥瓶這些揭示緊張的醫患關系的細節,我會認不出這是在我們自己國家的醫院。我這么說有些刻薄了,我也不是不信醫生會有如此修養,但我知道這不可能是作者所見聞的醫生形象的全部。我也理解作者不能或不肯說出全部真相的原因:她受到了非虛構文體的限制。
非虛構文學據說是以“事實”、“親歷”、“誠實原則”等為特征的一種文體。但我認為,虛構與非虛構文學的最大差異,在于作者與讀者的關系不同。對于虛構文學來說,讀者面對的是作者虛構的世界,作者隱藏在這個世界后面;而對于非虛構來說,讀者直接面對作者感受并描述出來的世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就是讀者直接面對作者的心靈世界,作者躲藏的空間與余地都更小,他(她)不得不更加小心謹慎。這一點在周芳的書中表現得非常明顯。
書的開篇已經按照非虛構文學的要求,標明地點是孝感中心醫院,作者是醫院系統內部的人。這實際上已經注定了作者不可能放開手腳隨心所欲地去說出全部真實了,尤其是關于院方的真實。況且作者還是一個那么敏感,那么懂規矩的人,“在這里,我只是一個外來者,我的一舉一動都得聽醫生和護士的,我不能給他們制造任何麻煩。”作者就連差點被車撞死發幾句牢騷,也會馬上反省到:“這有攻擊車輛保險的嫌疑。”作者和我一樣,被教化得多自覺多老實多知道規矩。我們不該說的就堅決不說。
最后還是回到作品本身好了。作品以佛教的《無常經》開頭,以基督教創世紀式的一切充滿活力的被創造物都是好的結尾,中間引用彌爾頓滿懷悲憫的詩歌前后呼應,事實上將全書置于一個超越性維度去思考生活與生命,視域寬廣,筆力遒勁,貫穿全書。很自然地,作者在經歷了這些人生的生死之后,悟到了不僅在人前光鮮亮麗、翩翩起舞的蝶是美麗的,那在黑暗污穢中蟄伏的蛹更加偉大而值得贊美。作者不是化蛹為蝶,而是化蝶成蛹了,對人性的挖掘通向了更加深邃那個或許在世俗眼光中不潔不凈、又說不清道不明的層面。
這是作者思想的沉潛與升華。感謝作者,我作為讀者,也有幸分享了這生命智慧的苦杯。
另外,文學從虛構到非虛構,是不是也是一種化蝶為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