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近務(wù)工提升了農(nóng)民工城鎮(zhèn)化意愿嗎——基于貴陽(yáng)市的調(diào)查
錢(qián)龍,錢(qián)文榮,洪名勇
(1. 浙江大學(xué)管理學(xué)院,浙江 杭州 310058;2. 湖州師范學(xué)院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院,浙江 湖州 313000;3. 貴州大學(xué)管理學(xué)院,貴州 貴陽(yáng) 550025)
就近務(wù)工提升了農(nóng)民工城鎮(zhèn)化意愿嗎——基于貴陽(yáng)市的調(diào)查
錢(qián)龍1,2,錢(qián)文榮1,洪名勇3*
(1. 浙江大學(xué)管理學(xué)院,浙江 杭州 310058;2. 湖州師范學(xué)院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院,浙江 湖州 313000;3. 貴州大學(xué)管理學(xué)院,貴州 貴陽(yáng) 550025)
“三個(gè)1億人”提倡的就近城鎮(zhèn)化已經(jīng)上升為國(guó)家戰(zhàn)略,但是否可行取決于農(nóng)民工是否具備就近城鎮(zhèn)化意愿。本文基于務(wù)工距離視角對(duì)此進(jìn)行了研究,并以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貴州省貴陽(yáng)市1 026份農(nóng)民工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為依據(jù),使用Oprobit模型和PSM模型,分析了務(wù)工距離對(duì)農(nóng)民工留城意愿的影響。結(jié)果表明:務(wù)工距離顯著影響個(gè)體的留城意愿,當(dāng)務(wù)工距離越遠(yuǎn)時(shí),農(nóng)民工的留城意愿相應(yīng)越低,這一結(jié)論在克服選擇性偏差后依然成立。務(wù)工距離也對(duì)農(nóng)民工的家庭遷移行為產(chǎn)生顯著負(fù)向影響,務(wù)工距離越遠(yuǎn)農(nóng)民工越不大可能實(shí)現(xiàn)家庭式遷移和城市穩(wěn)定定居。研究闡明了支持就近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國(guó)家戰(zhàn)略。在此基礎(chǔ)之上,提出了尊重農(nóng)民工主觀留城意愿、重點(diǎn)關(guān)注原戶籍地與打工城市較近的農(nóng)民工和吸引勞動(dòng)力就近務(wù)工的政策建議。
農(nóng)民工;城鎮(zhèn)化;留城意愿;家庭式遷移;務(wù)工距離
錢(qián)龍, 錢(qián)文榮, 洪名勇. 就近務(wù)工提升了農(nóng)民工城鎮(zhèn)化意愿嗎——基于貴陽(yáng)市的調(diào)查[J]. 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研究, 2016, 37(1): 102-109.
Qian L, Qian W R, Hong M Y. Can working in the neighborhood enhance the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A case study of Guiyang[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6, 37(1): 102-109.
全球金融危機(jī)爆發(fā)以來(lái),中國(guó)外向型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模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由投資和出口驅(qū)動(dòng)向出口、投資和消費(fèi)三駕馬車(chē)協(xié)調(diào)推進(jìn),對(duì)提高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質(zhì)量和推進(jìn)可持續(xù)發(fā)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在此背景之下,城鎮(zhèn)化被寄予厚望,被視為解決“三農(nóng)”問(wèn)題、帶動(dòng)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和擴(kuò)大內(nèi)需的新動(dòng)力。
國(guó)家“十二五”規(guī)劃提出,“要把符合落戶條件的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逐步轉(zhuǎn)為城鎮(zhèn)居民”,通過(guò)城鎮(zhèn)化水平提升拉動(dòng)國(guó)內(nèi)需求。這一判斷得到國(guó)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課題組[1]關(guān)于農(nóng)民工市民化與擴(kuò)大內(nèi)需研究的支持,即每年成功轉(zhuǎn)換農(nóng)民工1 000萬(wàn),可使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速度提高約1個(gè)百分點(diǎn)。但是,基于戶籍制度的歧視使得農(nóng)民工群體無(wú)法享受市民待遇,農(nóng)民工在住房、就業(yè)、子女教育和社會(huì)保障等方面均處于劣勢(shì)地位[2]。這既降低了農(nóng)民工的消費(fèi)能力和意愿,也加劇了城鄉(xiāng)居民心理鴻溝,影響社會(huì)穩(wěn)定。因此,加快推進(jìn)農(nóng)民工群體融入城市,實(shí)現(xiàn)“半城鎮(zhèn)化”向“真正城鎮(zhèn)化”的轉(zhuǎn)變,不僅有利于提振內(nèi)需,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平穩(wěn)快速增長(zhǎng);而且對(duì)中國(guó)二元社會(huì)向一元社會(huì)轉(zhuǎn)變,杜絕城市新貧民階層的出現(xiàn)有著重要作用。
除了繼續(xù)在宏觀政策和制度層面予以支持外,必須指出的是農(nóng)民工城鎮(zhèn)化應(yīng)當(dāng)是自主的城鎮(zhèn)化,是基于農(nóng)民工自身意愿的主動(dòng)選擇[3]。只有基于農(nóng)民工真實(shí)意愿的城鎮(zhèn)化,才是有生命力的城鎮(zhèn)化和可持續(xù)的城鎮(zhèn)化,因而需要重點(diǎn)關(guān)注農(nóng)民工自身的留城意愿。那么哪些因素會(huì)影響到農(nóng)民工的留城意愿呢?學(xué)界做出了諸多探索,并證實(shí)個(gè)體特征、家庭特征、工作特征、社會(huì)特征、制度特征、心理特征等均會(huì)對(duì)農(nóng)民工的留城意愿產(chǎn)生影響[4-8],這充分彰顯了農(nóng)民工留城的復(fù)雜性。然而,通過(guò)對(duì)文獻(xiàn)的梳理,仍然發(fā)現(xiàn)既有成果存在以下三點(diǎn)可以商榷的地方。
首先,諸多研究?jī)H僅將農(nóng)民工留城意愿區(qū)分為“留”或“走”兩種狀態(tài),忽略了處于“不清楚”這種中間狀態(tài)人群的考察[9]。事實(shí)上,除了上述兩種明確狀態(tài)外,有相當(dāng)一部分農(nóng)民工在留或走之間徘徊[10-11]。這部分人群也應(yīng)當(dāng)引起重視。其次,既往研究多多忽略了樣本可能的選擇性偏差問(wèn)題[12]。正如Heckman和Li[13]所言,樣本的偏差會(huì)直接導(dǎo)致回歸結(jié)果有偏,因而可信度不高。第三,就近城鎮(zhèn)化的相關(guān)理論研究亟需補(bǔ)充和完善。《2014政府工作報(bào)告》提出了“三個(gè)1億人”的構(gòu)想,其中關(guān)于引導(dǎo)“ 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qū)就近城鎮(zhèn)化”,這意味著農(nóng)民工在中西部地區(qū)就近城鎮(zhèn)化問(wèn)題已經(jīng)上升到國(guó)家戰(zhàn)略層面。但關(guān)于就近城鎮(zhèn)化的理論及實(shí)證研究十分匱乏,亟需學(xué)界展開(kāi)深入論證。
本文則是基于以上三點(diǎn)不足做出改進(jìn)。首先,將農(nóng)民工區(qū)分為留、走和中間狀態(tài)三類(lèi)。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除常規(guī)方法外,為糾正可能的樣本選擇偏差及其引致的內(nèi)生性問(wèn)題,本文還使用傾向得分法(propensity score model, PSM)予以分析。再次,本文試圖通過(guò)對(duì)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貴州省貴陽(yáng)市1 026名農(nóng)民工的調(diào)查,從務(wù)工(遷移)距離視角對(duì)農(nóng)民工就近城鎮(zhèn)化意愿進(jìn)行了分析,初步對(duì)就近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的可能性進(jìn)行了探討,從而為國(guó)家城鎮(zhèn)化路徑的戰(zhàn)略選擇提供決策參考。
1 理論假設(shè)
距離對(duì)人口遷移的影響是重要的[14],這一點(diǎn)為經(jīng)濟(jì)地理學(xué)所強(qiáng)調(diào)。早在19世紀(jì),基于歐洲人口遷移數(shù)據(jù),Ravenstein[15]就發(fā)現(xiàn)人口多傾向于短距離的遷移,而長(zhǎng)距離多向中心大城市遷移,且距離越遠(yuǎn)遷移人口越少。Zipf[16]首次把萬(wàn)有引力定律引入推拉模型,并應(yīng)用于人口遷移研究,指出兩地之間的人口遷移與遷移距離成反比,與兩地人口規(guī)模成正比。然而,西方移民的遷移行為往往與定居行為相伴而生,二者并沒(méi)有明顯的階段性區(qū)別[17]。但城鄉(xiāng)二元體制的存在,使得中國(guó)農(nóng)民工面臨著“工作性遷移—定居性遷移”的雙層決策。因而,西方理論在中國(guó)情景下是否發(fā)揮相同作用,學(xué)界仍然存在爭(zhēng)論。
有研究表明,農(nóng)民工定居決策與工作決策并不完全一致,是留在打工城市,還是回到家鄉(xiāng)城鎮(zhèn)亦或選擇其他城市均存在一定比例[11],遷移距離并不影響農(nóng)民工留城意愿。但也有研究發(fā)現(xiàn),工作遷移作為定居決策的前一階段,對(duì)定居決策有著較大的影響[7],存在遷移距離越遠(yuǎn),農(nóng)民工越不太可能定居城市的規(guī)律。整體而言,既有研究均未詳細(xì)闡述其影響機(jī)制,只是將遷移距離作為一個(gè)控制性因素予以考慮。參照國(guó)外遷移理論,并考慮到中國(guó)實(shí)際,我們認(rèn)為遷移距離可能通過(guò)下述四種路徑影響農(nóng)民工留城意愿。
首先,距離增加帶來(lái)了交通成本的上升,增加長(zhǎng)途遷移的負(fù)擔(dān)。如Mamermesh對(duì)美國(guó)國(guó)內(nèi)移民的研究表明,距離每增加1 mi,只有當(dāng)遷移者的預(yù)期收入增加5美元時(shí)才能補(bǔ)償[18]。就農(nóng)民工而言,在其完全定居城市之前,對(duì)農(nóng)村親人的牽掛和土地的眷念,使得農(nóng)民工在城鄉(xiāng)之間來(lái)回奔波。候鳥(niǎo)式的遷移透支了農(nóng)民工大量金錢(qián)和精力,為了方便照顧家庭,減少交通費(fèi)用,大量中年農(nóng)民工只能選擇就近就業(yè)務(wù)工或者返鄉(xiāng)務(wù)農(nóng)[17]。因而,長(zhǎng)途遷移可能對(duì)農(nóng)民工的留城意愿產(chǎn)生負(fù)向影響。
其次,距離的增加導(dǎo)致了遷移者心理成本上升。更遠(yuǎn)的距離意味著更加陌生的環(huán)境,以及與家人朋友的疏遠(yuǎn)[14],且適應(yīng)新的環(huán)境也需要花費(fèi)更多的成本。多項(xiàng)研究也表明,空間不僅是個(gè)地理學(xué)概念,而且還是一個(gè)被認(rèn)可的“心理空間”或“意象空間”。地理位置越接近,流出地與流入地在語(yǔ)言、文化、飲食、情感方面更加趨同[5],農(nóng)民工也更容易融入打工城市。
第三,遷移距離的增加使得原有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強(qiáng)度降低,增加了遷移的風(fēng)險(xiǎn)性。社會(huì)資本有著一定的區(qū)域性,一定區(qū)域的人們相互交往,互惠互利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對(duì)稱(chēng)和機(jī)會(huì)主義,增加社會(huì)支持度和個(gè)體抗風(fēng)險(xiǎn)能力[19]。資本存量的相對(duì)固定性使得移民一旦選擇遷出,就會(huì)失去這些社會(huì)資本帶來(lái)的保障效益。社會(huì)學(xué)家將其命名為“拖網(wǎng)效應(yīng)”,即遷移距離越遠(yuǎn),社會(huì)資本貶值越快。Tolley[20]證實(shí)了這一效應(yīng)的存在,發(fā)現(xiàn)短距離流動(dòng)(100 mi內(nèi))時(shí),原有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尚能維持。當(dāng)遷移距離達(dá)到100-1 000 mi時(shí),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就可能斷裂,但由于范圍內(nèi)環(huán)境相似性,新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能夠很快建立起來(lái)。但當(dāng)遷移者進(jìn)行遠(yuǎn)距離遷移(1 000 mi以上)時(shí),遷移者就進(jìn)入了一個(gè)完全陌生的環(huán)境,原有社會(huì)資本基本失去作用。社會(huì)資本具有緩沖風(fēng)險(xiǎn)的作用,為農(nóng)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提供了基本的支撐。同時(shí),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有利于強(qiáng)化農(nóng)民工城市認(rèn)同,促進(jìn)其定居城市意愿[3]。隨著遷移距離的增加,農(nóng)民工可利用的社會(huì)資本越少,放棄原有社會(huì)資本的機(jī)會(huì)成本越大,基于成本——收益的考慮,農(nóng)民工越不大可能選擇留城。
第四,由于戶籍制度實(shí)行屬地化管理,與本地農(nóng)民工相比,外地農(nóng)民工跨區(qū)域遷移可能面臨更多的制度和政策阻力。尤其是分稅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財(cái)權(quán)減少,地方政府承擔(dān)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壓力更大,這導(dǎo)致地方缺乏推動(dòng)外地農(nóng)民工市民化的動(dòng)力,本屬于“公民權(quán)”的權(quán)益也日漸“本地化”。為防止城市過(guò)度膨脹和公共資源不足,保護(hù)地區(qū)居民利益,很多地方政府設(shè)置了一系列政策來(lái)限制外來(lái)人口流入[4]。從這個(gè)視角來(lái)看,外地農(nóng)民工因政策阻力較強(qiáng),留下定居的意愿相對(duì)較低。
基于上述分析,并考慮到在中國(guó)情景下使用務(wù)工距離更為準(zhǔn)確,進(jìn)而提出農(nóng)民工務(wù)工距離越遠(yuǎn),其留在打工城市定居的意愿越低。
2 研究方法
2.1 數(shù)據(jù)來(lái)源
貴陽(yáng)是貴州省會(huì),位于貴州中部,是全省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中心。2013年全省人均生產(chǎn)總值為22 922元,而同期貴陽(yáng)市達(dá)到45 390元,接近全省平均水平的2倍。貴陽(yáng)市也是全省農(nóng)民工最多的城市,2013年貴陽(yáng)市總?cè)丝跀?shù)為468.4萬(wàn)人,其中外來(lái)農(nóng)民工達(dá)到120萬(wàn),龐大的農(nóng)民工基數(shù)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樣本。本文數(shù)據(jù)來(lái)源于2011年的一次農(nóng)民工問(wèn)卷調(diào)查,此次調(diào)查采用配額抽樣和隨機(jī)抽樣相結(jié)合的方式,對(duì)貴陽(yáng)市下轄的六個(gè)區(qū)進(jìn)行了問(wèn)卷調(diào)研。此次調(diào)查共發(fā)放問(wèn)卷1 063份,收回有效問(wèn)卷1 026份,樣本有效率為96.52%。
調(diào)研對(duì)象中,有男性520人,女性506人,其中17%的未婚。從來(lái)源地來(lái)看,省內(nèi)農(nóng)民工比例達(dá)到3/4左右,其中貴陽(yáng)下轄縣市比例為12.3%,貴州其他地市比例占62.2%。農(nóng)民工居住呈現(xiàn)穩(wěn)定性特征,接近半數(shù)農(nóng)民工在貴陽(yáng)定居時(shí)間超過(guò)5年。從遷移模式來(lái)看,有36.45%的農(nóng)民工舉家遷移到貴陽(yáng)。但整體上,農(nóng)民工選擇留城的比例仍較低,不足13%農(nóng)民工愿意選擇定居下來(lái),而表示不清楚的農(nóng)民工比例為29.5%,表明確實(shí)存在相當(dāng)一部分農(nóng)民工在留或走之間徘徊不定。
2.2 變量設(shè)置
因涉及務(wù)工距離和就近城鎮(zhèn)化問(wèn)題,留城意愿中城市選擇就尤為重要。調(diào)研員被要求向調(diào)查者說(shuō)明這一情況,請(qǐng)其回答定居貴陽(yáng)的意愿。務(wù)工距離是本文重要的解釋變量,通常采用兩種方式來(lái)測(cè)量。一是家庭來(lái)源地,二是老家離務(wù)工城市的距離。考慮到戶籍制度影響和貴陽(yáng)市在全省的中心地理位置,因而選定第一種方式,并設(shè)置本市下轄縣、本省外市和外省三個(gè)層次[21]。遵循文獻(xiàn)的傳統(tǒng),引入相關(guān)控制變量。考慮到引入頻率和實(shí)際效果,共引入5個(gè)維度9個(gè)控制變量。包括個(gè)體特征、住房特征、工作特征、社會(huì)特征和戀土特征。各變量設(shè)置與說(shuō)明見(jiàn)表1。
2.3 模型選擇
請(qǐng)?jiān)L談?wù)哌x擇“會(huì)=0、不清楚=1和不會(huì)=2”三個(gè)選項(xiàng)之一,來(lái)測(cè)度其留城意愿強(qiáng)弱。從脫離農(nóng)業(yè)決心來(lái)看,上述選項(xiàng)存在著遞減的關(guān)系,為有序排列變量[22]。因而,選擇Oprobit模型更加適合。

式中:LG為留城意愿,Dis為遷移距離,X為影響農(nóng)民工留城意愿的個(gè)體特征、工作特征等5個(gè)維度9個(gè)變量的向量組,α、β為相應(yīng)的影響系數(shù)。ε為擾動(dòng)項(xiàng),服從標(biāo)準(zhǔn)正態(tài)分布,且與X相獨(dú)立。

表1 自變量描述說(shuō)明Table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式中:t0<t1<t2為待估常數(shù),被稱(chēng)為切點(diǎn)。LG對(duì)X的條件概率為:

然而,基于微觀調(diào)研的數(shù)據(jù)分析,常常面臨樣本選擇性偏差及其引至的內(nèi)生性問(wèn)題,近年來(lái)傾向得分法(PSM)被開(kāi)發(fā)出來(lái)以應(yīng)對(duì)這一問(wèn)題[12]。PSM的基本思想是:評(píng)估某個(gè)具體因素對(duì)個(gè)體的影響時(shí),將整體區(qū)分為干預(yù)組和控制組。通過(guò)一定的計(jì)算方法,剔除其他因素對(duì)關(guān)鍵變量的影響,將諸多維度合成為一個(gè)綜合指標(biāo)——傾向得分值(PS)。當(dāng)干預(yù)組和控制組的PS值相同時(shí),意味著兩者有著基本相同的特征[23]。在此基礎(chǔ)之上最小化樣本之間的偏差,從而測(cè)度出特定因素的“純粹干預(yù)效應(yīng)”(ATT)。
就本研究而言,是否就近務(wù)工可能并不是外生變量,務(wù)工距離的遠(yuǎn)或近也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如高技能相對(duì)低技能、新生代相對(duì)老一代更可能選擇長(zhǎng)距離遷移,因而減少由距離造成的樣本選擇性偏差和相應(yīng)內(nèi)生性干擾十分關(guān)鍵。首先將農(nóng)民工群體區(qū)分為干預(yù)組和控制組兩個(gè)組。與省內(nèi)遷移相比,跨省遷移距離更遠(yuǎn)、風(fēng)險(xiǎn)更大,是否跨省遷徙常常被作為距離遠(yuǎn)近的指示變量[24]。因而,令“省內(nèi)遷移=0(控制組),省際遷移=1(干預(yù)組)”,并使用PSM方法解決遷移距離的內(nèi)生性,并進(jìn)一步驗(yàn)證遷移距離對(duì)農(nóng)民工留城意愿的影響。
傾向得分PS被定義為,給定資源稟賦(Z)下,個(gè)體進(jìn)入干預(yù)組的概率:

式中:Dis=1表示個(gè)體進(jìn)入干預(yù)組,否則Dis=0。對(duì)任意個(gè)體i而言,省際遷移對(duì)其留城意愿的平均影響ATT為:

式中:Yi1和Yi0分別表示跨省遷移和省內(nèi)遷移農(nóng)民工的留城意愿強(qiáng)度,資源稟賦Zi包括其性別、婚姻、教育程度等其他因素的特征。
3 結(jié)果與分析
3.1 務(wù)工距離與留城意愿分析
為保障回歸結(jié)果可信性,按照影響因素的維度逐一添加進(jìn)行了多次擬合回歸(表2)。模型一中只引入個(gè)體特征和務(wù)工距離,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礎(chǔ)上增加了住房特征,模型三進(jìn)一步增加工作特征,模型四增加了社會(huì)特征,模型五則增加了戀土特征。對(duì)比模型一至模型五,不難發(fā)現(xiàn)遷移距離均通過(guò)了1%的顯著性檢驗(yàn),且作用方向不變,這說(shuō)明模型有著很好的穩(wěn)健性。從影響方向來(lái)看,務(wù)工距離確實(shí)能夠顯著的影響農(nóng)民工的留城意愿。且務(wù)工距離越遠(yuǎn),農(nóng)民工越不可能選擇定居在該城市,研究假說(shuō)得到證實(shí)。
控制變量方面,婚姻、教育程度、人均居住面積、收入對(duì)數(shù)和居城年限五個(gè)變量通過(guò)了顯著性檢驗(yàn),且作用方向保持一致,說(shuō)明這些因素對(duì)留城意愿的影響十分穩(wěn)健。具體而言,婚姻對(duì)農(nóng)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響顯著,表現(xiàn)為已婚農(nóng)民工有著較強(qiáng)的留城意愿。這可能是因?yàn)楸敬窝芯繉⒘舫且庠傅摹俺恰毕拗茷橘F陽(yáng),而多數(shù)未婚農(nóng)民工則表示更愿意去中東部地區(qū)發(fā)展;而已婚的農(nóng)民工由于家庭原因,去更遠(yuǎn)的城市定居意愿較低。這一點(diǎn)也可以從農(nóng)民工年齡結(jié)構(gòu)顯示出來(lái),樣本中只有37%為出生于80后的新生代,這與其他研究相比,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占比明顯偏低。在1%顯著性水平下,教育程度通過(guò)檢驗(yàn),證實(shí)了教育程度越高,農(nóng)民工越可能選擇留城定居。這與多數(shù)研究保持一致,即個(gè)體人力資本水平越高,學(xué)習(xí)能力更強(qiáng),對(duì)工作和城市生活的適應(yīng)能力也越強(qiáng)[25]。另一方面,較高人力資本能夠獲取更高收入,使得農(nóng)民工能夠在城市生存和發(fā)展。住房情況是影響農(nóng)民工留城意愿一個(gè)重要因素[5],住房質(zhì)量和人均住房空間對(duì)農(nóng)民工的生活質(zhì)量有較大影響。結(jié)果表明人均住房面積越大,農(nóng)民工越可能選擇留下。
課后交流,同事總結(jié)說(shuō):“楊老師,你的這堂課,有朗讀、靜思、討論、爭(zhēng)鳴、共識(shí)、多元評(píng)價(jià),充滿學(xué)科特點(diǎn)、人文元素且智慧啟迪。你說(shuō)的話少,卻又畫(huà)龍點(diǎn)睛。滿堂課沒(méi)有花樣,卻有氛圍。讓人感覺(jué)意猶未盡,聽(tīng)了還想聽(tīng)。”
追求收入增長(zhǎng)是農(nóng)民工進(jìn)入城市的重要?jiǎng)恿Γ鋵?shí)現(xiàn)度也是農(nóng)民工在城居住意愿和能力的關(guān)鍵影響因素。回歸結(jié)果證實(shí)了上述判斷,即月收入越高,農(nóng)民工留城意愿也越高。居城年限在1%顯著性水平下通過(guò)檢驗(yàn),并正向促進(jìn)農(nóng)民工留城意愿的提升。這與李強(qiáng)和龍文進(jìn)[22]研究結(jié)果一致。居城年限可能在以下兩個(gè)方面提升了農(nóng)民工留城意愿。一方面,在城市居住時(shí)間越長(zhǎng),農(nóng)民工越適應(yīng)城市生活方式,對(duì)城市認(rèn)同度越高;另一方面,在城市居住時(shí)間越長(zhǎng),也意味著農(nóng)民工可能擁有更多的社會(huì)資本,良好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能夠?yàn)檗r(nóng)民工長(zhǎng)期留城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支持[4]。

表2 整體回歸結(jié)果Table2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models
3.2 省際遷移穩(wěn)健性分析
按照PSM方法的標(biāo)準(zhǔn)步驟,首先進(jìn)行統(tǒng)計(jì)性分析,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兩組數(shù)據(jù)有著較大的偏差,尤其是婚姻、月收入對(duì)數(shù)和代際的偏差均超過(guò)了20%,說(shuō)明樣本確實(shí)存在著嚴(yán)重的異質(zhì)性,有必要使用PSM方法對(duì)樣本進(jìn)行糾偏。本文選擇核匹配法、半徑匹配法(r=0.01)和最近鄰匹配法(非替代)分別進(jìn)行匹配。以核匹配法為例,結(jié)果顯示,核匹配后能夠很好的消除控制組和干預(yù)組樣本之間的顯著性差異。除婚姻因素外,其他各因素之間的差異均在5%之內(nèi),匹配效果良好。
省際遷移降低了促進(jìn)農(nóng)民工的留城意愿,即務(wù)工距離越遠(yuǎn),農(nóng)民工越不可能選擇定居在打工城市。使用其他匹配方法,如半徑匹配法(r=0.01)和最近鄰匹配法(非替代),也得到ATT值分別為0.50和0.51,與核匹配下的ATT值0.48接近(表3),從而結(jié)論具有穩(wěn)健性。

表3 基于PSM的ATT值Table3 ATT results calculated by PSM
3.3 家庭式遷移行為分析
與國(guó)外移民相比,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實(shí)現(xiàn)城市定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呈現(xiàn)階段性。為了分散家庭風(fēng)險(xiǎn)和獲取收入最大化,典型的農(nóng)民工家庭城市定居規(guī)律表現(xiàn)為一人或夫妻二人先行,其余的家庭成員依然在農(nóng)村,表現(xiàn)為“半工半農(nóng)”。但當(dāng)先行者在城市站穩(wěn)腳跟后,子女和其他家屬才會(huì)后續(xù)隨行,直至完成家庭式遷移。近年來(lái),農(nóng)民工家庭人口遷移發(fā)生率總體上呈逐年上升的態(tài)勢(shì),《2014年全國(guó)農(nóng)民工監(jiān)測(cè)調(diào)查報(bào)告》顯示,舉家外出農(nóng)民工總數(shù)達(dá)到3 578萬(wàn)人,占外出務(wù)工農(nóng)民工總量的21.27%,農(nóng)民工遷移家庭化趨勢(shì)逐漸明朗化[26]。
家庭式遷移對(duì)農(nóng)民工留城意愿有著顯著影響。當(dāng)農(nóng)村老家有老人或孩子,農(nóng)民工傾向在務(wù)工地和老家之間來(lái)回奔波,定居在城市的可能性不大。一旦完成舉家遷移,農(nóng)民工對(duì)家鄉(xiāng)的牽掛會(huì)迅速降低。很難想象,農(nóng)民工家庭尤其是核心家庭會(huì)在尚未實(shí)現(xiàn)家庭式遷移前選擇定居城市。另外,家庭式的遷移也標(biāo)志著農(nóng)民工已經(jīng)具備了在城市生活能力,能夠負(fù)擔(dān)起城市的生活消費(fèi)支出。由“個(gè)人式遷移”轉(zhuǎn)變?yōu)椤凹彝ナ竭w移”是農(nóng)民工家庭的理性選擇,是其自主性的體現(xiàn),因而有著更強(qiáng)的生命力。
以往研究均將家庭式遷移作為影響農(nóng)民工留城意愿的一個(gè)因素,并證實(shí)家庭式遷移有利于農(nóng)民工留城意愿的提升[3],卻忽視家庭式遷移已經(jīng)是一種穩(wěn)定的城市定居行為。且留城意愿與留城行為有著顯著區(qū)別[7],考慮到定居行為是在綜合意愿和能力之后的現(xiàn)實(shí)選擇,因而相比留城意愿,實(shí)際的家庭式遷移有著更高可信度。基于上述分析,我們選擇“是否實(shí)現(xiàn)家庭式遷移”作為農(nóng)民工真實(shí)留城意愿的替代變量,進(jìn)一步檢驗(yàn)務(wù)工距離對(duì)農(nóng)民工實(shí)際定居決策的影響。為提高回歸結(jié)果穩(wěn)健性,按照影響維度逐一增加進(jìn)行多次回歸(表4)。

表4 務(wù)工距離與遷移模式Table4 Distance and the migration mode
檢驗(yàn)結(jié)果顯示,在控制諸多因素前提下,遷移距離依然顯著負(fù)向影響農(nóng)民工的家庭式遷移。這表明較長(zhǎng)的遷移距離確實(shí)阻礙了農(nóng)民工家庭式遷移,距離越遠(yuǎn),農(nóng)民工進(jìn)行家庭式遷移的概率越低。考慮到家庭式遷移不僅是農(nóng)民工真實(shí)留城意愿的表示,更是農(nóng)民工定居城市能力的體現(xiàn)。因而,上述回歸結(jié)果意味著,遷移距離越遠(yuǎn),農(nóng)民工越不太可能舉家遷移到該城市,其留在城市的決心和意愿也相對(duì)較低。相反,距離越近,農(nóng)民工留城意愿相對(duì)較高,越傾向或更有能力進(jìn)行家庭式遷移,從而實(shí)現(xiàn)城市定居。而一旦完成這一過(guò)程,也會(huì)促進(jìn)留城意愿的提升。
控制變量方面,婚姻顯著影響個(gè)體家庭式遷移,已婚農(nóng)民工表現(xiàn)出較強(qiáng)的舉家遷移意愿。這可能與家庭生命階段密切相關(guān),已婚農(nóng)民工通常是家庭核心勞動(dòng)力,能夠按照自身意愿來(lái)做出這一重大決策。經(jīng)濟(jì)實(shí)力能夠提升了城市定居能力,在10%顯著性水平下,平均每月收入正向促進(jìn)了家庭式遷移,證實(shí)了預(yù)期判斷。另外,居城年限也正向促進(jìn)家庭式遷移的達(dá)成。
4 結(jié)論與啟示
4.1 結(jié)論
研究表明,當(dāng)農(nóng)民工務(wù)工距離越遠(yuǎn)時(shí),其留城意愿會(huì)越低。克服樣本選擇性偏差后,依然證實(shí)上述結(jié)論成立。進(jìn)一步分析表明,務(wù)工距離同樣顯著負(fù)向影響農(nóng)民工家庭式遷移。研究闡明了支持就近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國(guó)家戰(zhàn)略。
當(dāng)然,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就近城鎮(zhèn)化是今后中央政府及中西部各級(jí)政府需要大力推進(jìn)的戰(zhàn)略,但是我們的調(diào)查僅僅局限于貴州省,是否適用于其他中西部欠發(fā)達(dá)地區(qū)仍然需要更廣泛的調(diào)查和進(jìn)一步的驗(yàn)證。其次,就近城鎮(zhèn)化不僅僅是一個(gè)就近遷移的問(wèn)題,而且還涉及制度安排、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文化差異等多個(gè)方面的因素。本文僅就遷移距離這一視角做了初步探討,其他因素的影響有待后續(xù)研究。最后,定居決策和意愿可能是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變化過(guò)程,截面數(shù)據(jù)難以反映流動(dòng)經(jīng)歷對(duì)農(nóng)民工留城意愿的影響。因而,有待進(jìn)一步追蹤調(diào)查。
4.2 啟示
1)推進(jìn)新型城鎮(zhèn)化要重視和尊重農(nóng)民工自身的意愿。城鎮(zhèn)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鎮(zhèn)化,人的城鎮(zhèn)化在于保障權(quán)益。作為最可能首先實(shí)現(xiàn)市民化的群體,農(nóng)民工的主觀留城意愿需要得到尊重,在此基礎(chǔ)上的城鎮(zhèn)化才具有生命力。
2)遷移距離顯著負(fù)向影響農(nóng)民工的城鎮(zhèn)化路徑選擇。當(dāng)遷移距離越近時(shí),農(nóng)民工越可能選擇留城。城市政府要關(guān)注原戶籍地與打工城市較近的這部分農(nóng)民工,盡可能減少其遷入障礙,提供良好的接納環(huán)境。
3)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要加強(qiáng)吸引農(nóng)民工就近務(wù)工。欠發(fā)達(dá)地區(qū)通常也是人口凈流出區(qū)域,那么如何吸引住農(nóng)民工就近就業(yè)十分重要。對(duì)此,要繼續(xù)大力推進(jìn)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讓中西部農(nóng)民工能夠在家鄉(xiāng)城市或者不遠(yuǎn)的中心城市就近務(wù)工。欠發(fā)達(dá)地區(qū)的地方政府和企業(yè)也要做好相應(yīng)準(zhǔn)備,借力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kāi)發(fā)的良好時(shí)機(jī),吸引勞動(dòng)力回流和穩(wěn)定就業(yè)。
[1] 國(guó)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課題組. 農(nóng)民工市民化對(duì)擴(kuò)大內(nèi)需和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影響[J]. 經(jīng)濟(jì)研究, 2010(6): 4-16.
Research Group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effect of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on the domestic demand and economic growth[J]. Economic Research,2010(6): 4-16.
[2] Xu Q, Guan X, Yao F. Welfare program participation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11, 20: 10-21.
[3] 王玉君. 農(nóng)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十二個(gè)城市問(wèn)卷調(diào)查的實(shí)證分析[J]. 人口研究, 2013(4): 145-149.
Wang Y J.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ese cities: Findings from a 12 cities migrant survey[J]. Population Research,2013(4): 145-149.
[4] 馬瑞, 章輝, 張森, 等. 農(nóng)村進(jìn)城就業(yè)人員永久遷移留城意愿及社會(huì)保障需求——基于四省農(nóng)村外出就業(yè)人口的實(shí)證分析[J].農(nóng)業(yè)技術(shù)經(jīng)濟(jì), 2011(7): 55-65.
Ma R, Zhang H, Zhang S, et al.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wishes to be permanent migration and their social security needs—Based on the surevy of rural migrants of four provinces[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1(7): 55-65.
[5] 周建華, 周倩. 高房?jī)r(jià)背景下農(nóng)民工留城定居意愿及其政策含義[J]. 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 2014(1): 77-81.
Zhou J H, Zhou Q. The peasant worker’s settling down intention and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under the high price background house[J]. Economic Institution Reform, 2014(1): 77-81.
[6] 葉鵬飛. 農(nóng)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區(qū))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分析[J]. 社會(huì), 2011(2): 153-169.
Ye P F. Residential preferences of migrant workers: An analysis of the empirical survey data from seven provinces/districts[J]. Society, 2011(2): 153-169.
[7] 戚迪明, 張廣勝. 農(nóng)民工流動(dòng)與城市定居意愿分析——基于沈陽(yáng)市農(nóng)民工的調(diào)查[J]. 農(nóng)業(yè)技術(shù)經(jīng)濟(jì), 2012(4): 44-51.
Qi D M, Zhang G S. Rural migrant works’ flowing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y: Based on the survey of Shenyang[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2(4): 44-51.
[8] 劉磊, 朱紅根, 康蘭媛. 農(nóng)民工留城意愿影響因素分析——基于上海、廣州、深圳 724 份調(diào)查數(shù)據(jù)[J]. 湖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 2014, 15(2): 41-46.
Liu L, Zhu H G, Kang L 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igrant workers’will of stay in city for a long time: Based on 724 questionnaires from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J].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4, 15(2): 41-46.
[9] 李樹(shù)茁, 王維博, 悅中山. 自雇與受雇農(nóng)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異研究[J]. 人口與經(jīng)濟(jì), 2014(2): 12-21.
Li S Z, Wang W B, Yue Z 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ettlement intentions between self-employed and employed migrants[J].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2014(2): 12-21.
[10] 羅小峰, 段成榮. 新生代農(nóng)民工愿意留在打工城市嗎——家庭、戶籍與人力資本作用[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問(wèn)題, 2013(9): 65-71.
Luo X F, Duan C R. Do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s have the willing to stay in the city: The role of family, household register and human capital[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3(9): 65-71.
[11] 洪名勇, 錢(qián)龍. 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民工留城傾向的影響因素分析[J].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 2015, 15(2): 56-61, 68.
Hong M Y, Qian L. Long-term tendency of rural migrant works in developing regions to stay in working city[J]. Journal of Northwest A &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5, 15(2): 56-61, 68.
[12] Rosenbaum P,Rubin D.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J]. Biometrika, 1983, 70(1): 41-55.
[13] Heckman J J, Li X. Selection bi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heterogeneous returns to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in 2000[J].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04, 9(3): 155-171.
[14] Greenwood M J.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5, 13: 397-433.
[15] Ravenstein E G. The laws of migration[J].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85, 48(2): 167-235.
[16] Zipf G K. The P1P2/D hypothesis: On intercity movement of person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9, 11(6): 677-686.
[17] 蔡昉. 勞動(dòng)力遷移的兩個(gè)過(guò)程及其制度障礙[J]. 社會(huì)學(xué)研究,2001(4): 44-51.
Cai F. Two stages of labor’s transference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tuitional barrier[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1(4): 44-51.
[18] Mamermesh R. The economics of work and pay[M].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1993.
[19] 劉于琪, 劉曄, 李志剛. 中國(guó)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響機(jī)制[J]. 地理科學(xué), 2014, 34(7): 780-787.
Liu Y Q, Liu Y, Li Z G.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new migrants in China’s large citie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7): 780-787.
[20] Tolley G S. Population adjustment and economic activity: Three studies[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1963, 11(1): 85-97.
[21] 馬九杰, 孟凡友. 農(nóng)民工遷移非持久性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深圳市的實(shí)證研究[J]. 改革, 2003(4): 77-86.
Ma J J, Meng F Y. Factors that affect migrant workers non-persistent migr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in Shenzhen[J]. Reform,2003(4): 77-86.
[22] 李強(qiáng), 龍文進(jìn). 農(nóng)民工留城與返鄉(xiāng)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J]. 中國(guó)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 2009(2): 46-54.
Li Q, Long W J. Migrant works’ willingness to stay or leave and the corresponding factor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9(2): 46-54.
[23] Heckman J J.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J]. Econometrica, 1979, 47(1): 153-161.
[24] 王桂新. 我國(guó)省際人口遷移與距離關(guān)系之探討[J]. 人口與經(jīng)濟(jì),1993(2): 3-8.
Wang G X.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distance[J].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1993(2): 3-8.
[25] 聶偉, 王小璐. 人力資本、家庭稟賦與農(nóng)民的城鎮(zhèn)定居意愿——基于 CGSS2010 數(shù)據(jù)庫(kù)資料分析[J]. 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 2014,14(5): 53-61, 119.
Nie W, Wang X L. Human capital, Family endowment and farmers' willingness of urban settling-down: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10 database[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 14(5): 53-61, 119.
[26] 朱明芬. 農(nóng)民工家庭人口遷移模式及影響因素分析[J]. 中國(guó)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 2009(2): 67-76.
Zhu M F.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migrant works’ household migration pattern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9(2): 67-76.
(責(zé)任編輯:童成立)
Can working in the neighborhood enhance the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A case study of Guiyang
QIAN Long1,2, QIAN Wen-rong1, HONG Ming-yong3
(1.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2. Institution for Rural Development,Huzhou Normal College, Huzhou, Zhejiang 31300, China; 3. School of Management,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The neighborhood urbanization advocates by the “Three One-hundred-million People Plan” has become the national strategic goal. However,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goal depends on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 026 migrant workers in the undeveloped region, Guiyang City of Guizhou Province, and applying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and PSM Model, this paper seek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distance to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the neighborhood cities.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istance does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migrant workers’willingness to stay in the neighborhood: the closer the distance, the higher the willingness to stay. The regression result is valid even after overcoming the problem of sample selection bias; and 2) migration distanc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family migration: migrant workers are more likely to achieve family migration when the distance is closer. Findings from this research indicate that distance is important and it can affect both individual and family’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the cities. Results from this research provide a solid supportive evidence for the national strategic goal—developing the neighborhood town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1) we shall respect farmers’ subjective willingness of staying in cities; 2) we shall focus on the migrant workers whose homes are close to their working places; and 3)we shall attract migrant workers to work in the neighborhood cities.
migrant workers; neighborhood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to settle down; family migration; distance
the Key Project of Important Discipline and Particular Discipline in Humanities of Guizhou University (GDZT201104); the Innovation Team Project of Guizhou University (GDKWT2013002); the project supported by Institution for Rural Development of Huzhou Normal College (NFY2014-08).
HONG Ming-yong, E-mail: hongmingyong@163.com.
26 June, 2015; Accepted 26 September, 2015
F323.6
A
1000-0275(2016)01-0102-08
10.13872/j.1000-0275.2015.0145
貴州大學(xué)文科重點(diǎn)學(xué)科特色學(xué)科重大項(xiàng)目(GDZT201104),貴州大學(xué)創(chuàng)新團(tuán)隊(duì)項(xiàng)目(GDKWT2013002),湖州師范學(xué)院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院資助項(xiàng)目(NFY2014-08)。
錢(qián)龍(1988-),男,安徽樅陽(yáng)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人口經(jīng)濟(jì)與土地經(jīng)濟(jì)研究,E-mail: qianlongy101@126.com;錢(qián)文榮(1966-),男,浙江桐鄉(xiāng)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主要從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研究,E-mail: wrqian@zju.edu.cn;通訊作者:洪名勇(1965-),男,貴州金沙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主要從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和新制度研究,E-mail: hongmingyong@163.com。
2015-06-26,接受日期:2015-0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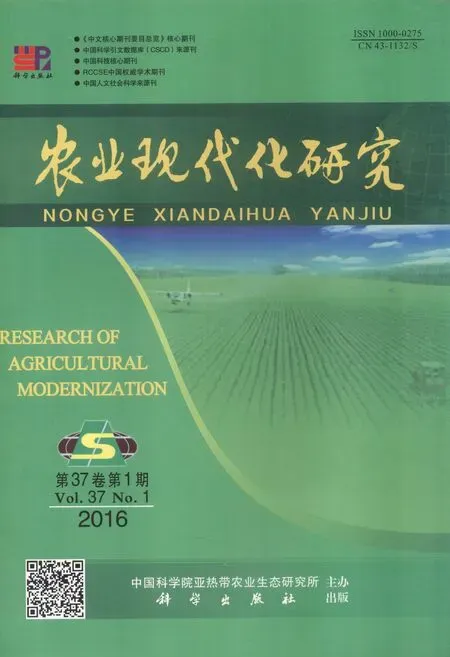 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研究2016年1期
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研究2016年1期
- 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研究的其它文章
- 玉米主產(chǎn)區(qū)深松作業(yè)現(xiàn)狀與發(fā)展對(duì)策
- 廣西不同林齡馬尾松碳儲(chǔ)量及分配格局
- 地表滴灌條件下滴灌量對(duì)土壤水分入滲、再分布過(guò)程的影響
- 農(nóng)地整理項(xiàng)目后期管護(hù)資金預(yù)算方法研究——以仙桃市張溝鎮(zhèn)高效種養(yǎng)基地土地整理項(xiàng)目為例
- 基于宏觀數(shù)據(jù)的乳制品質(zhì)量安全事件的影響及歸因分析
- 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農(nóng)民工收入分布變化對(duì)其食物消費(fèi)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