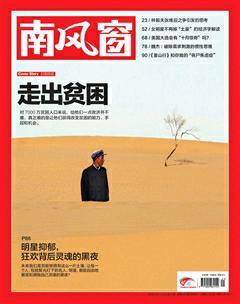轉型關口,我們需要更多華為與萬達
譚保羅
又是一個國慶節,而中國經濟也越來越到了轉型的關口。
從2015年下半年以來,一線城市的高房價,以及隨后二線城市房價大漲,讓很多還沒有進入樓市或者有著換房需求的普通人開始焦慮。特別是對那些還在大學校園或者剛畢業、沒有購房的年輕人來說,他們是直接的受損方。
高房價是個經濟現象,它推高了地租,蠶食實體經濟的根基。它也是個社會現象,帶來不公平和價值扭曲。那么,如何破解高房價?
世界上,高房價多數是經濟崛起之后的正常現象。經濟的運行,從本質上講,是個在資源稀缺條件下如何進行抉擇的過程。土地是最看得見、摸得著,并且永遠不需要計提折舊的資產。那么,它價格的走高,其實是市場發揮配置作用的結果。
但是,中國的高房價并不完全是一個基于經濟崛起的、正常模式的高房價。它的“不正常”,源自于兩個層面的深刻背景:一是財稅體制改革滯后,讓地方政府依然將土地相關的出讓金和稅收,視為第一財源,調控時常缺乏誠意;二是投資環境的疲弱,讓企業股權大幅度貶值成為經濟的一股暗流,于是資金全部涌向房子。
高房價的這兩個背景是歷史原因造成的,亡羊補牢,為時不晚。實際上,相應的改革已經啟動,決策層的決心非常明確和堅決。
就第一個背景而言,財稅改革是一場深度改革,既涉及中國國家治理的根本,也關乎經濟增長的整體框架。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一是中央放權時期,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0年代末完成分稅制和國企大改革為止。
二是中央的收權時期,從以上改革完成到現在可以算作這一時期。此間,中國不斷破除地方分割,統一的國內商品和要素市場逐漸建立,而金融體系也不斷趨于穩固,并從上到下配置著金融資源。在這一時期,中國開始真正享受“大國紅利”,實現了長期超過10%的增長。
現在,改革關口又到了。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同時,也指出必須“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并從預算制度、稅收制度、事權和支出責任等方面將改革路線圖具體化。
從營改增的不斷深化,到最近關于房產稅的討論,財稅體制改革已經在穩步啟動。財稅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改革有緊迫性,但更急不得。循序漸進,這是確保國家穩定、經濟結構調整成功的基礎條件。
高房價的第二個背景是企業股權的貶值,但這也并非實體經濟的全部,實體經濟內部依然有諸多亮色。它們代表著實體經濟轉型的方向。
任何國家,核心技術的創新一定是通過大企業來實現的,日本、韓國,走的都是這條路。因為,只有大企業才有條件和實力,而中小企業根本沒有。對中國而言,大國企的創新可能受到產權激勵方面的約束,因此民營大企業的創新更可能成為中國技術崛起、中國制造升級的主力軍。
華為就是這樣的典范。在外界唱衰中國實體經濟的時刻,2015年,華為銷售收入卻達到了608億美元(近4000億人民幣),比2014年增長37%,凈利潤57億美元,增長33%。2016年上半年,其銷售額同樣大幅增長40%。無論份額,還是口碑,華為已成為國產手機第一品牌。
手機業務的崛起,是華為這家曾經的“通訊基建企業”轉型的突破口。華為的藍圖已經很明確,一是向硬件上游要利潤,在芯片等核心部件領域,中國造的“華為芯”未來可能成為全球電子終端的主流之一;二是向軟件要利潤,不斷擴張的“花粉”(華為粉絲)版圖,這是華為發力軟件領域,乃至向娛樂休閑產業進軍的基礎。
除了華為,另一家龍頭企業萬達同樣值得關注。不同于萬科這樣的住宅地產商,萬達作為一家商業地產商,它更看重的不是賣房子、“做流量”,而是“盤活存量”。向已有的商業綜合體要利潤,從中國人的休閑娛樂要利潤,這是方向。實際上,除了一般的商業綜合體,側重于旅游休閑的萬達城項目早已在全國各地開花結果。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王思聰從國外回國,主動成為“網紅”,短時間內崛起為介于一線和二線明星之間的“1.5線明星”。其實,不妨將其看作是萬達轉型中國版“迪斯尼”的鋪墊。這種轉型,正是中國經濟所需,提振內需,更打造在娛樂產業的“中國品牌”。最終,也會匯聚為中國“軟實力”構建的力量之一。
某種程度上講,華為和萬達的轉型模式可以概括為:用中國的“大國紅利”,養出“中國技術”和“中國品牌”。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歸根到底要靠企業和企業家,而龍頭企業這種接地氣、講實際的轉型路徑,無疑是最優的選擇。
因為房價而焦慮,這是人之常情,但也更應該有信心。在經濟領域的縱深之處,一些積極的變化業已啟動,而改革更將為這種變化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