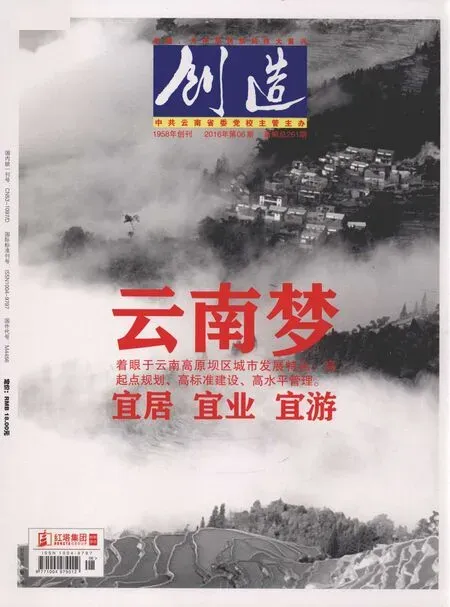返璞歸真,大愛流行——讀《不死的精神》札記
文/王海東(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研究員)
返璞歸真,大愛流行——讀《不死的精神》札記
文/王海東(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研究員)
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批判意識和大愛精神——是孟憲清作品所承載的大道。
盡管后現代主義反對宏大敘事,否定真理和進步等價值,解構文本、表征、符號和意義,但是它卻又悄然地建立起另一套理論——不可避免地滑向其所反對的那一極。而思想史也表明,偉大的作品少不了對人類命運的關照,必定要探究普遍性的問題,并作出具有超越時空的回應,方可成為經典。
而在當今中國充斥著消費、娛樂和價值碎片化的情形下,還能讀到反思時代精神狀況的作品實為不易。孟憲清先生的近作——《不死的精神》便是這樣一本“冒天之大不違”的作品!而我則獨愛這類作品,在孟先生的書中,不僅能夠看到強烈的批判精神,還能感受到其對人世的熱愛,那種大愛自然流行,光照人間。
一
通閱孟先生的作品,不僅能夠感受到匕首的鋒利——對當今中國社會諸種丑相陋習的嚴厲批判,還能夠明白其批判精神是如何培育與保持的?可以說,自由思想、批判精神和獨立精神是知識分子的靈魂。然而,在現實中,很多學人隨著年歲的增長和社會地位的提高,逐漸喪失這些寶貴的精神,有的潛心于自己的專業研究,有的犬儒化,有的干脆赤裸地追名逐利,還有甚者甘愿流氓化,禍害學術思想界。
而孟先生并沒有因為坎坷的人生道路就屈服于殘酷的現實,反倒猶如其家鄉沂蒙山上的青松——堅強不屈,與命運抗爭,克服病魔的折磨,求學問道,讀碩讀博,拿下哲學博士學位,改變自己的命運,循著理想一路攀升,登堂入室,成為文哲兼具的作家與學者。這樣的人生歷程,雖倍受苦難的煎熬,卻也“玉汝于成”,使其有足夠的勇氣面對一切困境,保持獨立之精神,不依附于任何外物——自由地思考和寫作,敢于向一切丑陋的現象開火。而多年的專業化哲學研究,使其批判精神愈加敏銳與深刻。哲學從不滿足于既有的論證與結論,而是反思一切思想,即便是真理也不放過對其進行審思。因而追問與考察,即批判精神,是研究哲學的必備條件。原本學中文的孟先生,轉而研究哲學,隱藏著這樣一個內在的邏輯。
有了批判的武器,進而展開對人性陰暗面、社會丑態和歷史文化毒瘤的深入剖析與批判。數千年來,我國形成一個官僚體系龐大的政治架構,官本位深入人心。在舊中國,“一個清白的人是不能當官的,必須在官場這個大染缸里泡一通,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才行”。逼迫自己同流合污,否則難以官運亨通。而這種異化的根源在于“傳統社會中的這種畸形和丑陋的人際關系是建立在人治、特權的基礎上的”。
因而“忍”與“混”也就成了一部分中國人的人生哲學,要么“自我封閉,消極避世”如五柳先生,要么“聽命于人,聽命于天”如楊白勞,要么“又熬又比,隱忍以待”如阿Q。這是“小農經濟和封建制度的土壤中培養出來的”,其毒害不淺,“它使人意志消沉、個性扭曲,是一種典型的庸人意識、奴才意識和教徒意識”。這樣的庸人和奴才,往往只會干些偷雞摸狗的勾當,混淆真假,模糊是非,騙人錢財。“在價值觀上,傳統社會并沒有把金錢至上普遍化,而在現代社會中則把它普遍化了,即成為人們的一種比較普遍的信念和習慣。”古代社會所形成的重義輕利觀,在商業大浪的沖擊下,已經被人們淡忘。而今雖然經濟高度發達,但是人們的道德水準卻大幅度下滑,精神生活幾近于無。
“潘多拉盒子”一經打開,人性中的邪惡就盛行不止,偽善、欺詐、不信任、欺騙、內斗、貪婪,猶如決堤之洪水,令人不寒而栗。政治上,政客頻出,不顧民生,執政為己,損公肥私,危及黨國的存亡。經濟上,奸商當道,官商勾結,巧取豪奪,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社會上,潛規則涌現,厚黑術廣為稱道,攀比成風,輕公德重私德,人間丑態百出。學術上,派系林立,江湖化,對真理的追求遠不及對名利的追求,人情大于真理,課題重于學術,學術環境不斷惡化,嚴重影響我國學術思想的正常發展。就連溫馨的家庭,也不斷異化,美好的兩性關系墮落為動物性關系——“中國人的婚戀中普遍存在著一種‘狗’和‘貓’的關系”。男人的狗性體現為“有奶就是娘”,而女人的貓性則表征為“誰家有肉到誰家,誰的被窩暖和就鉆誰的被窩”。在名利面前,很多人甘愿俯首為獸,卻也不肯挺直腰板為人。
這些都是我們民族的劣根。權力本位觀,人際不平等和人身依附使得人際關系惡化與異化,只有“通過長期的制度和觀念創新”才能消除這些丑態。通過借鑒他山之石,吸取傳統文化中的優良精神,以徹底清除我們民族的劣根,建立“健康、勇敢、創新、公正、勤奮等優良品質”。顯然,構建一種健康積極的時代人格是當前的迫切任務。
二
孟先生這種深刻的批判與建構,得益于長久的哲學研究。“哲學體現出對人的終極關懷,辯證法要立足于世界的整體和人的命運,以及對現實和理論的合理性進行不斷地追問和反思。我相信這個說法,并因此而熱愛哲學”。熱愛哲學,因其關乎著人類的整體命運。這其中要有一種大愛,也就是對人間滿懷悲憫之情,關注人世的種種問題,不懈地尋找出路。
歷史上偉大的人物,尤其是思想家,都對人世充滿深切的同情。“他們都是對人類的生活與命運進行總體性思考,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終極關懷’,即從總體上和長遠的角度來關懷人的生活和命運。這也是宗教家和思想家們對人的一種‘大愛’”。這種終極關懷,就是孟先生的精神追求與實踐智慧。他對災難的深情關切,對民生的持續關心,對政治問題的反思,對社會問題的系統考察以及對中國人的精神狀態的憂慮,都源自這份大愛之心。
而這種“大愛”并非一人獨占,是人人都能夠擁有的。“‘大愛’是一種精神原則、一種理性精神、一種博大的胸懷和高尚的人生境界”。每個人,通過不斷修煉,都能夠達到這樣的人生境界。由于當今社會價值混亂,物欲橫流,人情冷漠,就更需要“大愛”精神。因而孟先生呼吁社會多一些溫暖,多一些大愛。而知識分子則更應如此,“文人要如北宋大儒張橫渠所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就要‘無我’,就要有徹底的獻身精神”。只有做到無我,沒有分別心,放下私欲,才能客觀公正地審視人生與社會,探究出善良生活與人類的出路。
正是這種“無我”的精神,使其能夠真誠而勇敢地向讀者揭開自己的秘密。懺悔自己兒時犯下的小錯誤——捕鳥、捉魚和釣青蛙等活計殺生不少,而少時的我們何嘗又沒有干過類似的事情呢?懺悔吧!我們何嘗沒有參與“平庸之惡”呢?只是不自知而已。然而,這種懺悔不只是贖罪,更是大愛的呈現。“這是我的懺悔。同時,我想告訴人們,為了愛護動物、保護環境,不僅要增強意識,改掉不良習慣,而且要禁止買賣野生、消除貧窮。”大愛不僅愛人,還應愛護動物和環境,它們也有平等的生命權,還是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
三
不論是宏觀的政治問題反思,還是微觀的人物懷念,也不論是對歷史文化傳統的系統考察,還是對人性的深層拷問,孟先生的精神一以貫之——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批判意識和大愛精神。這是其作品所承載的大道!
與時下的作家相比,孟先生幾乎不考慮文飾與技巧,而是返璞歸真,沒有任何雕飾,自然純樸的文字,卻飽含真情,對人世的關愛盈盈滿眶。孔夫子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而在這樣的時代里,我更愿意看到真實質樸的作品,能夠脫掉偽善的面具,令人欽佩。孟先生正是這樣以質見長的作家,希望他能夠堅守此道!
這種不死的精神,它不僅是孟先生的精神,理當成為知識分子們共有的精神。愿其薪火相傳,光照萬古!
(《不死的精神》,孟憲清 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