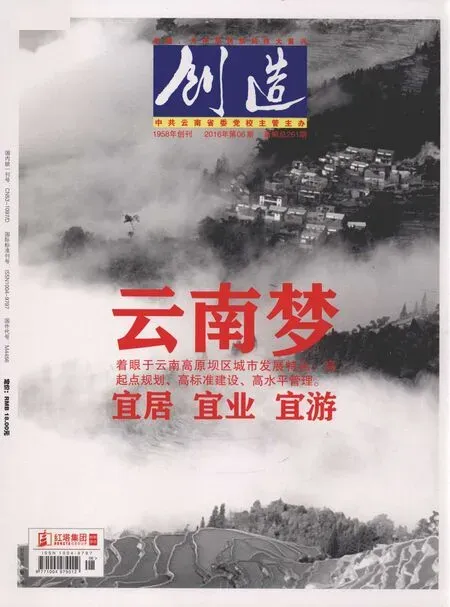瀘沽湖——游弋于自我時空隧道的神秘國度
文/圖 林 夫
瀘沽湖——游弋于自我時空隧道的神秘國度
文/圖林夫
記憶中的木屋、橫亙在草海蘆葦叢中的豬槽船、簡易的情人橋,都喚起人內心深處的渴望。

十年前,當我們風風火火地來到瀘沽湖邊,連裝扮成蜘蛛俠的女兒都被她的寧靜所感染;十年后,跟隨課題組重溫舊地,希望得到更多還是她的靜美。對于生活在速度之上的現代人來講,也許瀘沽湖最具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其特立獨行地游弋于自我的時空隧道中,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變化。
從寧蒗出發,一路穿過蜿蜒曲折的山路,行駛85公里后,淅淅瀝瀝的小雨漸漸停息,走出車子,沿著一條木板鋪成的小路拾級而上,映入眼底的是一塊鑲嵌在群山懷抱之中的清澈湖面,碧波蕩漾,天空湛藍,白云飄帶,一下恍入仙境,心曠神怡。這就是瀘沽湖了。
關于瀘沽湖的形成,當地流傳著一個有趣的故事:在遙遠的年代,這里曾是一片村莊。村里有個孤兒,每天到獅子山去放牧。人們只要把牛羊交給他,他總是把牛羊放養得肥肥壯壯的。有一天,他在山上一棵樹下睡著了,夢見一條大魚對他說:“善良的孩子,你太可憐了,從今往后,你不必帶午飯了,就割我身上的肉吃吧。”小孩醒來后,就到山上找啊找,終于在一個山洞里發現那條大魚,他就割下一塊燒吃,魚肉香噴噴的。第二天,他又去了,昨天割過的地方又長滿了肉。這事被村里一個貪心的人知道了,他想把大魚占為己有,就約了一些貪財之徒,用繩索拴住魚,讓九匹馬九頭牛一齊使勁拉,魚被拉出洞,災難也就降臨了。從那個洞里,洪水噴涌而出,頃刻間淹沒了村莊。那時,有一個摩梭女人正在喂豬,兩個年幼的孩子在旁邊玩耍,母親見洪水沖來,急中生智,把兩個孩子抱進豬槽,自己卻葬身水底。
湖的西北面,雄偉壯麗的格姆山女神山巍然矗立著;湖的東南面,一條公路把高低錯落個村子一分為二,這就是落水村。
懷揣逃離城市的喧囂與探尋女兒國的興奮,我們順山而下,走了10多公里后,住進了落水村的一家私人客棧,老板是一位湖南人,在此承包開店已經多年了。瀘沽湖的客棧肇始于1999年,目前已發展到100多家,基本上可以說家家都有一個客棧,人均收入2萬元以上。
我們住的房間面對湖水,湖中心有一小獨島,名為黑瓦吾島,是上世紀永寧土司阿云山總管的水上行宮,美國學者洛克也曾旅居于此。島上綠樹蔥郁,與天鏡般的湖面形影互映。一葉小舟緩緩劃來,船上的男子一會兒撒開大大的漁網,一會兒撐推長長的竹篙,好一幅漁歌唱晚的美景。

瀘沽湖全景

朝陽下的豬槽船

落水村全貌

落水上村

落水下村的街道

在落水村,摩梭人幾乎家家都有一個客棧出租

摩梭老人與她的兒子
這個時候是當地旅游的淡季,但對于在湖邊起起落落的水鳥來講,卻是它們歡樂熱鬧的盛日。千百年過去了,無論是土司還是洛克的身影,我們都只有通過斑駁的老照片來追尋歷史中的他們,而瀘沽湖依然年輕,依然如睡美人般溫柔地躺在格姆山女神山腳,湖周圍的百姓也一如既往地遵循著打魚、唱歌、串房、走婚的生活方式。
第二天,我們在當地人的引導下,走訪了幾家摩梭人家。瀘沽湖民房大多為方木垛成的井干式木楞子房,以木板當瓦。內部結構為適應其母系原則而組成家庭特點,有火塘所在的正室,為全家的中心。旁有老人及未成年孩子住的地方;另一幢二層樓房為“客房”,上層為青壯年婦女與他們的“阿注”的居室。家家都是寬敞明亮的四合院,那透著油膩發亮的木楞子老房子已經在這里很難找到了。
村子不大,公路上頭靠山的村子被人稱為上村,下面臨湖的則是下村,統屬落水自然村,目前共有122戶545人,全部都是摩梭人,原來主要是從事傳統農耕、捕魚業,現在通過旅游業的發展,當地居民的主要經濟收入已經是靠出租客棧、開飲食店為主的商業模式了。
走在村子明亮的石板路上,偶爾會碰到穿著民族盛裝、手持轉經筒的當地女人,幸福滿足的表情在陽光下熠熠生輝。
村子的兩頭,仍有村舍客棧在不停施工擴建,嘈雜刺耳的機械聲打破了這里安靜停滯的空氣,我不知道這是好是壞?事實是這里過度的開發已經引起了當地黨委政府部門的關注。
由于瀘沽湖位于四川省鹽源縣與云南省寧蒗縣交界處,為川滇共轄,四川的湖岸線比云南的湖岸線還長約占2/3。為了對瀘沽湖摩梭人的傳統民居有個全面的了解,我們驅車繞湖一圈,到達四川境內。
四川境內沿湖摩梭人的村舍,遠沒有我們云南的繁華與熱鬧,卻讓人感受到一種本質的樸實與純真,記憶中的木屋、橫亙在草海蘆葦叢中的豬槽船、簡易的情人橋,都喚起人內心深處的渴望,也許簡約已經成為現代人的一種奢求。
摩梭人把瀘沽湖看作母親湖,把格姆山當作女神山,把家中的女性擺在社會最高的位子。可以說,瀘沽湖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滲透著女人濃濃的文化元素。也許,在這里,正是女性天然的本性注定了這塊神秘之地的神奇。

摩梭女人

早上起來去轉經的女人們

住在木楞房里的居民

四川境內的情人橋

在瀘沽湖打魚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