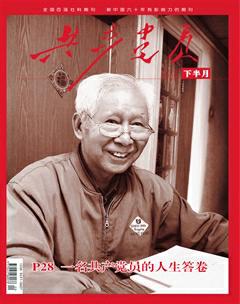駐村幫扶的苦辣酸甜
曾慶剛
我是2015年10月28日開始駐村的。回想起駐村以來的一幕幕,不僅有波波折折、跌宕起伏,更有苦辣酸甜。
第一個感受是苦,百姓境況的苦,強化了我們的責任,使我們忘記了駐村幫扶工作的苦。工作隊一共3人,我自認為從小在農村長大,對農村的苦有切身感受,之后又在部隊摸爬滾打了25年,是個吃過苦、不怕苦的人,但當我們進村入戶調查、精準識別時,對于貧困村的現狀和貧困群眾的苦,還是目瞪口呆了。
我們所幫扶的岫巖滿族自治縣牧牛鎮南馬峪村,是個遠近聞名的窮山村,共有14個村民組,615戶,2353人,主要靠種山腳下的人均一畝薄田為生。村集體沒有財產,收入為零,負債28萬元。進村第二天,我們就按要求開展精準識別工作。在村干部的指引下,我們去的第一家是五保戶楊佩林家。他所謂的家在一個半山腰上,遠遠看過去,一座低矮的土坯房,都趕不上好人家的牲口棚。我們費勁地沿著小山路爬上去,推開屋門后,看到一個頭發灰白的老漢半臥在炕上。嘮嗑過程中,我環顧了一下家里的陳設,除了電燈外,沒一樣家用電器。第二家,遠看房子院子的境況能比上一家好些,可一進屋,還是讓我們的心揪了起來,一個中年男人拄著拐杖站在屋當中,炕上兩人,一個是癱瘓多年的妻子,一個是17歲的智障兒子,三雙無助失神的眼睛看著我們,不用深問,面對眼前這些,再鐵石心腸的人都會動容。在走訪的貧困戶中,像這樣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讓我們深受震撼和觸動的至少有20多戶。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南馬峪村的貧困情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人數多。僅建檔立卡貧困戶就多達81戶193人,約占全村總戶數的13%。二是覆蓋廣。14個村民組每組都有貧困戶。三是程度深。一半左右的貧困戶都是失去“造血”功能的深度貧困戶,貧困程度之深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四是致貧原因類型多。因病、因災、因學,缺資金、缺勞力、缺技術,觀念落后等致貧因素在這里都能找到鮮活的例子。
隨著調查的深入開展,我們深刻認識到,貧困問題已經成為我們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塊“短板”,是最難啃的一塊“硬骨頭”。脫貧攻堅工作關乎百姓的福祉和發展大計,也關乎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我們所肩負的駐村脫貧工作職責是如此神圣、沉重和緊迫,我們必須全力以赴,不辱使命,不負重托。
我們住的地方是政府的簡易宿舍,冬天冷得要命,蓋被伸出胳膊擺弄手機,手指能凍僵,過個兩三分鐘就得放在肚皮上焐一焐;夏天又熱得要命,前后不通風,沒有空調,日照時間短,被褥潮濕得很,蚊蟲也特別多;室內沒有衛生間,上趟廁所得走出40米,夏天還好些,冬天最打怵上廁所,好不容易在被窩里有點暖和氣了,折騰一趟又凍得渾身發抖;房間里也沒有浴室,多數得回鞍山的家時才能洗個澡。
困難群眾的苦,激起了我們攻堅克難的斗志和勇氣。工作隊的隊員們一致認為,如果我們吃些苦頭,哪怕就是脫皮掉肉,能換來貧困群眾脫離貧困,過上幸福的好日子,我們的辛勞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第二個感受是辣,百姓的質疑辣味十足,這是對我們的期待,更激發了我們干事創業的熱情。工作隊當初滿腔熱忱進村入戶時,所受到的“禮遇”是我意想不到的,用當地老百姓的話說就是——熱臉貼上冷屁股。
在走訪群眾時,有的貧困戶指著我們說:“扶貧扶貧,你們來了多少撥兒了,扶出個啥來了?”有的帶著輕蔑的語氣說:“你們帶來多少錢撂這,我們自己會分。”有的在背后嘀咕,“他們下來就是來‘鍍金的,走個過場,回去好提拔,升官發財”。聽到這些辣味十足的話,我們心里很難受。難道我們黨員干部就給他們這樣的印象嗎?對以上種種不理解,我們沒有做更多解釋,但每個人都憋足了勁兒。
進村約一個月,11月下旬,隨著天氣轉涼,我們向市民政局爭取為全村81戶貧困戶籌集了棉衣、棉被、毛毯等過冬物資860件。從今年開春到現在,新安裝路燈100盞,建設文化廣場2000平方米。對貫穿全村的鄉級公路進行大修;修建村組扶貧路3.8公里、橋梁5座。修建移民動遷水利工程600延長米;實施應急防汛工程500延長米;為村里植樹5000棵;首批向12戶貧困戶發放帶崽母羊24只。
喊十句口號,不如做一件實事。隨著駐村工作隊把一件件貧困群眾看得見、摸得著的實事做到實處時,群眾的口風也隨之發生了改變,那些辣味十足、陰陽怪氣、帶著譏諷的話語再也沒有聽到,相反,有一天,我聽到一位村民說:“原來老曾他們是動真格的,我要也是貧困戶就好了。”當貧困戶能讓別人羨慕,讓我哭笑不得。
第三個感受是酸,扶貧路上充滿辛酸,我們在想方設法爭取各方支援的過程中感受了太多的酸楚。如何增強貧困村、貧困戶的造血機能?發展什么樣的產業項目,既能帶動貧困戶脫貧,又能解決村集體收入“空殼”問題?項目建設啟動資金從哪里來?怎么建設?建完了怎么管理?一個個問號擺在我們面前。
南馬峪村山多地少,種苞米一年每畝地也就能收入三五百元,根本無法脫貧。牧牛鎮是香菇種植大鎮,被譽為“中國香菇第一鄉”,種植香菇對勞動力的要求也沒有那么高。鞍山市委組織部領導班子帶著我們工作隊一起開會研究想辦法,最后大家一致認為建香菇種植基地是個不錯的選擇。為此,我們加大了對這方面的考察調研力度,先后三次驅車到撫順市清原滿族自治縣學習考察層架式香菇種植模式。同時到鎮里德圣食用菌種植專業合作社等十幾家企業學習,了解掌握香菇種植的現狀、市場需求和發展趨勢。經過反復研究論證,最終確定建一個總投資約120萬元的大型香菇扶貧攻堅基地。
120萬元,錢從哪來?辦法總比困難多:一是要,組織部主要領導親自找到鞍鋼負責同志,協商扶貧資金30萬元;二是籌,市委組織部向全體部機關黨員干部發出扶貧集資倡議,一天下來籌集資金25.4萬元;三是賒,以鋼架大棚等做抵押,向菇段加工商賒一部分菇段;四是省,大棚建好以后的菇段進棚階段,需要很多人工,當地人工很貴,一個男工一天下來最少也得在150元錢以上。部領導知道情況后,兩次帶領部分機關干部80余人,來到基地親自動手干。部長、副部長帶頭親自推車,其他機關干部有的裝車,有的擺放菇段。在乍暖還寒的早春時節,大家干得熱火朝天、大汗淋漓,僅人工成本一項就節省一萬余元。
建成的基地屬于村集體資產,這徹底改變了村集體經濟“空殼”問題。基地建好了,交給村里管理和運營,老百姓不能信服,什么貪了占了,這樣的非議聲肯定會隨之而來。那就暫時由我們駐村工作隊來管。于是,我們從頭學習食用菌種植管理的各種知識,對于什么時候注水,什么時候通風,什么時候翻段,菌段發育成什么樣算健康,采摘的蘑菇如何分等級等,我們都了如指掌,儼然成了“土專家”。我們現在在基地既是管理者,又是技術員,更是勞動者。每天,我們和工人一樣忙來忙去。工作隊隊員金大鵬每天斜挎個小包,與前來收蘑菇的小販討價還價,斤斤計較,有時還爭得面紅耳赤,外人不知道,還以為他是個會過日子的莊稼漢呢。
鞍山市農委領導看了我們頗具規模的基地,非常震驚和感動,主動協調有關部門及企業,為我們捐助了一臺農用廂式貨車。為了能讓蘑菇賣出好價錢,擺脫中間商的盤剝,我們利用這輛小廂貨,把采摘下來的蘑菇直接運送到鞍山各大機關食堂銷售。現在蘑菇已經采摘三茬了,收入30多萬元,預計至少還可以出兩茬蘑菇,總收入達到50萬元沒問題。
我媳婦是初中畢業班班主任,兒子在外地工作。全家起初對我跑到100公里以外的窮山溝扶貧不是很理解。一天,岳母不慎跌斷胳膊,媳婦電話里帶著埋怨:“你已經54歲了,還能怎么著?”聽了這話我心里酸酸的,為了多個項目落地,我多次驅車往返于市里和山村之間,古人三過家門不入,我又何止三次?早就到了結婚年齡的兒子為了早日促成雙方家長謀面,多次和我商量,被我一再拖延,我確實對他們有太多的歉疚。
第四個感受是甜,群眾滿意就是我們的幸福,這永遠是我們黨員干部的追求目標。苦盡方能甘來。雖然吃了很多苦,付出了很多辛勞,也受了不少委屈,但看到脫貧攻堅工作在我們的推動下取得了一些實實在在的成果,我們心里也是甜滋滋的。
100盞太陽能路燈拔地而起,當初我提出的“條條路上有燈光,百姓出門見燈光”的承諾兌現了,村里近百名青年男女在活動廣場的燈光下跳起廣場舞,扭起大秧歌,早已經熟悉我們的百姓紛紛向我們豎起了大拇指。10個月的時間,我們通過多方努力,為南馬峪村爭取各項資金709萬余元。
走訪的第一個五保戶楊佩林家也變了樣。我們幫他新建了房屋,窗明幾凈,給他配上了電視。送電視、接有線的那天,他一面拉著我的手,一面目不轉睛地看著電視,他說他想看看現在誰是國家領導人,是誰讓黨的好干部又回到百姓身邊了。聽了這話,我很感動。我在市委組織部干了十幾年的基層組織建設工作,一直要求基層要強化宗旨意識,踐行群眾路線,沒想到在那一刻,我們真真切切地光榮了一把、偉大了一把,在老楊眼里,我們就代表了黨,代表了新時期的好黨員、好干部,我們為黨增了光、添了彩,我發自內心地感到驕傲!
看著一個個貧困戶家里的生活好起來,看到他們憨厚樸實的笑臉,我覺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作者系鞍山市委組織部組織二處副處長、駐岫巖滿族自治縣牧牛鎮南馬峪村工作隊隊長)
□本欄編輯/張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