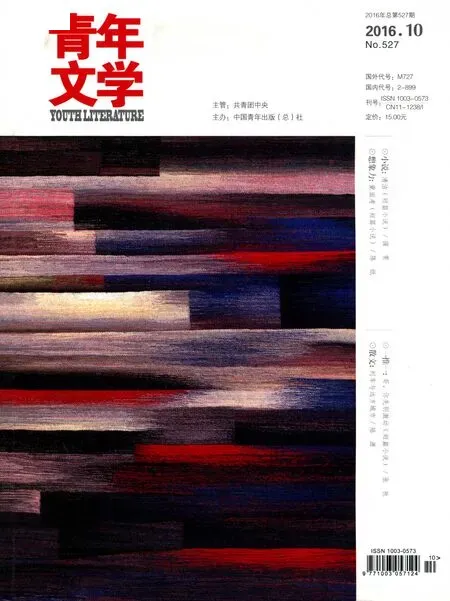“就這么瞎混吧”——《哥,你先別激動》的一種語態分析
⊙ 文 / 張艷梅
“就這么瞎混吧”——《哥,你先別激動》的一種語態分析
⊙ 文 / 張艷梅

張艷梅:一九七一年出生,文學博士。現為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在《文藝爭鳴》《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理論與批評》等期刊發表論文近兩百篇,出版《海派市民小說與現代倫理敘事》《文化倫理視閾下的中國現當代小說研究》等著作。曾獲山東省劉勰文藝評論獎、山東省高校優秀科研成果獎等。
在一篇創作談中,張敦說起,自己的小說大多是第一人稱,幾乎都來自本人的生活經歷。他寫了很多一事無成的年輕人,在生活的污泥濁水中浮沉,看似拼命掙扎,總不免還帶著些放任的頹廢。那些細小的特別之處,漫漶出張敦的敏銳和心不在焉。就像一片果園,青澀的惹人遐想,成熟的明艷動人,還有個別的傷痕累累,讓人心懷向往又惴惴不安。這,或許就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生活和世界。讀到這篇《哥,你先別激動》,想起甫躍輝的《動物園》,王威廉的《非法入住》,孫頻的《菩提阱》,文珍的《安翔路情事》等篇。“80后”作家筆下的底層生活,呈現出獨特的敘事間性和客體感受的延展性。在上述小說中,無論是第一人稱自述,還是他人視角建構,提供的往往是類似的個體,并且這一切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有效地形成了社會經驗或生活體驗的共同體。
場景特寫。
張敦顯然對于社會邊緣人的普遍困境非常理解。他的表達自由流暢,真實感和在場感,交織成不錯的視覺效果。為了強化那種心不在焉的感覺,他會給人物背后陳列的場景補光。不是為了放大視覺上容易忽略的細部,也不是為了調整語言的亮度,而是要突出心理上晦暗不明的那部分。讓敘事溢出固有的生活邊框之外,提供一個新的可供平衡的重心。
小說中,張敦有多處借助性來實現這一意圖。和小麗的例行公事,一個人與自我的糾纏,和黃萍的酒后放縱,敘事作用大致相類似。張東刻意強調的理性,看起來是負責任的自覺,久而久之反而更像一種推卸和慣性。顯然,刻板的形式,意外的笑場,借助欲望滿足消解了緊張感,反襯出人生中更深的無聊和無奈。性,不是打通兩個世界的隧道,而是一堵自我禁閉的墻。一堵把個人精神苦悶張貼得理直氣壯的墻。那些自動聚集的消極和淡漠,彌漫在狹小的空間中。張東無動于衷心如止水,與黑夜沖動糾纏的身體,連同“激動”這個詞語,都成為一個大寫的符號。
深圳,北京,省商務廳,作為鏡像的空間。合租的蝸居,大學校園,菜市場里的會友飯館,真實的生活現場。四處流淌的無意義。一群年輕人,茫然地游動在時代的銅墻鐵壁之中。小麗去深圳,“我”假裝不舍,黃萍去北京,“我”頗覺意外,“你怎么能這樣?”張東內心隱含的追問是,生活,怎么能這樣?那么,不這樣,又能怎么樣?“就這么瞎混吧。”“我”打定主意。關上手機。冷靜地躺在床上。等待黃昏的到來。從床上到華北平原,空間莫名其妙地打開,時間卻凝固了,小說最終以極晝這一束強光穿透黑夜,一切模糊的都無所遁形,包括與生活一起破碎的悲傷和孤獨。
解構反諷。
小說把一些零散的事件,放置在反復擠壓的時間之中,醉酒,醒來,時間被卷曲,又平鋪開來。作為比較典型的室內劇,遠沒有《歡樂頌》那么虛假的戲劇性和勵志激情。鏡頭打開,推到我們面前的,是一張床,一張飯桌,一臺電腦,來回走動的三個人,還有一個偶爾漂浮在合租屋里的影子。
緩慢推進的敘事如同翻卷的海浪,把愛情、職業、未來,都降低到最本能的層面。陳希堅持復習考研,小麗遠赴深圳淘金,黃萍去北京尋找機會,張東每天不厭其煩地撥打推銷電話,看起來,每個人都在左沖右突地與生活較量,無限循環的是迷惘的未來。就算是無知無覺地被扔進命運的河流,個人感受同樣會有巨大落差。張敦賦予合租的這幾個人不同的個性,不同的心態,就像混合在一起的洗面奶,慘白的臉,蒼白的生活撲面而來。無論是面對面的交流,網上的交流,身體的交流,都無法抵消彼此的陌生和疏離。
表面上,兩個平庸的人,相愛,同居,吵架,跳槽,分手,是小說的主線。“我倆本來就是別人挑過的,平凡得猶如食堂大盆里的雞蛋,被人拿走的與剩下的,都是一個樣。”正因為都是一個樣,兩個人的糾葛,其實更像是一個人的獨舞。第一人稱,往往可信度更高,讀者更容易被代入,作者的代理人,與讀者的代言人暗暗重合。打電話的沖動,是一個饒有意味的細節。渴望建立起與世界的聯系,然而這種聯系又是荒誕和不確定的,隱藏的真實心理,是對這個世界的深深厭倦和嘲諷。這一細節有著相當不錯的解構和反諷效果。打開罐裝的日常性,切片,看到生活的肌理,讀者既是舞臺下面的觀眾,又是后臺幫助化妝的技師,同時,在某些情境中,與小說人物互換位置,虛構的故事分解為無數具有象征意義的瞬間。
流動的沖突。
小說有種內在的緊張。張東的情緒仿佛隨時會爆發,卻又平淡無奇地打發掉了每一個日子。激動,是全篇的,時常跳出來打斷敘述的節拍。張東說:“我寫的都是狗屎。”“狗不用找工作,我連狗都不如。”小麗說:“你是一個沒有上進心的人。”“嗯,我以前覺得那是一種灑脫。”“現在覺得你是個傻逼。”即使如此刻薄,小說的基調依然算不上尖銳。沒有劍拔弩張的社會批判,也沒有故作高深的人性探問。比起滿眼皆是的殘酷敘事,簡直稱得上溫和調侃。
小說描述了某種真實的狀態。生活平淡無聊。工作機械重復。感情波瀾不驚。性愛乏善可陳。嚴肅的人生,沉重的現實,被“你先別激動”渾然消解。張敦把蒼白灰冷的生活,寫出了色調悅耳的節奏。小說的基調是慵懶的,這符合主人公的生活狀態。女朋友離開,沒有形成什么危機感,反而內心是竊喜的。在喧囂的背景聲中,黃萍掛掉了電話。失去,仿佛是一種解脫。陳希對黃萍的鄙薄,小麗對“我”的不屑,“我”對工作的挑剔和對感情的將就,都在驗證生活挺沒勁這個結論。張東身上那種無所謂的氣息,加深了生活的褶皺。每個人在生活中被標識出來,放在那里,即使沒有什么外在行動,內在也不為所動,依舊在自身的存在中獲得了存在的位置。
張敦,算是一個固執的寫作者吧。他熟練地出入于小說文本內外,把他對生活的觀察和認識,不緊不慢地講述給我們。光線悄無聲息地推移,日常生活依舊拖泥帶水平庸無聊,極晝只是幻覺。夏日黃昏終將覆蓋激動到極點的身體。一切敞開的,同時也是隱匿的;無論多么遠,或者近;復制,或者刪除,生活本身,就在那里。想起《當幸福來敲門》中的克里斯·加德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