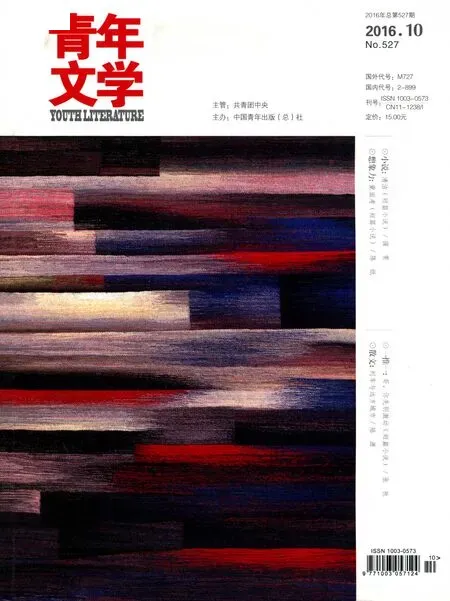哥,你先別激動
⊙ 文 / 張 敦
哥,你先別激動
⊙ 文 / 張 敦

張 敦:一九八二年出生于河北棗強,河北文學院簽約作家,著有短篇小說集《獸性大發的兔子》。現居石家莊。
三年前上大學的時候,我和小麗成了情侶。作為兩個各方面都很一般的人,我們的感情之路也稀松平常,并無所謂的風雨坎坷,就像兩塊吸鐵石,只因為離得太近,啪的一聲撞在一起,沒有絢麗的火花,沒有奇妙的化學反應,就這么硬生生地黏住了。我倆都很清白,互相是對方的初戀,沒有第三個人跑出來,要搶走她,或者搶走我。我倆本來就是別人挑過的,平凡得猶如食堂大盆里的雞蛋,被人拿走的與剩下的,都是一個樣。
就我來講,已徹底接受小麗的平庸,盡管對她的相貌和身材深表遺憾,但這有什么辦法呢,我的相貌與才智也很一般,與小麗般配得讓人無話可說。我們一起吃飯,一起上課,一起去圖書館,從不逃課,從不掛科,小麗甚至還能拿到獎學金。這段戀愛沒有逾越校規校紀,就連開房做愛都選擇休息日,干完即收兵回營,不在外面過夜。
畢業后,我們在省城找工作,租房同居。到目前為止,小麗沒有懷孕過——這種不理智的事怎么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已經習慣使用避孕套,如果不戴,反而會潰不成軍。這一點,小麗非常滿意,認為此乃愛意的表現。同居之后,做愛的機會唾手可得,漸漸有了例行公事的意思。實際上,我們的性生活與感情生活如出一轍,也是乏善可陳的,具體表現在行房的姿勢千古不變,我在上面她在下面。有時我試圖改為女上男下,小麗堅決不從,她覺得那不是正常的做愛方式。
“不行,我總覺得這不是做愛。”
“不是做愛?那是什么?”
“是淫亂。你從哪里知道這些姿勢的?你有問題啊。”
聽小麗這么一說,我也覺得事情挺嚴重的,于是放棄那種非分之想,繼續匍匐在她身上埋頭苦干。
其實,在小麗的心中,我們算是前衛的。這些不計其數的婚前性行為,已經讓她覺得驚天地泣鬼神了。她說:“如果我是保守的人,絕對不會與你在結婚之前上床。”我無話可說,在這件事上,絕不能與她爭辯,否則會背上道德敗壞的惡名。
我們在床上身經百戰之后,也和別人一樣,考慮結婚的問題了。結婚得有房子,這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我家和小麗家條件差不多,都挺窮的,即使連首付的錢,也拿不出來。我們只能自己攢錢,省吃儉用,每月攢下兩千,大概再有五年,就能付得起省城三環外房子的首付了(如果房子不漲價的話)。
五年,對于我們這樣的年輕人來講,何其漫長。問題還在于,我們并不能圓滿完成每月積攢兩千塊的目標。小麗還好,一直在某家房地產公司干策劃,收入比較穩定。與之相比,我的情況不容樂觀,總在換工作,從小報編輯到培訓班老師,從保健品銷售到保險銷售,干來干去,沒掙到什么錢。在找工作的日子,我逐漸花掉小麗攢下的錢。其實是我倆一起花掉的,吃住一起,誰都有份,但由于我只出不進,飽受小麗的指責,顯然被當成消費的唯一主體。
由于我的“不夠走運”,買房計劃中的“五年”被拉長為八年。這觸目驚心的八年,是小麗計算出來的,不知她運用了怎樣的運算法則。她不明白,像我這樣的老實人,為何不能長久地待在一個工作崗位上。——我應該像一顆螺絲釘,銹死在社會機器的某個固定的角落。
“你要跳槽也可以,但你找好下家再跳啊,你往待遇好的地方跳啊,你倒好,頭腦一熱就辭職,辭了職就像狗一樣找工作,一找就找一個多月,新單位還不如上一家給錢多。”
“狗不用找工作,我連狗都不如。”
從不吵架的我們,開始因為工作的問題發生爭執。這期間,性生活幾乎廢止,而我也因為內心的焦慮,顯露出陽痿的態勢。直到春節過后,我們從各自的鄉下老家回到省城,事情才有了轉機。
“我表哥開了家文化公司,請我去做策劃經理,工資挺高的,你說我去不去。”
“去啊,當然要去,你也該嘗嘗跳槽的滋味了。工資能高到哪里去?”
“是我目前的三倍吧,管吃住,而且將來還能入股。”
“嗯,那真不錯,你馬上就辭職,去表哥公司上班吧。”
“表哥公司好是好,就是有點遠。”
“在哪里?”
“深圳。”
小麗告訴我這件事的時候,已經做好了遠走他鄉的打算。她的計劃是:她遠赴深圳,掙那份比較高的工資,而我則留在原地,等她站穩腳跟,我再過去。
意識到將來我們要分開一段時間,我內心竊喜,卻面帶憂愁,表現出對即將離去的戀人的難分難舍。我還得問幾個問題,以示我在此問題上進行過深入的思考。
“我為什么不能跟你一起去?”
“你去?你住哪里?我住公司宿舍,不可能讓你也住進去,你去租房子,那又是一筆錢。咱們這里的房租已經交到下季度,你不如先住著,找到工作后就去上班。”
“那咱們怎么見面?”
“五一黃金周,我來看你。”
“好吧,我會想你的。”
“我也會想你的,咱們每天打一個電話。”
事情就這么定了,小麗打點行裝,去買了火車票。因為即將到來的離別,我們狠狠做了兩次,我沒有陽痿,小麗破天荒地叫起來,叫得拘謹而笨拙,十指摳進我后背的肉里。
與我合租的那對情侶,在小麗走后的第五天,也打點行裝離開了這里。這套房子有兩間臥室,我和小麗住一間,他們住另一間,如此合租,主要基于經濟上的考慮,我們原本素不相識,并無交情。沒想到他們會與小麗前后腳走掉。畢竟在同一套房子里生活了兩年,可謂朝夕相處,積攢了一點感情,分別時,吃了頓散伙飯。在桌前,他們說,這里不好混,打算去北京闖闖。言談之間,他們流露出對我仍固守此地的不解,小麗業已遠去,我沒道理還待在這里。我懶得對他們講將來的打算。實際上,我并無打算。本著過一天算一天的態度,我什么也講不出來,只能祝他們一帆風順。
房子霎時間空了。原本四個人共享的空間,完全被我一個人占用,讓我不知所措。而我還沒有找到新工作,每日大部分的時間都耗在這空蕩蕩的房子里。上廁所、洗澡和做飯都不用再統籌安排,隨心所欲,甚至可以去另一個房間的床上睡覺,他們還在的時候,這里可是個神秘的地方。
房東過來看了看,拜托我一件事,為那個空出來的房間找到租客。
“誰和你住在一起,由你來選吧。”
她認為我是個老實人,對我還算信任。而我正游手好閑,覺得這可能是件有意思的事,就答應了她。
我在網上發了條信息,附上房間的照片,床和衣柜赫然在目,可以隨時入住的樣子。手機開始頻繁地響起,我耐心地接聽一個又一個的電話。有性子急的,當天就登門拜訪。我穿著拖鞋開門,請他們進來,去那個房間打量一番。大多數人對房間還算滿意,只是對我本人產生了疑問。
“請問,你是做什么的?”
“我正找工作。”
“就你一個人住嗎?”
“是的,我自己。”
來看房子的,大多是情侶,偶爾也有成雙成對的女孩。盡管他們找了各種理由推脫,但我知道,事實是他們接受了房間,卻不能接受我。因為我是一個沒有工作的單身男子,無疑被認定為潛在的危險因素,就像一個精神病患者,說不準什么時候就發起瘋來,強奸,甚至殺人。我不想告訴他們,我是個有女朋友的人,在性方面并不饑渴,盡管她在南方的深圳。一想到她,我的欲望就灰飛煙滅。
我漸漸心生厭煩,在接電話的時候,首先向對方坦白:房子是不錯,但另一個房間里,住著一個單身男人,如果要來看房,請先接受這一事實。大多數人猶豫了,少數人表示可以接受,跑過來看看房子,又看看我,依舊否定了我。
如果我是個看上去文質彬彬的知識分子,情況就不會這么糟。我雖然酷愛讀書,也寫點東西,但這些并未在長相上顯露出來。小麗走后,我剃了光頭,頭皮發出青光,再加上一雙挑起的濃眉,更顯兇惡。
那天,我又接到一個電話,對方是個女孩,聲音清脆,聽上去干凈利落。我照例把情況說了一遍,以為她會猶豫一下,然后說聲不好意思,掛斷電話。沒想到,她卻毫無顧忌地表示要來看看。
“你什么時候有空,我過去看看?”
“我隨時有空。”
“好嘞,等會兒見!”
她所說的“等會兒”,真的是一段很短的時間。放下手機五分鐘后,門被敲響,我開門,外面站著兩個女孩。靠前的女孩說是她打的電話。她面帶笑意,長得不難看,再認真地看一下,好看的成分居多,算是個漂亮的姑娘。后面那個面無表情,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模樣也乏善可陳。我讓她們進來,把該看的地方都看一下。
“這是客廳,小了點,大了也沒什么用,這是你們的臥室,有床和衣柜,還有寫字臺,你倆住的話,挺不錯的。這是衛生間,可以洗澡,旁邊是廚房,可以做飯。”
“你住另一個房間?”
“是的,不是都告訴你們了嗎?”
“你一個人住?”
“是的,就我自己。”
“那好,我們商量一下。”
我在客廳里坐下,她們站在那個房間里,悄聲交談。似乎發生了一番爭論。雖然她們交談的時間長了些,沒事,我很有耐心,只等她們走出來,說聲不好意思,然后義無反顧地消失。不知為何,我突然生出一種希望她們留下的渴望。我想象著與她們朝夕相處的情景,其中一個畫面無比清晰:我打開臥室的門,迎面走過那個漂亮的女孩,她剛沐浴完畢,裹著浴巾,露出圓潤的肩膀。
“你們放心,我是個好人,沒有不良嗜好,我的業余愛好是讀書看電影,平常也寫點東西,不信我可以讓你們看看我發表的文章。”
我在客廳里大聲說著,單刀直入地插入她們的爭論之中。
“什么,你是作家?”
漂亮的女孩一躍而出,欣喜地看著我。我一臉無所謂的樣子,站起來,走進臥室,拿出幾本雜志。她翻到印有我照片的那頁,笑了。
“你真是個作家啊。”
“寫得一般,沒什么大不了的。”
“你有女朋友嗎?”
“嗯?女朋友?有的,她前段時間去了深圳。”
“你怎么不去?”
“我有可能過段時間去。”
她們對視了一眼,表示爭論結束,可以做出決定了。
“好吧,我們租了,相信你是個好人。”
“好,你們的行李在哪里,需要我幫忙拿一下嗎?”
“那太好了,我們請你吃飯!”
我們一起下樓,在樓道里,她們問我叫什么名字。
“我叫張東。你們呢?”
“我叫黃萍,她叫陳希。”
黃萍活潑漂亮,愛說愛笑。陳希有點冷淡,看上去和我的小麗一樣,是蕓蕓眾生里的老實人。
我們仨騎著車子,進入附近的一所校園。她倆半年前就畢業了,一直蹭住在學妹宿舍空余的床上,如今終于住不下去,只能被迫搬離。我站在女生宿舍樓下,等她們一趟趟把東西拿下來。幾大包的東西,一趟帶不走,只能跑兩次。如果沒有我,她們得跑四五次。
房子終于有了人氣。她們在房間里忙活著,不時發出清脆的笑聲。我打開電腦,與小麗聊了幾句。對于這里的變化,我只字未提。她說她的工作非常順利,南方的空氣也很好,沒有霧霾。
為答謝我幫忙搬運行李,她倆請我吃飯,地點定在菜市場內的會友飯館。這個地方是我選的,以前經常與小麗來此吃飯。價錢便宜,量又大。沒想到,這個飯館她倆也經常光顧。
“會友啊,我們常去!”
因為對同一家飯館的熟知,我們瞬時找到了共同話題。也因為我搬運行李時的殷勤表現,陳希似乎也對我略有好感,幾乎要忽略我那兇猛的光頭和邪惡的眼眉。在黃萍無窮無盡的話語的間隙,她會插上一兩句,并根據幽默的對白笑上幾聲。
我們三個人深入菜市場,掠過生意興隆的菜攤,到達會友飯館。老板娘是我們的熟人,她對我們的三人組合感到陌生,問我們是不是同學。我說不是,我們是同居的。
聽到“同居”二字,黃萍笑了笑,而陳希則馬上糾正我的話。
“什么同居啊,我們只是一起租房子的。”
點了三個菜后,黃萍問我要不要喝點酒,我點點頭,此刻我確實想喝幾杯。黃萍要了三瓶啤酒,分別擺在各自的面前,她拿著開瓶器,嘭,嘭,嘭,像開了三槍,讓平靜的啤酒泛起白沫,幾乎要噴出瓶外。沒想到,她倆也對啤酒表示出莫大的好感,積極主動地把酒杯倒滿。
“哥,謝謝你幫我們搬東西。”
“張哥,以后請多關照。”
一個叫哥,一個叫張哥,這兩種稱呼自此定下格局。
她倆挺能喝的,馬不停蹄地輪番敬酒。老板娘流星般來回穿梭搬運啤酒。這是一種讓人產生強烈傾訴欲望的液體。我喝得多,理所當然地率先把自己的故事和盤托出,主要講了講我的女朋友小麗,這也是她們最為關心的,不斷追問。
“她說要去南方,那就去吧,我知道,這是分手的前兆。”
“放心吧,她不會跟你分手的,你是個好人。”黃萍說。
“分手也沒什么,真的沒什么。”
“你該去深圳。”陳希說。
“別說我了,說說你們吧,在做什么?”
也是喝酒的緣故,她們坦白了自身的情況。畢業后,之所以還賴在學校不走,一則是從經濟方面考慮,省下一筆租房的費用,二是貪戀大學的學習氣氛,尤其是擠滿了用功之人的自習室和圖書館,非常有利于準備考試。陳希要考研究生,黃萍則兩手準備,司法考試和公務員考試,這兩個只要有一個成功,即可吃一輩子。這些考試,她倆都考過一次,全部失敗了。她們相互鼓勵,明年再考。我雖然覺得挺沒勁的,但也順勢說了幾句鼓舞人心的話,跟黃萍說小麗不會與我分手的話意義差不多。
“哥,你參加過公務員考試嗎?”
“沒有,這么說吧,我討厭任何形式的考試,除了必須要考的那些,我從未主動報考過什么。”
“你真瀟灑。我也覺得考試沒意思,有點不想考了,打算找個工作。”
“你可以一邊工作一邊準備考試嘛。”
“你不知道,這兩個考試沒那么簡單,如果不用全部的時間來準備,肯定過不了。”
我對于這些考試,確實知之甚少,于是不便多言。話題將盡之時,陳希問起寫作的事,她說自己也經常在網上讀小說,還提到了一兩本網絡小說的名字,問我有沒有聽說過。我搖搖頭,遺憾地告訴她,沒聽說過。
“你不是寫這些東西嗎?”
“不是的。”
“那你寫什么?”
“我寫的都是狗屎。”
我與小麗的交流日益稀疏。每天早上,她在網上問我一句,“今天去干什么?”我扭頭看看外面的天空,起身倒杯水,喝兩口,拿起笤帚打掃地面,而后擦抹桌案,再把門窗打開,站在窗前,看看外面。直到涼颼颼的空氣把房間填滿,我才回答小麗的問題。
“去面試。”
看得出來,她對這個答案是比較滿意的,通常會追問兩句,面試什么工作?有多大把握?工資高不高?
我不知道該如何作答,只好站起身,活動幾下,甚至做幾個俯臥撐。我回到電腦前,打出幾個字。
“我去了啊!”
隨后我在網上隱身而行,瀏覽幾個感興趣的網站,新建幾個下載任務,把網上的電影轉移到硬盤里。
這是寂靜的早晨,黃萍和陳希已經離去。她們挎著書包,前往附近大學的自習室,為考試做準備。按照她們的說法,只要通過了考試,就會有遠大的前程。好像真是這么回事。好像我和小麗也該這么干。當初剛畢業的時候,小麗攛掇我去考公務員,我沒去,她去考了,沒考上。也就是從那時起,她開始介意我的性格。
“你這人怎么這樣?”
“我哪樣了?”
“你是一個沒有上進心的人。”
“我不是一直這樣嗎?”
“嗯,我以前覺得那是一種灑脫。”
“現在呢?”
“現在覺得你是個傻逼。”
我沒想到傻逼這個詞會從小麗嘴里蹦出來。難道在我沒有察覺的某段時間里,她也在發生著改變?也許,這個詞早就駐扎進她的心里,等到時機來臨,像子彈那樣噴射而出,想必這種快意恩仇的感覺猶如她從未體驗過的性高潮。
她說得十分準確,我就是傻逼。那天我在會友喝酒,想著她的話,不知不覺就多喝了幾杯。多是多了,但沒到失憶的程度。我記得黃萍和陳希一邊一個攙扶著我,走過午后冷清的菜市場。為了不辜負她倆的好意,我裝作醉得更厲害些,雙臂放在她倆的脖子后面。她倆架著我,仿佛滿懷著革命友誼,艱難前行。

⊙ 黃土路·想飛的魚
我躺倒在床,黃萍倒了杯水,放在床頭。她帶上房門,悄悄的,不發出一點聲響。我沒有睡著,喝多后,總要上無數次廁所,排出的尿量幾乎要超過喝下去的啤酒。往回走的時候,即有大量的尿液匯聚在我的膀胱。我不好意思在跨進家門的那一刻就擺脫她倆的左右,狗急跳墻般沖進廁所。那樣會讓她們覺得我在裝醉。我要讓她們把好事做到底,讓人性的善良得到圓滿發揮,再伺機而動。
這房子對她倆來說,還有點陌生。她們在收拾東西,準備開始新的生活。在酒精的催發下,她們唱起了歌。我站在門前,聽她們唱。我好像還能憋,那就讓她們再唱一會兒。
“讓我們蕩起雙槳,小船兒推開波浪……”
當她們唱到“迎面吹來涼爽的風”的時候,我再也憋不住了,推開門,穿過客廳,一個餓虎撲食,沖進廁所。尿液滾滾,仿佛在強奸馬桶。
從這泡綿長的尿開始,我們三個人的同居生活拉開帷幕。每天的情景大致如下:早起時我們幾乎同時打開臥室的門,輪流使用衛生間。她們拎著書包走出門去,我則回到臥室,打開電腦看點什么。中午,她們回來,帶著蔬菜。我下廚,把蔬菜炒熟,放到客廳的茶幾上。三人圍坐,一邊說話一邊吃。晚飯也是如此打發。這兩頓飯體現出我們通過那頓酒建立起來的友誼。吃來吃去,好像一家人。客廳里回蕩著黃萍“哥、哥”的叫聲。
一大早,我躺在床上,眼睛盯著天花板,什么都不想,像個死人。外面的門響了,一個人的腳步聲,回蕩在客廳中。是黃萍還是陳希?我想做出判斷:這腳步輕快明朗,肯定是黃萍。我跟自己打賭。賭什么?我也不知道。
客廳中光線冷漠,涼意彌漫,猶如秋日的黃昏,更像空無一人的荒野。廁所里有聲音——水流沖擊洗手盆,一雙手接住水,拍打在臉上。我不能去敲廁所的門,假裝試探里面是否有人。她搞出這么大動靜,已經宣告了有人的事實,我再去敲門,騷擾的意圖太過明顯。我不想騷擾她,我只想知道她是誰。我要等她出來,看她長著誰的臉。
面對客廳的另一扇門突然開啟,一個人的腳步聲蔓延過來,令我猝不及防。我背對著她,不知來者為誰,情急之下,突然轉身,正與她迎面撞在一起。首先與我身體發生接觸的,是兩個乳房,來者不善,單單據此判斷,此乃黃萍無疑,更不用提那一聲悅耳的尖叫了。
據觀察比較,黃萍的胸無法無天地鼓著,想必里面埋伏著一對足以耀武揚威的乳房;而陳希的胸部一馬平川,猶如乏味無聊的華北平原。但我對黃萍的胸持謹慎懷疑的態度,經驗來自小麗。從外表看,小麗的胸挺鼓的,而一旦撥云見日,卻發現那是胸罩營造的假象。而經過這一撞,我終于發現黃萍的胸是貨真價實的大。她身穿睡衣,沒戴胸罩,一對乳房坦蕩豪邁地聳立著。我緊張得啞口無言,她卻連聲說著對不起。我逃回自己的房間,躺在床上穩定心神。
躺在幽暗的床上,我有些情思迷亂,恍恍惚惚中,我好像看見小麗突然出現在床邊,怨恨地看著我。我揮揮手,讓她走開。小麗知趣地隱身而去,只留下一攤模糊的聲音,那是發自鼻腔的一聲“哼”。在看了我新寫的小說后,她也會發出這種聲音,然后坦誠地告訴我,“你寫的就是狗屎”。
有人敲門,“哥,你是不是要上廁所?”黃萍在外面說話,真擔心她會破門而入,對我的齷鹺行徑嚴厲指責。
“哦,是啊,廁所你們還用嗎?”
“不用了,哥,你快去吧!”
“好的。”
我提上褲子,開門來到客廳。她們的門已然關閉。我站在黃萍剛剛來過的廁所里,釋放出積存整晚的尿液。洗手盆上擺著我們的洗漱用品,這些東西當然以她們倆的為主。我那瓶洗面奶,是小麗的“遺物”,她買來后用著不好,舍不得扔掉,于是讓我用,作為男人,我用什么都無所謂。我突然意識到,作為我生命中第一瓶洗面奶,竟然是一個女生常用的品牌。我拿起來,打算把這瓶用了一個月的洗面奶扔進垃圾簍,又有些舍不得,畢竟是幾十塊錢的東西,放回原處,接著用吧。
我洗了把臉,拿起另一瓶洗面奶,擠出一點,揉搓一會兒,抹在臉上。我不能確定這瓶洗面奶屬于黃萍還是陳希,只好又拿起另一瓶,同樣揉搓一會兒,把臉涂得像曹操那樣慘白。
一個月后,我終于找到一份工作,上述生活情景從而發生改變。每天早上我們一起出門,在小區門口,我們分道揚鑣,我趕往幾條街外的一家小公司,她們走向附近的大學。中午我們不能見面,只能等晚上才能在一起吃飯。
我的工作很簡單,抱著電話和一本黃頁,一家家企業打過去,問人家要不要接受采訪。我打了一個星期,所得到的回答都是不接受。不知道哪里出了問題,我可是完全按照公司要求講話的,說什么我們這里是省商務廳下屬單位,應政府要求,做一本刊物,宣傳優秀企業……我一遍遍說著這樣的話,說得久了,真的覺得自己是省商務廳的人,只是電話對面的人始終不相信。經理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的問題,“小張,你的聲音不夠自信,還懶洋洋的,要拿出政府人員的氣勢來。”
他裝腔作勢地示范了幾次,像個傻逼。像他這樣其實不難,只是我不想干。我想做得自然隨意,懶洋洋的語氣不正代表著政府人員天生的傲慢嗎?說這些,他肯定不懂。于是我就學他的樣子,學得盛氣凌人,讓他拍案叫絕。可笑的是,即便如此,對方還是不肯接受我的采訪。這仿佛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面對幾乎為零的成功率,經理鼓勵我保持樂觀的態度,“一個月內,有一家企業接受你的采訪,你就算沒白干。”我聽他的,不厭其煩地打著電話,機械地重復那套說辭。對方拒絕后,我說聲謝謝,掛掉電話,喝口水,然后撥出下一個號碼。可以這么說,我上班的每一天,都在被人不停地拒絕。兩個星期后,我變得麻木不仁,認為他們就應該拒絕我,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把找到工作的消息告訴小麗,她非常高興,希望我長期干下去。
“先干干看吧,這也不是能長久干下去的,電話遲早會被打完。”
對我這種說法,小麗馬上表示出一如既往的厭惡。
“如果這份工作你也干不下去,那等房租到期的時候,你就來深圳吧。”
“你終于想讓我去深圳了,我還以為,你根本不希望我去。”
“你怎么能這么想,我當然想讓你過來。”
“嗯,我知道了。”
“看來你留在石家莊真掙不到什么錢,我剛發了工資,給你打一千塊,你趕快買票來深圳吧。”
“不用了,總會有家企業接受我的采訪的。到時我就能拿到提成了。”
“別做夢了,你還是來深圳吧!”
上面的交談發生在網上。我本想給小麗打個電話,把她當成一家企業,用盛氣凌人的語氣,講出那套說辭,然后一起哈哈大笑。
我們文字交流的不快讓我最終放棄了給小麗打電話的沖動。問題是,我覺得打電話已成為我的一項技藝,急需找人展示一番。這種想法在心中盤桓幾日,終于按捺不住,趁經理不在,我鬼使神差般撥通了黃萍的手機。
我上班的時間,她應該正在大學自習室里刻苦學習。過了一會兒她才接,這幾十秒鐘的時間,想必她起身穿過了桌椅的叢林,站到教室外的樓道里。她“喂”了一聲。我馬上流利地說出那番話,遺憾的是,無論如何我也不能讓自己的語氣變得盛氣凌人。
“哈哈,哥,是你吧?”
“是我,哈哈。”
“太逗了,你每天都這樣說吧?”
“是啊,一天重復上百次。”
“哥,我不想考試了,我想上班。”
“為什么?現在工作可不好找。”
“不工作沒錢花。”
“家里不給你錢嗎?”
“給的太少,根本不夠花。”
“哦,那我們晚上再說吧。”
“好的,晚上弄倆菜,咱們再喝點。”
看來黃萍深諳借酒澆愁的道理,既然她要喝,我絕不反對。這時,我的手機顯示銀行卡里多了一千塊錢。是小麗轉給我的,她就是這樣,說到做到。我想,是不是應該給她轉回去?下班后,我找到一臺銀行柜員機,把卡插進去,顯示余額為1010。原本的余額是10,小麗通過在深圳的打拼,讓這個數字變成了四位。我的腦袋抵住冰冷的機器,想起和小麗度過的那些夜晚。我的樣子就像要扎進銀行柜員機里去。排在后面的人不耐煩地說:“哥們兒,你取錢還是睡覺?”
我幡然醒悟,慌忙把那一千塊錢取了出來。
我去買啤酒,考慮到黃萍和陳希的酒量,多買了些,足以讓我們三個人喝個痛快。回到房子里,發現她倆已從學校回來,正在廚房里忙活。
因為兜里揣著一千塊的原因,我的心情有點沮喪,也有點興奮,做好了大醉一場的準備。黃萍在廚房晃動的背影吸引著我的目光。從前,都是小麗的背影在那里晃動。黃萍的背影只不過纖細了一點,卻顯得出類拔萃,看著舒服。她發現了我,叫了一聲,“哥”。我答應著,走進廚房,打算搭把手。黃萍用雙手抵住我,將我推出廚房。
“今天你就嘗嘗我倆的手藝吧。”
我只好坐在沙發上耐心等待,其間回房間換了衣服,還去衛生間洗了臉,讓自己看上去隨意而干凈。她們的手藝擺上桌面,我嘗了嘗,還不錯,不由得大加贊賞。她倆坐下,倒上啤酒,和我一樣,也是大喝一場的架勢。
“哥,你今天要是不給我打電話,我竟然忘了祝賀你找到工作。”
黃萍說完就干了一杯。我連忙也干掉一杯,其實心里有點尷尬,因為我給黃萍打電話這事讓陳希知道了。陳希也敬我一杯,一改表情嚴肅的模樣,笑著說:“張哥,好好干。”
接下來,我們談起找工作的話題。這兩個女孩沒找過工作,希望我這個總在找工作的人傳授點經驗。我說:“只要別要求太高,工作并不難找。”黃萍問:“你工資高不高?”我說:“不高,兩千。”陳希說:“每月扣除五百塊的房租,你還剩一千五,再扣除五百零花,還剩一千,剛夠吃啊。”
“是啊,剛夠吃,但我還要攢錢,每月五百。”
“你攢錢干什么?哦,對了,你要去深圳找女朋友。”
“哈哈,買房子啊,誰攢錢不是為了買房子。”
“哦,明白了,哥,你真是個有上進心的人。”
“哈哈,一提買房這事我就想笑。”
“哥,你先別激動。真羨慕你能工作,不像我們,只是花錢,不能掙錢。”
“你們一旦通過考試,就可以掙大錢了!未來是屬于你們的。”
“但我們現在沒有錢啊。哥,我真的不想考試了,我要去找工作,一邊掙錢一邊準備考試,就像你說的那樣。”
我對黃萍的決定不置可否。沒想到,陳希竟然持反對意見,她仰頭飲下一杯酒,將酒杯重重蹾在桌上,嚴肅地說:“咱倆當初怎么說的?要一起學習,永不放棄,你可倒好,經歷了一次挫折就要放棄。”
“我真的學不下去了。”
“不行,你一定要堅持,你不學,我也學不下去!”
“你這人就是自私,沒有我,你照樣能學下去!”
“我自私?我自私能借錢給你?”
“我馬上還你錢,你自己去學吧。”
就這樣,倆人吵了起來。我連忙勸解,讓她們安靜,不要攪了喝酒的興致。她們終于安靜下來,沉默而兇猛地喝酒。我為了打破僵局,頻頻敬酒,講了幾個笑話,讓她們笑了幾聲。氣氛終于有所緩和。黃萍主動向陳希敬酒,并道歉,但表示找工作的意愿已無法更改。陳希依然不高興,勉強接受了對方的歉意。她突然站起身來,憤憤地說:“你倆喝吧,我先去睡了。”
陳希走進臥室,重重地關上門。黃萍斜視一眼,說:“哥,她不喝拉倒,來,咱倆喝。”
因為彌漫在空氣中的那點莫名的哀愁,我們迅速喝完了剩下的啤酒。我感覺自己的身體處于大醉的邊緣,勉力支撐,上廁所撒尿,用涼水洗臉,這才清醒一點。我從廁所回到客廳,發現黃萍不見了。我的臥室門開著。黃萍正坐在我的桌前玩電腦。我坐在床上,看著她的背影。她長發披肩,腰部的弧線攝人心魄。電腦屏幕上晃動著淘寶的頁面,她在看衣服,喝了那么多,她還能看清嗎?
“哥,能不能借我點錢?”
“行,你要多少?”
“一千吧。”
“我就剩一千多了,先借你一千好了。”
我搖晃著,拿出白天從銀行取出的錢,放在電腦鍵盤上。黃萍說了聲謝謝,順勢把頭靠在我尚未撤離的手臂上。我撫摸她的頭發。她一把將我抱住,哭了起來。我也抱住她,并輕輕拍打,讓她不要哭。她站起來,向我展示滿臉的淚水。我內心一陣翻騰,先用手為她擦去眼淚,然后吻了上去。
“哥,你先別激動。”
黃萍輕輕地推我,力道太小,難以奏效。我抱緊她,繼續吻她。她不再掙扎,配合起來。我們倒在床上,迫不及待地脫光了衣服。
在這之前,我從未和小麗之外的女人做愛,以至于我的笨拙讓她一次次笑場。
“哥,你先別激動,慢慢來。”
……
我是被渴醒的。起床找水喝,掠過黃萍的身體。我一邊喝水一邊看她,喝完了,又掠過她美妙的身體,躺進床的里面,扭頭看她,睡過去。
等我醒來,已是中午,卻看不見她。我坐起來,打量房間的各個角落,都沒有她。頭痛得厲害,像被人打了。我穿好衣服,來到客廳,看見陳希正坐在沙發上發呆。衛生間里悄無聲息,我推門進去,黃萍果然不在里面。我排泄完畢,回到客廳,問陳希:“黃萍呢?”
“她走了。”
“走了,去了哪里?”
“北京。她去北京找工作了。”
“她怎么走得這么急?”
“我怎么知道?她總是這樣,說發瘋就發瘋。”
我連忙回到房間,找到手機,撥通黃萍的電話。在等待的忙音中,我仿佛看見黃萍拉著行李箱從我門前走過。
“哥,對不起,我去北京找工作了。”
“你怎么能這樣?”
“哥,你先別激動。借你的錢,我會還你的。”
“你怎么能這樣?”
“哥,你先別激動。雖然我們搞過了,但那并不代表什么。你還是你,我還是我。就是這樣,你懂我的意思嗎?”
在喧囂的背景聲中,黃萍掛掉了電話。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和陳希一起發呆。陳希說:“昨晚你們搞得很爽。”
“你都聽見了。”
“嗯。她是個騷貨。你有女朋友的,你不該搞她。”
“陳希,我是不是很愛激動?”
“什么?”
“你說,我是不是很愛激動?”
“是啊,你看,你現在就很激動。”
這天剩余的時間,我都躺在床上,一是為了醒酒,二是為了消化黃萍離去的事實。下午四點,小麗打來電話,我拿著手機看了半天,最終還是接了。她第一句話就問我在做什么。我毫不隱諱地告訴她,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本人還高臥在床。意外的是,小麗并沒有被激怒。電話那頭的小麗仿佛已經在南方的艷陽里脫胎換骨,她語氣柔和而且略帶緊張,問我是不是病了。我原本以為她會質問我為什么沒去上班,那樣的話,我會說再也不想去打那些徒勞無功的電話了。她突如其來的關切讓我猝不及防。
“沒事,只是昨晚喝多了。”
“唉,你又喝大酒。有件事,不知道該不該對你講。”
“什么事?你快說!”
“這邊的工作我不想干了,想回石家莊。”
“怎么回事,不是干得好好的嗎?”
“你別問,就是不想干了。”
“好吧,那你回來吧。”
“你真的不想知道我為什么不想干了?”
“哦,你為什么不想干了?”
“唉,你還是別問了。”
“操,你不說還讓我問!”
“你今天怎么了,這么愛激動?”
“你也覺得我是個愛激動的人嗎?”
“你以前不這樣,從來不激動,跟塊木頭一樣。”
“哦,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就愛激動了。”
“我喜歡你激動。你一激動我就覺得你充滿了活力。”
“好,那我以后就經常激動給你看。你哪天回來?”
“還沒想好要不要回去。”
“你剛才說要回來,你他媽的到底想好沒有?到底為什么?”
“唉,說了你可別生氣,激動一點可以,但你別生氣。昨晚上我陪客戶去唱歌,那個老男人對我動手動腳的。”
“就因為這事?”
“是啊。你怎么沒生氣?你甚至都不激動,你根本不愛我。算了,我還是不回去了,你來深圳吧,馬上買票過來,以后我陪客戶的時候,你也跟著,幫我把他們灌醉。”
“小麗,咱們分手吧。”
“你說什么?”
“您好,我這里是省商務廳下屬單位……小麗,咱們分手吧,您看可以嗎?”
“你是不是在發神經?什么省商務廳……”
我不想再聽小麗說話,把手機掛斷。最后那段話,我激動到極點,聲音顫抖,相信這些沒有妨礙我的表達,希望小麗在心領神會之后,平心靜氣地考慮一下。也許,她將是第一個沒有拒絕我的人。深圳是一座適合她的城市,就像石家莊是一座適合我的城市,讓我們各守一座城,就這么瞎混吧。我打定主意,關上手機,冷靜地躺在床上,等外面的光線變暗。根據以往的經驗,大醉后的身體在黃昏時分才能恢復基本活力。這是夏天,黃昏來得很遲。時間好像凝固在光明的白天,華北平原迎來一次前所未有的極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