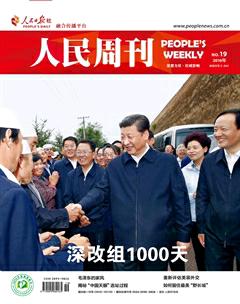中國或將有第19個稅種:環境保護稅
馬卓敏++王亦君
污染重才會負擔重,多排放多納稅,少排放少納稅,這也是開征環保稅倒逼企業減少污染的應有之義。
我國或將有第19個稅種——環境保護稅。《環境保護稅法(草案)》(以下簡稱“草案”)8月29日首次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草案提出在我國開征環境保護稅。這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立法法》對“稅收法定”作出明確規定之后,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首部單行稅法。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作草案說明時表示,草案的立法原則是“稅負平移”,從排污費“平移”到環保稅,征收對象等都與現行排污費保持一致,征收對象為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噪聲。
“稅負平移”的立法原則
我國從2003年開始征收排污費,截至2015年,全國累計征收排污費2000多億元,繳納排污費的企事業單位和個體工商戶累計500多萬戶。樓繼偉說,排污費制度對于防治環境污染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與稅收制度相比,排污費制度存在執法剛性不足、地方政府和部門干預等問題,因此有必要進行環境保護費改稅。
雖然中國已頒布《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但地方政府能真正做到按條例辦事的并不多,記者查詢各省排污費征收情況后發現,每個省區市都有大量重點污染企業因“政策性免征”不用繳納排污費,這其中不乏長期污染大戶。有業內人士表示,近年來,排污費減免成了一些地方“政策優惠”“減輕企業負擔”的借口,甚至成了個別人權錢交易的“籌碼”。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說,未來一旦由稅務部門征收環保稅稅款,且環保部門配合,將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排污費制度帶來的執法剛性不足等諸多隱患。
“這是因為一旦改為稅收體制,地方政府就不能隨便‘拍腦袋,想減免就減免,想增收就增收。”常紀文認為,這將從側面對中國節能減排任務產生有利影響。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經濟法研究室副主任劉洪巖也認為,“費改稅”可實現兩個具體功能:一是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執法亂象,從此變成有法可依,對于地方政府來說有相當的約束作用;二是可實現一定的市場公平競爭,不僅不會加重企業負擔,反而會規范整個市場。
由于征稅可做到一視同仁,劉洪巖表示,這就避免了排污費在操作上產生的一些地方政府靈活性過大的問題。“在原有的排污費制度下,他們可以根據自身和企業的關系好壞決定征收標準,而這無形中造成某些企業的負擔過大。”
排污費改為環保稅后,將產生多大變化?樓繼偉指出,環境保護費改稅按照“稅負平移”的原則進行,納稅人為在我國領域和管轄海域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征稅對象則為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和噪聲。在稅負方面,草案以現行排污費收費標準作為環境保護稅的稅額下限,允許各地在規定基礎上進行上浮。但這并不意味著企業的稅負將會增加,因為現行排污費也同樣是各地有別,比如北京的收費標準是最低標準的8~9倍。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白景明表示,污染重才會負擔重,多排放多納稅,少排放少納稅,這也是開征環保稅倒逼企業減少污染的應有之義。
流動污染源應否征稅存爭論
草案中規定環境保護稅的納稅人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向依法設立的污水集中處理、生活垃圾集中處理場所排放應稅污染物,繳納處理費用的,由于其不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不繳納相應污染物的環境保護稅;在符合國家或者地方環境保護標準的設施、場所貯存或者處置固體廢物的,不繳納固體廢物的環境保護稅。
與現行排污費制度的征收對象銜接,草案規定環境保護稅的征收對象為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噪聲等4類。
草案以現行排污費收費標準作為環境保護稅的稅額下限,規定:大氣污染物稅額為每污染當量1.2元,水污染物為每污染當量1.4元,固體廢物按不同種類分別為每噸5~1000元,噪聲則按超標分貝數,稅額為每月350~11200元。
對于草案,目前仍存在很多爭論。對于草案中提及的“對機動車、船舶和航空器等流動污染源排放的應稅污染物實行免稅”,劉洪巖認為,這是一個明顯的缺陷。征收環保稅,其范圍應根據不同的排放情形而定。“應包括水污染、空氣污染、固體廢物以及碳排放等,草案對這方面的關注度的確不足。”
在劉洪巖看來,未來將航空器等流動污染源納入征稅范圍是必要的,但考慮到中國航空器的碳排放問題和促進產業發展等相關因素,從國情出發考量,暫時未被納入征稅范圍。“另一個因素是此類事件的征收成本可能過高,而高于稅收額的征收成本也是目前無法實施征稅的重要原因。”
常紀文則表示,一架飛機的排放量相當于幾百輛汽車的排放量,今后還會有更多家用小飛機出現。因此,對航空器和機動車等是否征收環保稅,應授權國務院作出進一步決定。
應厘清稅收環保兩大部門的權責
草案課稅范圍主要涉及破壞環境的污染排放行為,不過呼聲極高的碳排放沒有包括在內。鑒于環境保護稅是新稅種,碳排放暫不納入其中,無疑有助于環境保護稅法的出臺,且可以為國內經濟發展贏得相對寬松的空間。但長遠來說,開征碳稅,將碳排放植入環境保護稅中,不僅能夠釋放自身國際政治壓力,而且可以應對發達國家的碳關稅威脅。
同樣值得考慮的是將污染產品歸入環境保護稅的課稅范圍。目前污染產品由消費稅課征,但消費稅終歸不是環境保護的特定目的稅。更為理想的方案是,將已由消費稅課征的污染產品交由環境保護稅課征,實現環境保護稅法與消費稅法的協同規制。
草案“稅收征管”專章12次出現“環境保護主管部門”這一非稅征管部門,其中5處提到環保部門的職責,這是過往稅收立法不曾出現的獨特景觀。如此強調環保部門的作用,與環境保護稅計稅依據的特殊評價機制有關。
環境保護稅以應稅污染物的排放量為計稅依據,而排放量的計量和判斷均需要高度專業化的技術條件,不易為一般納稅人和稅務機關所掌握。草案強調“稅務征管、環保協同”,便是對這一技術困局的回應。
不過,草案只是提及稅務機關與環保部門的協同征管,既未真正厘清二者之間的法律關系,又未科學設定協同征管不力等的補救機制。恐怕難以滿足“排污費改稅”加強征管、增強執法剛性等原初目的。
比如環保部門針對排放量的核定,對稅務機關來說,可以視為一種證據還是只能看作是一種常規的聯合執法?再如物料衡算、排污系數、抽樣檢測,或者自動監控數據的核定計量,能否作為環境保護稅行政處罰,甚至追究稅收刑事責任的事實依據等等。
此類問題的解決,都建立在環保部門與稅務機關清晰的定位基礎之上。如果不能有效界分兩大部門的權責,調動環保部門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排污費征管中可能出現的問題,環境保護稅征管中照樣可能出現。不僅如此,采納兩個部門協作課征環境保護稅的新型稅收征管模式,還可能帶來一系列新的問題,環境保護稅立法必須高度重視這一點。